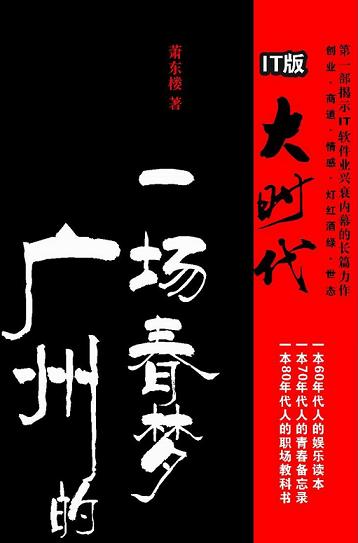最长的一天:我见证了诺曼底登陆-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背上降落伞前,我们将这些装备包系在C…47飞机的底部。起飞命令下达的时候,夜幕刚刚降临机场。约摸晚上10点——英国的夏令时提前了两个小时,每人挑了一个叠伞员精心叠好的降落伞,然后背上伞包、扣好搭扣、将装备归位。班里的成员要互相协助才能完成这项任务,独自一人几乎不可能办得到。制服,也就是跳伞服的许多口袋都充了气,和每人背在背上的一种叫做野战背包的帆布包一样,一旦触地,即刻膨胀。每名官兵身上携带的物资重达150磅。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物品:
我的个人物品:一杆M…1型步枪和枪套、4份K型干粮、150发30毫米口径的子弹、4颗手雷、一颗叫做熏腿手榴弹的反坦克手榴弹、一副防毒面具、一块手帕、两双袜子、一条内裤、一个盛满水的水壶、两个急救包、牙刷和牙粉、安全剃须刀和5片刀片、一块香皂、一块手表、身份识别牌(贴在一起的狗牌牌)、10包骆驼牌香烟、一卷战时货币、一把挖战壕的工具——一把鹤嘴锄、带子弹带的野战背包、钢盔、一把折叠刀、一把双刃匕首、24张手纸、铅笔、纸张、一本法语短语手册、净水用的哈拉宗药丸、火柴、打火机和刺刀。
22点50分左右,我爬上舷梯,进了C…47运输机。刷在机头上的机名是“凯丽琪小姐”。我在铝制长凳上没坐多久,就有了尿意。这种被大家戏称为会飞的箱车上没有厕所。也就是说,我只能起身,请人扶着走下舷梯,在机翼下方便。身上绑着降落伞带外加装备,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这种“紧张撒尿”综合症,我们班人人都经历过。舷梯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第23页 :
马达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机上很少有人说话。我使劲儿地想象一旦落到海岸上会是一番什么样的遭遇。会和跳进西西里那晚一样吗?出了舱门我能好些吗?我会不会在半空中给一枪毙命?我的伞能不能打开?
临近诺曼底海岸上空时,看到红色警示灯的跳伞长下令起立挂钩。这时,伞兵将各自的开伞索挂在一根差不多与机身一样长的钢索上。一旦跳出舱门,开伞索即从伞包中拉出降落伞,让伞对准机尾排出的气流,正常打开。跳伞长喊出的第二条命令是:“检查好装备的报数。”站成一排的每一名伞兵要报出自己的数字,表明自己亲手检查完毕,也就是用手摸站在自己前面的伞兵的开伞索等装备。我报的是“6号,正常”。×米×花×书×库× ;http://__
这时,跳伞长站在飞机的舱门内,双眼紧盯着即刻就要转绿的红灯。届时,他会大喊一声“跳!”接着纵身跳下了飞机。其他十五个人飞快地跟着他鱼贯而出。飞机的速度约为150英里/小时的巡航速度,能看得见小巷中小小的身影,但我尽量从狭小的舷窗往外张望。只见从眼前一闪而过的曳光弹,以及地面上燃烧的飞机。
飞机飞临空投区域,飞行员亮起了绿灯,16名伞兵迅速鱼贯而出。大家跳离飞机时间均不超过30秒。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无疑急着返回英国大本营这个安乐窝,发出绿灯“起跳”信号后忘了减速。这次的跳伞速度是90英里/小时。我刚离开舱门,飞机就大头冲下。我的伞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看见机尾从我头顶几英尺的上方掠过。接着,一股螺旋桨推过来的强气流涌进了我的伞,这是我经历的最强的一次开伞冲击。高速度导致伞打开时猛地一拉。伞猛然一晃,把我从一名意大利海军军官手上缴获的750毫米比雷塔手枪给晃掉了,还外带跳伞服口袋里的一把崭新的吉利保险剃须刀。我跳伞的时间大约是0145时,也就是凌晨1点45分。当时是1944年6月6日,D日前五个小时。由于我着陆的时间非常短,肯定不超过30秒,我估计我跳伞时飞机的高度不超过325英尺。非常低。
落到了地上,我吓了一跳,虽说既紧张又害怕,我还是连忙完成了下一个步骤。我卷起降落伞,和备用伞一起塞进了一个灌木丛。接着又将三块加兰德M…1型步枪拼装好:枪身、枪筒和枪托。然后又往步枪的弹膛里压了一梭子弹,装上了刺刀,这都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完成的。黑暗中,传来一阵自动武器开火的声音,只见几枚曳光弹和高射炮火向空中飞去。
着陆后听到第一个人发出的声音,是班里的一名战友的呼救声。班里的另两名战友也听到了这个声音,我发现我们的朋友,来自阿拉巴马州塔拉哈西〔43〕的马里兰J高登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他左腿骨折。我们为他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抬到一处树篱后,等营部军医过来。
这时候,我摸黑去找其他美军。我降落在一座法国农场,此刻走进了一座农家的院子。总之,我和班里照顾伤员的两名战友走散了,现在是孤身一人。我掏出“蟋蟀(快板一样的两片小板子)”,这东西进攻部队人手一个,用以判断对方是否是个美国佬,或者说一名美国兵。
我碰到的恰好是另一支空降部队的三名美国佬。我们继续寻找其他美军士兵,并尽量避免和德军交火,但两者都没碰到。远处传来了交火声。我们没和敌人交上火,没发一枪一弹。拂晓时分,我们碰到了几名看似了解一些情况的美军官兵。我们和他们一道,向南走了两三英里,来到圣…梅尔…艾格里斯村。集结地是一片足球场大小的空旷地带,位于村子北端。东和南端各有一条很深的战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挖的战壕相似,显然是德军挖的,一排树篱横在这片场子的北边。
我们一整天都耗在修筑集结地四周的防御工事上。前哨设在工事的外围,架设的两挺轻机枪的火力带可压住东西两个方向。这段时间,我和步枪班的战友等着看有什么情况发生。这一天都没见敌人来这一带活动。我们吃了K型干粮,我试着在离深战壕非常近的地方睡了一觉。一位显然是同情盟军的法国人给我们送来几瓶叫做卡尔瓦多的酒精饮料。我喝了一杯,然后倒空了自己的水壶,灌上了这种美味可口的饮料。没过多久,看见我灌水壶的排长特德彼得森少尉命令我倒掉。尽管这位军官说酒里可能下了药或对我身体有害的说法,我不敢苟同,但我还是不情不愿地照办了。
这一天,空军的活动相当频繁。一整天都能见到歼击机、P…51战斗机、轰炸机。下午时分,我看见三架C…47运输机,载着补给物资飞过我方阵地上空,将带着补给的降落伞投到了德国人手中。飞行员显然搞错了空投区域。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协助战友沿营区西面边界的路上埋了一些反坦克地雷,这些随机埋设的地雷,可对敌军的车辆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夜色降临后,我裹了一顶降落伞,睡了过去。(回忆打印文稿,美国新奥尔良国立D日博物馆和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美国研究中心)
第24页 :
约瑟夫A戴利亚
我们跳了下去,散落得遍野都是。我们排没能结合齐,我跳得不错,落到了一家奶牛场的一堆肥料上。下来的时候,见地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以为是德国人,但出乎意料的是,不是德国人,是一群奶牛。
我碰到的第一个兄弟是约翰逊中士。要不是我反应快,他差点一枪结果了我。我们共集合了6个人,卡尔奎斯特中士,约翰逊中士,副排长鲍克斯迪,哈泽尔琼斯,德米迪欧和我自己。当天下午,我中了狙击手一枪。这颗子弹从我的步枪弹到我的左手,打得刺刀和导气室与枪身分了家。我拼命地在树篱间奔跑,我的一帮兄弟都惊呆了。要不是来自新泽西的上等兵德米迪欧为我实施了紧急处理,我的血会淌得全身都是,我估计是伤到了动脉。※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的枪废了,帮不上他们,于是他们丢下了我。我手上仅剩四颗手榴弹。他们走了以后,我设法挪到了一户法国农家,这家人对我是悉心照顾。可惜没过多久,两名德国人到这户农家来找吃的。他们发现了我,把我给抓了起来。两人用马车把我带到了离农舍11公里外的一个镇子,然后又送进了一处设在天主教修道院里的前线救护站,在这里,一名德国医生给我做了手术,为我截了中指,又把我的拇指缝了上去,清除了我的掌指骨。法国医生会说英语,他问我,“你是不是美国人?”我向右转过身,给他看我缝在袖子上的美国国旗。这位医生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大学学过医,是已故红衣主教孟德莱昂〔44〕的座上宾。手术以后,我与其他6名美国伤兵住在一间病房。(回忆打印文稿,美国新奥尔良国立D日博物馆和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美国研究中心)
杰克艾萨克
真倒霉,我们飞向海岸的途中,遇到了大雾,为避免与其他飞机发生碰撞,一部分飞行员只好采取规避行动。记得我们这组三架飞机向左掉转机头,向北飞去,也就是说,我可能远离了预定目标。这将是我第三次空降作战,也是我平生第28次跳伞。冲出雾区后,约莫进入内陆3到4英里,我没看见别的飞机。空中有一些浮云,德国人的防空炮火非常猛,都是轻机枪,20毫米口径,有的是88毫米威力很大的家伙。不论是东西南北,都能看到猛烈的防空炮火。我想是没有高射炮朝这架飞机直接开火,我们才没有被击中。刚一到空降时间,红灯就亮了起来,等绿灯一亮,我就知道自己到了陆地的上空。至于哪片陆地倒没有多大区别,带领一队18名伞兵跳出去,是我的职责,因此,一接到飞行员发的绿灯指令,我就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离地面越来越近,夜色中,我看得很清楚,本来前往诺曼底,却落进了一块相当大的农田里,这块地长宽约150×250码,四周围了一圈树篱。下降过程中,我见地里有几头奶牛,这让我放了心,地上有奶牛,说明这块地肯定没埋地雷。
我平平安安地落了地,解下伞包,着手去召集我的人马,能找一个是一个,然后指挥他们向目标出发。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但我不认识他,这表明附近还有别的飞机,只不过我没看到罢了。找到这名士兵后不久,我们听到有车辆开过来的声音,当时我不知道这块地在一条沥青路的东面。我俩认准这是辆德国人的车,得想办法打一个伏击,于是立刻循着车子的声音跑了过去。这辆车比我们还要快,还没等我们赶到,它就从沥青路上开了过去,不过,我们占据了一个有利地形,以防还有车过来。我们断定,这是一条沥青路,来往的车辆肯定不少。
第25页 :
我在这个点待了5…10分钟,一辆车也没见到,于是又动身去找人。这时候,传来了一声对口令的响板儿,循着响板声,我发现一名受了重伤的士兵。德国人在诺曼底大一点的田地里竖起了木桩,用来阻挡滑翔机着陆。他们在地上竖起一根根电话线杆大小的桩,但没那么高,离地约10…12英尺,而且还屁颠屁颠地把杆子给削尖了,像是一根根插在地上的大铅笔。倒霉的是,这名士兵正好落在其中的一根杆子上,摔折了大腿。他疼得死去活来,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什么也干不了。我没办法带上他。每名官兵的跳伞服内都有了一个装了吗啡的急救包,我掏出他的吗啡,给他注射了一针,然后拿起他的步枪,上了刺刀,倒插在地上,又将他的头盔挂枪托上,这算是一个通用的标志,表明这名士兵已经退出了战斗,无意再参战,然后我又动身去找其他人。
到了农田的北侧,此时大约是我们跳伞后一个半小时,我遇到了另几名美国伞兵,不过,我一个都不认识,几个人正沿着农田北侧的树篱走。最后,我总算见到了战术教官帕特沃德上尉,他集合了几名弟兄,我们合并在一起。当然,我们达成了一致,立刻动身赶往圣…梅尔…艾格里斯。我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总结出一条经验,如果偏离了空降区域,不论你找到谁,他都得听从你的指挥,向目标前进,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执行这一任务。
我们还找到了两三个装备包裹,将物资集中在一起。黎明时分,在这片农田的西北角发现了一处小屋子,我们转移到了那座宅子,将这儿当做一处集合点。我们派了一两个士兵出去打探消息,看看这一带还能不能再找到几名伞兵,最后,我们集合了约35个人,其中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