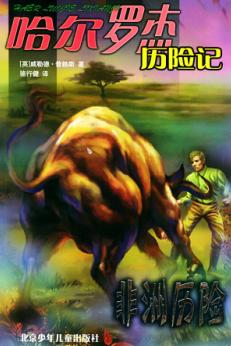思想的历险-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姆斯·卡麦隆那样做一个报纸专栏作家? 你得做你擅长的事情。我倒很愿意自己能有詹姆斯·卡麦隆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样的天才,可我不是。不过,我能做这个(工作),他们却不一定能做我能做的事情。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
安德鲁·高尔斯
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1959-),《金融时报》总编辑。 2002年下半年,《金融时报》亏损了600万英镑,在英国的发行量已跌到15万份以下,比五年前降低了25%。高尔斯决定花费300万英镑用于报纸的重建工作,如在日刊中增加体育版块,加强对艺术和专题的报道力度,增加一份每周六出版的杂志以及周末《商业增刊》。重建工作开始后的第一周,《金融时报》的发行量就上涨了5%。 1983年,路透社的实习记者高尔斯加入《金融时报》。1994年,他升为该报副总编。时任总编辑的理查德·兰伯特前赴美国开创美国业务时,高尔斯任代总编一职。2000年,高尔斯被派往德国汉堡,负责建立《金融时报·德国版》。2001年9月,控股该报的皮尔斯集团的CEO马约莉·斯卡迪诺宣布高尔斯将升任总编辑,接替理查德·兰伯特的职位。 。 想看书来
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1)
“一位杰出的记者。”斯卡迪纳—商业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皮尔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安德鲁·高尔斯的评价再简洁不过了。2001年5月,时为《金融时报》德国版主编的高尔斯先生被宣布任命为这份创办于1884年、在橙黄色新闻纸上印刷的报纸的新任总编辑。“它令我感到颤栗与荣耀”,当时42岁的高尔斯这样评价他的新职位,“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新闻职位之一。在国际商业、金融与时事的报道上,没有比《金融时报》更出色的了。” 高尔斯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对着泰晤士河,你可以看到河水静静地流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内,理查德·兰伯特—高尔斯的前任—用10年时间将《金融时报》带入了一条看起来前程似锦的通道。当他离任时,这份报纸的全球发行量由1991年的28万份增加到2000年的47万余份,美国版与德国版分别在1997年与2000年创办。尽管在发行量上仍与180万份的《华尔街日报》相去甚远,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它的读者几乎囊括了政界、商界与意见领袖。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的第10页是格林斯潘翻阅《金融时报》的照片。 除去对于新闻职业本身的严肃追求、对于商业新闻的详细报道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崇、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是使《华尔街日报》卓尔不群的重要因素。那么是什么使《金融时报》与众不同呢?对大多数的陌生读者而言,这份报纸在1893年的一项伟大的市场策略仍具有感召力。当时经营者为这份报纸引入了新奇的粉红色,这是令《金融时报》在类似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今天很多报纸在印刷商业版时采用这种颜色,并称之为商业粉红色(business pink)。但是,除去颜色,以及每一位《金融时报》的编辑都会强调的“高质量的新闻品质”外,这张报纸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餐桌上的经济学”,这是一家欧洲媒体对于《金融时报》的评价。在过分注重事实陈述的新闻界,这张报纸却带有一定程度的学究气,它的经济学与金融分析,优雅而不回避专业精神。此外,高尔斯先生还乐于承认,这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商业报纸,它四分之三的发行量是在非英国地区,而本国的新闻不过占到15%左右。也就是说,斯卡迪纳女士与兰伯特先生在1997年雄心勃勃地为《金融时报》制定全球计划时,它赶上了一股看起来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 对于媒体而言,时机、潮流与自身的品质同样重要。长达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推动了《金融时报》在全球的扩张,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特质—如何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商业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声音。《华尔街日报》在每个区域设立不同的版本,并尽量使内容“本地化”。而《金融时报》则尽量“全球化”,它的各种版本几乎拥有一致的内容。它是由伦敦编辑中心设计出的“四海一家”的报纸,它是不以国籍与地域为限的世界公民的读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经济学人》与《国际先驱论坛报》有着类似的定位。它们遵循一种更为普适的原则,寻找一种超越区域性的视角。正如高尔斯曾写的:“这份报纸坚信超越边界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我们相信这是惟一健康的方式。” 但是高尔斯执掌《金融时报》之时,也正是这种全球融合遭遇挑战之日。这是一份充满荣耀的工作,但它却面临着更多来自内外的挑战。“在‘9·11’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对于从事了多年国际新闻报道的高尔斯来说,这的确是个伟大的时刻。从双子塔的倒塌,到安然公司的丑闻,再到阿富汗的重建,以及今日的伊拉克战争,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为这一代新闻记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是战争,以及战争之后遗留下的长时间的后遗症,除此无它。”安德鲁·高尔斯在2002年12月中旬,向我们预测未来几年新闻业最重要的报道方向。 《金融时报》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出色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高尔斯的个人经验。他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包括普京、拉宾在内的众多政治领袖。他还是一位中东事务专家,他与另一位同事合作的《阿拉法特传》被认为是一流的传记作品。 卷入这种重塑历史进程的报道的确激动人心,但是已经身为总编辑的安德鲁·高尔斯却必须面对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的重大事件使世界经济陷入恐慌,经济下滑使《金融时报》的主要客户群不断裁员,并减少广告投入。比起2000年的8100万英磅的收入,《金融时报》在2001年的收入下降至3100万英镑,而这个数字在2002年则陡降至180万英镑。它的广告收入则在2001年和2002年里分别下跌20%和23%。当然,这与高尔斯先生实在没有太大关系,全球的报业都在面临这种考验。除去经济衰退的因素,他们还要与不愿意读报纸的新一代年轻人做斗争。 也就是说,兰伯特在缔造了一个光辉时代之后,还顺便带走了《金融时报》的好运气。当然,高尔斯先生不会承认他生活在“影响的焦虑”之中。他是一个温和而低调的总编辑。人们常说兰伯特具有牛津教授的风范,是一位公共哲学家。但高尔斯则是一位典型的记者形象,他的身材短粗却有力,他的回答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足够真诚,他的表现使他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坐着回答问题时还时不时把身体往椅子里陷,这个举动使他有点孩子气的胖胖的面孔分外有趣。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2)
高尔斯为2003年设定了很多计划,他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是《金融时报》的销量达到70万份。而谈到在这样动荡的世界里《金融时报》应扮演的各种角色时,高尔斯说是帮助人们重建全球信心。更为清晰的表达是他在《金融时报》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上的导读:“《金融时报》身处智慧中心。我们拥有清晰的信条与同伴,我们倾向投资于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头脑……我们的英国根基给予我们牛斗犬的品质:坚定,值得信赖与从不害怕拥有足够支持理由的战斗。对于《金融时报》而言,比起显而易见的观点,我们更愿意陈述不受欢迎的论点。当我们偶尔变得不那么受敬重和不可预测时,我们为此而高兴。大体而言,美国的价值观就是《金融时报》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关乎提高民主、人权与自由投资时,我们会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不恐惧美国的权力,我希望这种权力有适当的用途。比起退回到最近的范围,《金融时报》希望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接触。《金融时报》……” 这份半宣言式的文字令人想起了安德鲁·高尔斯的大学时代。1979年,20岁的剑桥学生高尔斯与他的同学一起编辑着一份独立的学生报纸《Stop Press》,并赢得了《卫报》第一届学生新闻奖。24年后,高尔斯说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最终放弃了成为舞台演员的梦想,而投身新闻业。从中他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经验:首先,新闻远不止杰出的散文写作。你不是要从容而优雅地坐在书桌前写作,而是更需要把你的鞋底磨穿,把你的手弄脏;第二,这培养起他的反抗本能。他与同学们都试图让权威们更不舒服,他们要制造噪音来打破规范;最后,他还深深地理解了编辑独立的重要性,即使在这份学生报纸面临破产时,他们都拒绝用独立编辑原则来做为交换。 。 想看书来
访谈(1)
两年前,当你成为《金融时报》新总编辑的候选人之一时,你面对的是罗伯特·汤姆森等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你的什么特质令你最终赢得了任命? 我猜想,这是我以前丰富的从业经历的结果,尤其是我在德国创办了一份新报纸(《金融时报》德国版)。我去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国家,说的也非母语,招募了150个编辑记者,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团队,做出一份报纸来。这就是同事告诉我被选中时的想法,我想在德国的这个经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事实上,我相信,将我在德国的经验带回来,能为历史悠久的《金融时报》提供新鲜的视角。 在德国的经历怎样改变了你对报纸的观点? 我因此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新闻究竟需要具备什么元素。比如说设计,也就是版式:你怎样凸显报纸的独特之处,才能让人不买别的报纸而去买你的。每天都需要想一遍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从零开始,从一张白纸开始,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 在(伦敦)做《金融时报》,你用不着每天都去想怎么去搞版式,但在做德文版时你自然就得每天都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就是写作风格,我们该怎样突出独特、简洁、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这种事在这边(伦敦)花不了多少时间,人们甚至都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但在德国就不一样了。 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才算是值得购买的好报纸?在德国这样一个报纸市场很小的地方,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让自己凸显出来。我们的成果是,现在《金融时报》德国版在德国的发行量是9万份,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同。尽管还没有盈利,但是我们已经缩短了盈利预期。 你的前任理查德·兰伯特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编辑,是他将《金融时报》带到了今天的这个地位。他是如此强劲、如此有影响力,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焦虑? 我没有这种感受。我非常感激他,因为我从他那里继承下了非常坚实的基业,他组织起一个了不起的团队,这里集聚的人才多得难以置信。理查德做了很多事情,招收和保留了大量人才,这些他都留给了我。我接任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说:“这个地方太棒了!”“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决策。”这样做是因为,当周遭一片破败,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时,你这时就得明白地告诉人们,你会解决好一切问题。 但在这之后,在我让每个人都确信我不会把这里弄得天翻地覆之后,我就开始去看哪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当然了(笑),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我寻找和发现了我可以加以改进的事情,然后就去做。接着我又把这些事情分成了几类,哪些已经做了,哪些尚待完成。 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网站。它需要有新的外观、新的设计,需要和报纸保持更进一步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编辑力量上要增加两者的融合度,同时要让人们在浏览网站时能够获得与阅读报纸相同的感受。我从报纸这边聘了一个人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她做得非常出色,重新设计了网站。2002年5月,我们还增加了收费浏览这一元素,现在我们已经有40000个交费用户,每个用户所付费用是每年100欧元。而直到2001年5月份结束时,我们的交费用户数还是零。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评论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往,我们有两个版叫做“评论与分析”,包括社论、分析、来信和一个每日专栏。社论、强有力的评述、谈论的问题都更多。 所以人们称“没有《金融时报》,就没有评论”? 的确如此。人们需要评论。在德国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这一点:在报业不发达的市场上,新闻就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