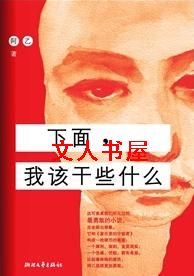钱是什么东西-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轻时别人给他说媳妇,人家问他家人多不多?孑然一身的他,拍拍胸脯说,村里都姓屠,是大户!他知道人家的意思是怕闺女嫁到小户家受气!还真给他骗来了媳妇。“屠大户”的大名不胫而走,人们多不知道他叫屠浩川,只知他叫“屠大户”! “屠大户”说,看着人家在水里撒欢儿眼气得不行!于是,下定决心,到大河里去,一个上午就学会了!用两只细腰葫芦绑在身上就行了。细腰葫芦可真是个学游泳的好物件!看着那东西一点点大,可往身上一绑,人往水里一跳,“嗖”就漂了起来。两手交替着向前刨,两只脚替换着往前蹬,人在水里箭一样蹿,熟练了摘掉葫芦就行了…… “屠大户”像说书般唾沫星子乱飞,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春才听不下去了,他的心早飞到波涛翻滚的大河里,他一边走着,想家里那两只细腰葫芦放在哪儿——他看见自己身上绑了细腰葫芦,在水里吃力地游着——他看见自己绑着细腰葫芦,在水里自在地游着——他看见自己摘掉了那象征初级的细腰葫芦,在水里奋力游着——他很快看见自己赤条条在水里轻松地游着,一会儿“狗刨”,一会儿仰泳,一会儿立泳——他看见自己在水里立泳着,左手举衣,右手执一柄钢钗,眼睛注视水里——一条红丢丢的鲤鱼向他身边游来,一摇三摆神气活现——右手不自觉地握紧了钗,并把右眼沿着钗柄瞄向鲤鱼——“噌”地出手,钢钗直刺过去,他下压钗柄上抬钗头,那鲤鱼扑楞扑楞在钗头扭动起来! 。。
钱是血红的印记(3)
回到家,翻箱倒柜找那两只细腰葫芦,最后在养驴的草屋中见到了它们,它们身上积满了黑不溜秋的灰尘,他心疼地拿到外边洗了又洗!父亲问他弄那东西干啥?他没好气地说玩呢,你别管!好像是父亲不让他会游泳!他又到处找绳子,他想,决不能用那种细小的尼龙绳,那东西结是结实,可勒得人生疼!最后,他找到了奶奶的绑腿带子——长三四尺、宽二三寸,用它们来绑细腰葫芦是绝好的! 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睡不着,一想到“屠大户”、细腰葫芦、绑腿带子、游泳、钗鱼中的任何词语,他就会沿着那思路徜徉而去…… 第二天,吃了早饭,他手拿宝贝似的细腰葫芦出发了,他选择大河边上的河汊子,河汊子看上去水也算很深了。他想,急什么呢?学好了再游大河也不迟!可是,就在他脱得只剩一条裤衩,拿起细腰葫芦和绑腿带子时他犯愁了——绑在哪儿呢?他开始后悔没听完“屠大户”的讲解。 绑在头上吧!他比划了一下,感到不合适!头是圆的,细腰葫芦也是圆的,而且是一大一小连着的两个圆球。再说了,要往头上绑,也要不了两只葫芦啊!决不会是绑在两只耳朵上!他的判断很正确! 接着,他试了试肚子上,两只细腰葫芦往肚皮上一放,拿着绑腿带子试着一绑,蹭得肚皮直痒痒,他嘿嘿嘿笑起来,葫芦就掉在水边上!他想,决不是在肚子上——如果在水里蹭得肚皮痒痒起来,那岂不坏了大事?他的判断依然正确! 肚子往下,短距离内显然没有合适地方! 他泄气地坐了下来,双手把玩着脚踝骨,看着被风吹皱的水面,他眼里一片空洞。这时,一只牛虻飞过来,悄然接近他,轻飘飘落在他右小腿下部,看准了一根血脉充足、血气旺盛的血管,狠狠把那支长而锋利的嘴扎进去,他明显感到一丝疼痛,一看是一只牛虻。心想,我正烦着呢,你还来捣乱!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把找不到合适的绑细腰葫芦地方的愤怒凝聚到手上,打得小腿都疼了——那只可恶的牛虻却唱着歌儿飞走了! 他看看它扎针处,一粒小米粒大小的血珠子拱出来……他仔仔细细看它时,血珠子在眼里迅忽放大了,先是成了细腰葫芦,再就成了波涛翻卷的大河——对呀!就这个地方啊!再没有这么好的位置啦!他想,那牛虻该不是神仙派来的吧?是神仙派来告诉我怎么绑细腰葫芦的吧!? 他用绑腿带子先在细腰葫芦的细腰哪儿绑一圈,系一扣,然后,把它们分别绑在两边脚踝哪儿,站在水边双手撑腰,向着远处和水里分别看看,像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然后,他大叫一声“春才已经会游泳啦!”扑通一声就跳了下去…… 可是,跳下去他才感到坏了!! 头浮不起来,腿压不下去,他使劲往下压一下腿,头就露出水面吸一口气,脚还没有向下多少就在细腰葫芦的作用下又浮起来,头便又沉下去……他感到越来越不对劲,求生本能让他每次头出水面就大叫一声“救命啊!”那声音凄厉至极,传播辽远!大概喊了十来声,就什么也不知道啦! 等他叔伯二伯郭满囤把他从水里背出来时,他嘴里像压水井一样间歇地“滋滋”地喷着水,二伯在他肚皮上又是拍又是揉,弄了半天,他才迷迷糊糊醒来。 他叔伯二伯郭满囤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谁、谁、谁教你、你啊把细、细葫芦绑、绑、绑脚上,游、游、游泳哩?” “是、是、 屠大户。”春才缓了一口气说! “不、不、不中,走、去、去找他。”他叔伯二伯郭满囤说,“非、非梃、梃他不中,这害、害、害人哩这!”梃是名词,和杆同意。这里名词动用,是用棍状物打的意思。郭满囤说着拉起他就要走,去找“屠大户”算帐。他哭了,死活不去!因为人家只是说绑细腰葫芦学游泳,并没有说要他绑在脚踝上! “咱、咱 、咱们家和他家无冤无、无仇,他这是害人哩!”他二伯郭满囤说,“这、这、这不能和他、他、他算了!独、独门小户,还、还、还真赖、赖、赖啊孙!” 后来,两家还是在街上拉开了阵势,亲娘祖奶奶地对骂!“屠大户”是绝不会承认的,因为他的确没有这样教春才。春才家的人自然是不想罢休的,因为这要是真的,可真是在害春才!眼看着郭家的人就要对不服气的“屠大户”发起总攻了!这时,春才的一个本家出面说,“屠大户”的确没有那样教春才。不信你问问春才!”躲在一边的春才来到人前,说是路过时听“屠大户”说的! 郭家人一下子就泄了气! 对他叔伯二伯郭满囤来说,失去了一次展示郭家团结、显示郭家力量的机会!因为,郭家在村里不是大户也不算小户,跟高家斗他们不敢,可对付“屠大户”家却绰绰有余! 最让春才尴尬的是,他学游泳把细腰葫芦绑脚脖子上的故事,被那次吵架吵到了全村每个人耳朵里,还有心里!这让春才在感激郭满囤救命的同时,常有一些讨厌! 其实,“屠大户”没说错,细腰葫芦是可以用来学游泳,不过不能绑在脚脖子上,应该绑在膈肢窝!只要上身不下沉,再大水也淹不死人。实际上,只有春才和他二伯才知道,最可笑的是那水根本没有多深,只到春才胸口稍上一点!他庆幸因为郭满囤结巴、口板不利索,或是吵架时需要把危险说得严重点,郭满囤没有把这细节说出来,说出来非笑掉人家大牙不可! 。 想看书来
钱是血红的印记(4)
春才一走神就走这么远,郭满囤和屠大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等春才嘿嘿笑出声时,弄得他们两个都莫名其妙了,“笑什么呢?春才。”屠大户问。 “不笑啥,”春才说,“我觉得高兴旺的‘宝葫芦’很好玩。”春才听们俩也聊不出什么新鲜话题,就先行告辞了,一是所有新情况,郭满囤会第一个告诉他,更何况他还有事,他得按郭满囤给他出的注意,去赶紧抓落实。要不然就没办法实现梦想了。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春才害了郭旗、郭升,倒不如说是郭满囤害了两个儿子。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村里像开了锅一样,人们到处在议论一件事,不知是谁在村里大街小巷撒了很多传单,传单上写得像诗。每个传单都半张稿纸大小,打印机印出来的,字迹清晰工整。 村长兴成,实在不行; 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河滩赔款,据为己有; 百姓心血,喝着嫌腥; 带头破坏,计划生育; 儿生四胎,照样分地; 经常出差,实是旅游; 厮混银花,万明不吭!不敢吭! 传单把村里搅得像开了锅一样,把高兴成私分地款、儿子超生、公款旅游,私通万明媳妇银花等事情全写了进去。吃早饭时,人们听说不仅是本村,而且乡政府和全乡各村都发现了传单。春才早上放羊回来时,听到满街的人都在议论,在心里不经意地笑笑,赶着羊回家了。 他心里越来越有数了,他委托郭旗、郭升俩去做工作,基本上全部郭家人,和相当一部分杂姓人都表态支持春才当村长。春才交代那哥俩,给本家人说时,主要强调这么多年受高家压迫,郭家也应该有个人当当领导了。给其他杂姓做工作时则要强调,春才放羊出身,还当过一段警察,家里有当大官的亲戚可以帮忙。总之,要根据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说话,譬如,到万家做工作就得拐弯抹角把万明媳妇银花和高兴成的事点到,但又不能说得太明,尤其是直接做万明的工作时决不能这么说,因为万###里以为别人不知道呢!你要一说他会感到很抓脸。直来直去地骂高兴成就行了。更重要的是他让郭旗、郭升有意识放出春才是全村首富的风儿,因为富了所以就不用沾群众便宜了。别人问,春才有多少钱?他们说弄不清楚,反正很多钱,比村里还有钱。别人问他从哪里弄的钱?他们就说谁知道呢!反正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 为了准确无误,他们买了个小本子,把做过工作的人家记在一起,算出自己能拿到多少票。然后,把高兴成的铁票源一家家列出来,就可以算出他的大体票数。算来算去就算得挺失望,因为怎么算也比高兴成少三十来票。高家本身就三百五十来口人,有投票资格的大约二百人,高家人中不投高兴成票的大约有三四家,不到二十个人。而他的儿女亲家加上高兴旺的儿女亲家刚好可以把这个缺补上。他的票主要是郭家、屠家、万家等,共三百二十来人,有投票资格的一百八十来人。要想达到高兴成的二百票,要么去把高家的那几家挖来,要么就得去把剩下的三四家比屠家还小的小户挖来。要想赢得选举,就得把剩下的票都拉来。春才想,高家那几家不好挖,别看平时他们内部斗得像狗争骨头,关键时刻对外又团结得铁板一块。那几家小户人家就不用说了,小户人家一般都对大户采取惹不起,怕得起,怕不起,躲得起的战术,同时,一个重要生存原则是扶竹竿,不扶井绳。谁家势力越大,就越是扶着谁。这事弄得春才挺难受!要不是后来又请郭满囤策划,又让屠大户出面运作,春才都有点儿泄气了。虽然,乡里从稳定局势出发,逼着高兴成退了那笔钱,对外说是因为村里有事挪用了,没有来得及上账,把时代久远的糊涂账永远地糊涂了下去。维持原来班子不动。这让春才有点儿不舒服。可心里七上八下的春才,还是时不时就找到点儿当村长的感觉来。 终于,到了选举那天! 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吃了清早饭,人们开始三三两两走向会场。 早上,书记和村长已经在“大话”里“是不是”、“对不对”半天了,大话是指村里的大喇叭,不知道是指那玩意儿声音洪亮,还是指说话人吹牛厉害,也或兼而有之。总之,村里大喇叭一响,就有人说“大话”又响了,看来村长心情不错,村长心情不好时“大话”是决不会响的。前一段,大字报事件发生后,个把月“大话”都没响。村长心情一好,就义务为群众放戏曲,什么《朝阳沟》啊、《铡美案》啊,也还放流行歌曲呢!别看一大把年纪了,很爱听时髦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心雨》、《迟来的爱》……不过,也有人说那是放给银花听的。甚至,有人总结说,只要头天晚上村长弄了银花,第二天早上肯定放流行歌曲。有人进一步说,那歌是老牛吃嫩草时两个狗男女对唱的,他就听银花常哼那几首歌。另一个说,你去球吧,大口喘气还喘不过呢,还对歌?对球呢!弄完了抱着银花说说还差不多。另外一个说,我听村长说那——什么——啥——男人四十才学坏,怀里抱着下一代,嘴里唱着迟来的爱。那个说,为这事儿他儿媳妇没少骂他老不要脸呢!那一个说,他儿媳妇骂他是因为他对她动手动脚。其实,他唱歌挺好呢!那个说,去球吧你,鬼哭不像鬼哭,狼嚎不似狼嚎的,有心脏病的一听,弄不好非心肌梗死不可……总之,早上村长不但讲了“啊、啊、那个、对不对。” 还放了流行


![[综漫]为什么喜欢你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5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