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底斯遗书-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书名:冈底斯遗书
作者:陈庆港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庆港,摄影家、作家。1966年生,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影系,曾就职于多家媒体,曾为《杭州日报》首席记者。目前供职于《浙江日报》。代表作《走出北川》获得52届荷赛突发类新闻一等奖。曾出版《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丽嘉则拉》《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陌生地带》等。
内容简介:
那是一次逼近天堂,逼近死亡的旅程。那次旅程,让我懂得死亡不是终极,今生今世只是你的一部分。明白生命是个奇迹,它与万物相连,没有独立的存活,一切都与天有关、与地有关、与山有关、与水有关、与云有关、与风有关、与雨有关、与草有关、与树有关、与羊有关、与狼有关与善有关、与恶有关与你有关、与我有关明白每个生命都是另一个生命的神灵﹩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书摘正文
最后一天
死者
走进阳光中,竟毫无觉察它与平日的不同,更没预感到一段远逝二十年的人生往事,此刻已掉头,正朝我夺路而来。其实那件不幸的事,早在昨天黎明时分就已发生,然而令人不安的消息却要等我接到那个即将响起的电话后才能知道。
打开车门那一刹那,似有一盆硫酸从里面泼出。一股热辣浸透全身。往车里坐,如同往炉膛里钻。屁股落到座椅上,像摊在煎锅里,先是一阵灼痛,接着有一条滚烫的蛇,在两股间钻游,并逐渐往空虚处探入那个抓不着挠不得的痛痒处,顿时生出一阵诡异的惬意。就在几天前那个同样炎热的中午,我正和此时一样,屁股在座椅上不停地“掂锅”,蓦地灵光乍现:如此高温刺激,是否会对痔疮有疗效?随即给一位开门诊的朋友拨打了电话。然而朋友支支吾吾了半天,并没给我一个明白答复。刚才,我不得已登门去找他,座椅的高温,终于让痔痛变得异常难忍。来到朋友的门诊前,我看到那里新添了一个巨幅灯箱广告,灯箱上有四个特别显眼的红色大字:“祖传绝痔”。“祖传绝痔”前的毒日下,摆着一溜椅子,朋友在汗流浃背地忙碌,他的汗珠滴在椅面上,滋滋地化作了缕缕白气。一群患者推推搡搡的在排队,他们一个个迫不及待地想坐到那一溜椅子上,希望能早点得到我朋友的治疗。看见我,朋友掰开拽住他的好几只手,迎了过来。他一手擦着额头的汗,一手扯起前襟扇着风,说:“刚刚推出的新项目,想不到一下子来这么多病人。”他扭头望了下吵吵嚷嚷的病人,然后略带几分羞涩地对我说:“这可有你很大功劳。”突然感到脸上一阵发烧,我急忙转身而逃。
第2节,
像是去赶乘“诺亚方舟”,车一辆顶着一辆,拼命往高架路上涌。这场景让我联想到昨晚电视上的一则新闻:一群抹香鲸,不顾一切地往海滩上冲。
太阳照在前边的车顶上,发出电弧光一样的亮。高架路像一块白炽化的金属板,轮胎口香糖一样在上面粘着,挪动一步都很难。
广播里,几个专家在分析一起杀人案。中间,主持人时不时插入广告,还有听众一次次打热线进来。
“怕她记住了车牌号,以后会来找麻烦,他就朝她举起了刀”
“他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在被撞者的胸口连捅八刀,这一行为是他习惯了弹奏12345671八个音阶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受流俗文化的影响,那瞬间他只是下意识做了个吉利数字选择”
急救车在右侧“哇呜哇呜”叫个不停,车顶上快速旋转的蓝灯闪闪烁烁,搅得人心神不宁。左一把方向,右一把方向,急救车一直试图从前面的两车之间钻过去,但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所有的车都抽风般一阵一阵往前涌。谁也不让谁。
“没有预谋,没有计划,这不是直接发生的故意杀人,纯属偶然”
“有人说地球变暖主要是因为牛羊放屁造成的,老子算是找到今天这般炎热的缘由了,敢情是你们几个在这儿侃大山”
突然间专家和听众就气候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大大超出了主持人预料。广播里有些混乱。电话铃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
我似乎隐隐预感到这个电话非同一般,但这丝微弱的预感转瞬即被更为现实的判断赶开。看了下时间:两点五十九。离开庭仅剩一分钟。我毫不犹豫地认定:电话是律师打来。
不接听。
主持人连续插播了两次广告,才终于将双方情绪稳定下来,并成功地把话题从无聊的气候问题上转移开。广播里嘶哑的争论声,再加上一阵阵尖锐的电话铃声,以及急救车连绵不绝的哀鸣声,使这个灼热午后令人厌恶,不堪忍受。
关掉收音机。
电话仍在响个不停。
在路上!我在心里回着律师的电话。即使不在这条路上,那么我也一定在通往这条路的另一条路上!这座城市,任何一条看似简单的道路,其实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你在走完它之前,永远无法预测,它耗去的会是你的一天,还是你的一生。
第3节,
此时,高架路的另一侧,空空荡荡,泛着白光。路中心的隔离带,将一条路分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狭窄干涸的河滩,里面挤满了即将渴死的鱼虾鳖蟹。一边是浩淼宽阔的江流,它与狭窄干涸的河滩之间,隔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想到喜马拉雅山脉时,我笑了起来。笑是因为让我想起喜马拉雅山脉的,竟是那条小小的隔离带。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能挡住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它的北麓形成大片荒漠,然而它没有挡住道路。可路中心这条小小的隔离带,虽然它连一个屁也挡不住,但你却不能通过。
高架路的另一侧,已被牢牢封锁,每个出入口上,都笔直地站着警察。封路、开道,这种福利从来都是个别人享受,但有专家却大胆推测:根据最近一段时期封路、开道的频率,此项福利似乎正在逐级下放,并且极有可能至2018年,即会惠及科级领导听上去这像是扯淡,但因为之前他曾有过多次比这更荒诞的预测一一应验,所以他的这个预测,我没理由不信。。xjqi。
急救车仍在“哇呜哇呜”着一次次寻找机会往前挤。
电话仍在响个不停
“陈小鸟吗?”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个完全陌生的声音。与律师快速、尖刻的语调相比,这声音宽阔、深沉,让我的耳朵感觉很不适应。它在我耳膜上震荡时,竟让我想起了海子“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的诗句,就像是一只飞越了千年时光,穿过了茫茫天宇的鸟儿,最终停歇在我的耳畔。
虽然仅仅只是四个字,但它让我愣半天,一直回不过神来。对方也不急。
“陈小鸟吗?”过了一会,它再次在我耳旁响起。这声音不会和此时此刻的我有任何瓜葛。“陈小鸟”是我过去的名字,它代表的是我生命里那段已经远去了的日子。
“陈小鸟吗?”
“你是谁?”
“你就是陈小鸟吧?我是拉萨刑警,朗刚。”他的回答令我一惊。然而他接下来的这句话,则令我浑身打了个哆嗦:“昨天早上,在药王山下我们发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死者。”
“死者?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死者身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在拉萨一个身份不明的死者身上?”一方面我觉得这极其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又掩饰不住开始莫名的惊慌。
“那么他,他是谁?”我有点结结巴巴。
“我们想从你那得到答案。”拉萨刑警说。
第4节,
汗水预谋好了似的,它们在一秒内从身体的各部位同时冒出,弄得衣服湿淋淋的。这些年来,时不时冒出的种种意外,已将我变成为一只惊弓之鸟。
“我怎么知道一个万里之外的死人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想让这句话听起来轻松些,就特意在后面缀了声“嘿嘿”,但这装腔作势的笑,反而令自己真的像是心怀鬼胎。
“纸条上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名字。”
“还有谁?”
“还有朱卓尔、罗益、黄青、胡超、林百惠”
记忆深处,那个蛛网尘封的昏暗角落,掠起一阵旋风。尘埃落定后,一张张面孔逐渐清晰,映衬在他们身后的是白的雪山,绿的湖水,还有湛蓝湛蓝的天空时间常常只会让你和过往旧事多了回旋的距离,却绝难让你与它形同陌路。你可以把记忆折叠收起,藏到时间的深处,但它一旦被重新翻出,打开,你会发现,它竟然不曾有一点损减,簇新如昨。
“纸条不是纸条这个纸条是个合同”我的语调有些失控。
“是的,这确实是一份有你们共同签名合同。”
“那早就是个无效合同了。上面说得很清楚,它只对那次阿里之行起效用。那次阿里之行早在二十年前就结束了。”我很快控制住情绪。
“合同上不仅有签名,还有你们每个人的联系方式。”
“有什么都无效了。这份合同我早扔了。这件事早就结束了。”我嘴上虽这样说,但心里仍旧紧张,“更何况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每个人的生命和财物安全由他本人负责。白纸黑字你看得到的。”
“我们试着和合同上的每个人都联系过,”他对我“过期无效”的言论并不发表看法,继续说:“除了你,其他人都联系不上。”
“你不能因为找不到其他人,就把所有嫌疑都推给我一个人。”我怕事情越来越复杂。
“当年你留的是父母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一直没变过,只是前面增加了一位数。我们和你父母通了电话,从他们那得到了你现在的电话。”
都调查过我父母了!情况果然很复杂。大脑变成一团乱麻,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全没有听明白。直到听见他说“是想得到你的协助,请你配合我们弄明死者的身份”,我的思绪才又重新清晰起来。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将粘在胸口的T恤向外拉了拉。
第5节,
急救车还在东一头西一头地往前挤。
“难道死者会是在合同上签名的人?”像是突然醒悟了什么,我急忙问。
“这也正是我找你要弄明白的问题。”刑警朗刚说,“死者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我会尽快传一张死者照片给你,请你帮助辨认。”
急救车朝着高架的出口靠去,它的转向灯一闪一闪着。我跟着它。
路口直行,通往市中心,通往医院、法院,也通往我上班的那座黑色大厦。急救车向着市中心驶去。在禁止左转的标志牌下,我左转掉头,返回高架。其实每次置身这个路口,内心都会萌生这样的冲动,但又总是都忍住,并且告诫自己:你得往前走,你不可以扔下那一堆乱麻不管。
封锁高架路入口的警察示意我靠边停车。我从他身边快速地开了过去。后视镜里,我看到警察跟着车追了两步,然后站住,他用手抹了把脸上的汗,又把手上的汗狠狠甩在了地下
死者是谁?
“冈底斯攻略”
当我出现时,爸爸像被点了穴,站在那直愣愣看我,而妈妈在大吃一惊后,转身朝黄历跑去。她手指头蘸着口水,扒黄历上翻了好久,然后重新回来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离过年还有一百多天呢?!
“发生了什么事?”他俩眯起眼上下打量我,神情里饱含不安。
“没有任何事发生。”我柔声说。
鬼才信!在爸妈眼里,我是世上最忙的人。一年到头,只在过年时他们才能见到我。每次也都匆匆瞅一眼,就又分开。今天这是怎么了?他们继续追问。
“你们别乱想了。我只是想回来看看。”我一直压着的声音高了起来。
见我变得不耐烦,老两口相互瞅一眼,转身去为我做饭。
“我的那只箱子还在吗?”吃好了饭,我问爸妈。
“在!在!”妈妈说着,起身就往阁楼上走。
一切依然保持着我在家时的样子。褐色的木箱,在阁楼的一角静静放着。离家那会,我把自己的东西全都锁在了里边。
“没打开过,”妈妈用手在箱盖上掸了掸,“我只是常上来看看,扫扫尘。”
阁楼上有股淡淡的霉味。推开屋顶那扇窗,一股浓浓的黄尘,夹着刺鼻的味道飘进来。妈妈赶忙又关上窗。她说:“这窗子不能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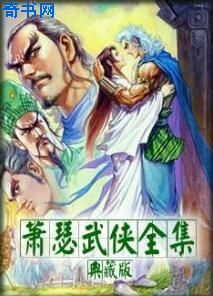

![[网王]书呆子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