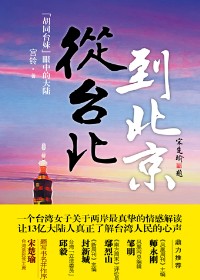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黑,仅有一团暗红灯光在移动……“咔嚓”、“咔嚓”地在进行。
此时汪宏杰已醒,悄悄地从他那边爬过来,我们二人调换了睡觉的位置,我把没有取血的左耳侧在上面佯装睡着。过了一会两个取血的医务人员从东头绕到汪宏杰原来睡的位置,一个医务人员推了推我,“你是**号?”,我仅用鼻子哼了哼装着熟睡。这时汪宏杰也帮着说:“他白天喜欢踢足球活动量大,晚上睡觉不容易叫醒,你们就抽吧。”二人如前泡制又是“咔嚓”一声在我左耳朵上猛扎了一下,殷红的鲜血再次被他们取走……
次日清晨,刚吃完早饭,一位身着戎装配戴少校军衔的军官(据说是县兵役局长)走到我的跟前说:“小郭!刚才你姐来说你母亲死的早,家里没什么人,你就不要去当兵了。”
当时我脑袋一蒙一片空白,顿时变得那么的呆滞和无奈。竟然没有向局长说明我的条件是完全合格的和陈述自己无力上学的困难,而是一言不发白白地把机会给放弃掉。这次待遇优厚被人们羡慕的空军应征入伍的机遇再一次被我姐给否决掉……,然而此时她已经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负担,对我上学接济已经感到是一种累赘和厌烦,但又怕给别人留下不愿照顾弟弟的口实,于是便做出一个口是心非“不舍得让我走”的决定。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兵役局返回学校,在走时竟然没有看到汪宏杰的踪影,他是否故意地回避我?我不得而知。
当时我年少单纯,不涉世故,不知这个世界上有时还会出现——假若“真”时,真亦“假”。真若“假”时,假亦“真”的怪诞现象。
没想到我无血吸虫病没有走成,而患有血吸虫病“借血”化验的竟能蒙混过关“光荣”地应征入伍了。古人秦琼为朋友能以两肋插刀,我可做不到,但我为同学却做到了两耳抽血。
两天后汪宏杰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在准备赴杭州某空军驻地报到的前一天来校告别,风光了一阵后离去。但他始终没有和我见面,可能是作假者心虚怕泄露隐讳,在入伍前最忌见知情的人。
后来听别的同学讲他到部队后,血吸虫病又被复查出来,按照以往惯例都要被退回。此次算他侥幸部队允许他就地治疗,以后当了一名地勤兵。二十年后我由新疆返亳,听同学说他后来转业到阜阳地区工作。
此事在当时和六零年我高中辍学,直到三年后我在亳县无法生活,户口迁出离开亳县我都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至今时过四十六年可谓久远,当时的事如同路人不期而遇,而后各自东西,早已淡忘……更无提它的必要。
而今追述为其秉笔直书,以便澄清事实真象。
将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往事如烟……
有时我在反思,扪心自问我做错了吗?我在过去的求学谋生道路上,为人处世总是与人为善,愿意替别人排忧解难,帮人办事,有时竟然过犹不及,甚至会出现像东郭先生怜悯不当的事情,以至于招来他人过河拆桥,自讨苦吃!
7月初,临近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当时县里动员人们向新疆移民(又名支边),亳县也进行了这项工作。多数是来自乡下贫困地农民和城里少数的无业市民,他们有的拖儿带女一家几口集中到我们学校,在此吃住,并发放了棉衣和棉被,高兴得他们屁颠屁颠的。我们班一个外号叫“大耳朵”的闫青云和三(4)班一个叫张济慈的两位同学也都报名去了新疆。而我此时穷困潦倒无力上学,本应报名支边还能落个“支边青年”的光荣的称谓。
然而我却没有如此,竟然苦苦地支撑着继续上学。直至后来在六零年的大饥荒中被迫辍学,生活拮据,境况窘迫,走投无路,千辛万苦地去盲流,最后还是流落到新疆……
一次次机遇错过,一个个机会丢掉,就是在我初中毕业时,还在报考学校的选择上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以至于贻害无穹,为此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9年夏天;对于我们四个班的两百多个初中毕业生来说是一次人生选择。多数城里和乡下贫困学生大都作出了符合自己的抉择——有的报考师范(中师),有的报考卫生、邮电、化工、电力、煤炭、农林、地质等中等技术专科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国家是补贴的,可以解决学生的生活费所以报考的人比较多。
当时决策最实惠,手段最聪明的还数年龄较大并有几分姿色的女生,她们生来就比男生具有生存的优势……有的年龄已有十八、九岁,大的已有二十岁,按照当时“男二十、女十八登记结婚正合法”的结婚年龄规定,她们已是条件成熟,完全可以择夫婚嫁了——她们为了解决上学的消费问题,就物色一个当时刚工作几年的中学教师。有的老师在城里或乡下虽有糟糠之妻,但“糟糠”毕竟多是土里土气的女子,哪能比得上城里时髦风流的“洋学生”。
还有的学校领导和中学教师,现在已经是知识、地位、工资均有增高,个人欲望也就随之增大了。于是一时间学校里就出现了当代的“陈世美”和“糟糠”之妻离婚,与城里自己的学生匆忙结婚的闹剧。
一个是贪恋姿色,一个是图有金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爹娘老子都管不了的事情。至于在求学期间学生不允许结婚的规定也就成为一张空文。
于是校园里出现了——学校团委书记、教务主任、政治老师、数学老师……纷纷寻找自己的学生为妻的怪事。
而作为学生的女生初中毕业还要继续深造,上学吃饭、穿衣消费,样样都要用钱,对于家境不好的便是天大的难题……找一个能够供养自己的男人,既能求学,又能解决钱的供给问题,同时还可以提前享受小家庭的幸福生活!这样“一举三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否则你就是一个不会算计的“傻子”这完全符合了“爱情”是上层建筑,“金钱”是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
当年我作为一个既无家又无亲人,连吃饭都要靠别人施舍的孤儿!本应该报考中等专科技术学校到毕业国家还会给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这样当时不仅可以继续求学,同时又减掉了别人对我的负担,的确是一个让人皆大欢喜的事情,到后来更不会为上学拖累别人而遭嫌弃!
然而当时我并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我上初中时,老人已相继去世,家中已没有人供养我上学——每月六元的伙食费除学校补助三元的助学金外,还要靠我姐给点接济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在初中毕业报考学校的问题上,我还要征求她的意见,这就是端谁的碗受谁的管的道理。但她却让我报考高中,准备以后考大学。
此措虽佳,但是却是一件“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确有些不切合实际。后来事实证明事与愿违,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
。。
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二)
第二节
1959年秋季开学,我进入亳县二中就读高中,当时的学习环境和初中时相比还是老样子,基本上没有挪窝——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教室还是那个教室,宿舍还是那个宿舍。只是教室、宿舍的门头上摘掉了三(3)班的牌子,换上了高一(3)班的牌子。班主任由物理老师胡德蔚换成了教语文的“秃顶”颜老师。
此时的二中经过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反右倾、全民皆兵的锻炼,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开学后,其它课程均有人任教,唯独高中的物理老师空缺,拖了一周后教务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打扫厕所,先前上海送来的大学生“右派”的杨嘉桂拉来上课。
一天下午,由校团委书记杨本初押着“右派”杨嘉桂向我们教室走来,行至门口,杨叫“杨”立在门外等候,团委书记径直地走上教室讲台,表情严肃,二目圆睁地向我们宣布:“今天我把右派分子杨嘉桂带来给你们上物理课,你们听他讲课是学课本上的知识,并要对他监视,如发现他在放毒,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对他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绝对不可留情。杨嘉桂!滚进来给学生们上课。”于是“右派”分子杨嘉桂就灰溜溜地“滚”上了讲台。他低头翻书,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开始讲课。他刚刚在厕所里劳动,身上沾染的屎尿散发的臭气在教室中飘溢……似乎他又在放“毒”。
他进教室全班同学既不起立,也不致意,坐在座位上“风雨不动安如山”。不仅听课还要随时监视“右派”分子是否放毒,若是发现“敌情”,就马上会有积极分子向他开火!
“羊”和“羊”(杨和杨)不一样。团委杨书记是革命的带头羊,而“右派”分子杨嘉桂是破坏革命的捣蛋羊,所以必须对他进行专政。
杨嘉桂给我们讲课,杨书记还放心不下,他站在窗外向里面窥视,隔着窗户静听了几分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才转身扬长而去。
杨书记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从乡下一个区里调来的青年团干部,其实他才上了几年小学对于高中物理什么是力学、杠杆原理、牛顿定律、自由落体、加速度……他根本也听不懂,只是当时出于革命的责任心和警惕性,才装模作样地听一听,如听“天书”似懂非懂地扫兴而去。
升入高中,课程增多、负担加重,我更不敢掉以轻心。此时我经济拮据,生活窘迫。因无钱购买书籍和订阅刊物,我几乎每个周末和星期天都要从城南穿过市区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和读杂志,以便积累知识和提高我的解题能力,竭尽全力克服困难,坚持到高中毕业。
五九年“中秋节”,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利用不上自习课的机会,从二中穿过城里大街赶往北门外的县图书馆阅览室去读书看报,并借阅些学习参考资料。
这是我自一九五六年秋季考上初中以来,因为贫穷经济困难,订不起杂志和参考书,几年来所采用的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途径。
晚上八点,我走进阅览室,里面已经坐满了读者,多数是上中学的学生,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看报,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到了晚上十一点半时阅览室只剩下我们三、五个学生,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说:“平时晚上十一点下班,但今天是星期六已延长了半个小时,现在时间到了请大家离开,改天再来。”我们只得放下手中的书报离开了图书馆。
走到北门口,此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快到散夜戏的时候,我准备回学校宿舍睡觉。突然听到东面街口,亳县饭店门前有人在拉二胡卖唱。我出于好奇便走了过去。
没想到昏暗的路灯下,在大门台阶上坐着一个头发、胡子老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旧尼子大衣非常邋遢的三十多岁男子,他面前地上摆着一个旧瓷缸,低头拉着二胡,嘴里唱着河南豫剧。他既不抬头看人,也不管别人耻笑,只顾自己认真地唱。二胡声,伴着他唱了一段马金凤的《西厢记》中“红娘”的唱腔:“樵楼上打四更霜露寒又凉……”
随后他又唱学唱了一段豫剧名角常香玉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唱完两段后,他从地上拿起茶缸要钱……
人群中,有的转身扬长而去,有的向茶缸里丢进一分两分的纸币或硬币,有的给了五分、一角。我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仅掏出了两分钱硬币,丢进他的缸子里。
此时,从街口的北边,走过来几个人,看样子是听完夜戏的戏迷,他们边走边谈论着戏的内容。打我们身旁经过,并随口说道:“今天右派又来这里卖唱了。”
“怎么他是个右派?”我感到很奇怪。
后来,又听了他的一段江苏民歌《月亮弯弯照九州》,便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一起离开了那里,向北门口走去。
在路上听那个老汉讲:“人要是倒了霉,就算是称了二斤盐巴也会生蛆。”
“大叔,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他说这个卖唱的姓张,两年前农业中专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粮食局工作。五七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弃他而去。加上经常被批斗弄得神经失常,从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没办法隔三叉五地会到街上去卖唱糊口,但是又怕被熟人看见,嫌丢人。所以每次都是赶在天黑以后才出来,这都是因为小知识分子死要面子的缘故。
走到北门口我们分手,此时街上灯光昏暗,路上行人稀少,已是夜深人静了。背后又传来了粮食局的“右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