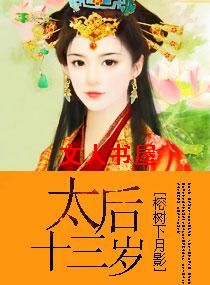鲁迅的最后十年-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4。“国家主权”与“民族主权”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家,一个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一个遭到外族侵略而面临着亡国危险的国家,再没有比利用民族的归属感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动员国民效忠于自己的政府的了。在这里,国家与民族被主权打通了,也不妨说,它们结合成了一个“复合主权”。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是:民族认同往往是通过国家来完成的,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或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鲁迅认同民族而拒斥国家,认同民族文化,却拒斥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他在一个特定语境中陷入了言说的困难。只要抨击政府和国家主权,很容易被看作对民族的伤害,因此,他常常被一些“爱国者”和“忏悔者”加上“汉奸”、“买办”、“破坏统一战线”等罪名。那些攻击他的人,正是利用了他作为一个言说者的尴尬地位,实际上是事实本身的矛盾性。但也正由于他不能回避可能招致的风险,所以必须进一步揭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代名词——的危险性和欺骗性。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只要有可能,国家和政权都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反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政府机器是庞大的,国家会利用手中的一切政治能源,如教育、传媒、组织效能,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向国民灌输应有的国家意识,要求国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而且经常地依靠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致国家整合的目的。如何可能阻拒焦虑不安的人群在共同抵御外侮的口号之下,团结到政府——“国防”的大旗之下呢?如何可能使他们在紧急的状况下,费力了解“国家享有内政的最高指导权”的涵义呢?如何可能向他们解释民族主义的根本效忠对象,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原版”,而是经过政府改写后的版本,即由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国家呢?这就需要在救亡中坚持启蒙,坚持常识普及,坚持“思想革命”。不然,从救亡到救亡,一切为了救亡,其结果只是救了政府。穆勒说:“在专制国家里,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所以,鲁迅必须对国家、民族、爱国主义、联合战线等概念做出新的解释和界定。
表面上看起来,鲁迅对“国防文学”的否定,以至同意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取代之,颇有点小题大做,实际上是在事关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上,给正统的一致性打进一个简易而有力的楔子。他有这样两段话,一段说:“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还有一段是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做人还是做奴隶?做谁的奴隶?做奴隶有没有内外或上下等级之分?这是关于国家、民族的核心问题。启蒙工作在救亡中进行所以变得特别困难,还因为:一、虽然政府是有意识、有技巧地全面进行着将国家问题转化为###的意识形态的制作工程,可是,民族情感这东西并不是政府直接制造出来的,而是现成的,非官方的,大众的,政府不过是挪用一下罢了。二、随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以国民大众为诉求对象的组织和势力毕竟愈来愈多,而政府的旨在加强国家统一和巩固现存秩序的理论、口号和命令,只要贴上“民族”“国防”一类标签,许多所谓的革命组织或群众团体便自动地代为推销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所以受到否决和围攻,就是因为其中的内容有碍“国防”的缘故。带根本性的问题被无聊的字面论争掩盖了,必要的批判性意见被“战友”看成“标新立异”,鲁迅的关于挑战国家主权而争取人权的思想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理解,更不用说“大众”了。然而,事实的无效性,并没有使他放弃他的自以为急迫的工作。萨伊德在说到知识分子的目的性时,曾经指出说:“虽然国家处于紧急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仍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忠实于大众的生存之战,非但不会使知识分子因此失去或者削弱其批判意识,而且,由于这类超越生存的问题,将使之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统治阶级,提供另类选择(这些另类选择在身边的主要战事中,经常被视为无关而被边缘化或置于不顾)。即使在被压迫者中,也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因此,知识分子的忠诚必须是不限于随同加入的集团的行列前进的。”鲁迅超越——实际上是一种决裂——了他所在的左翼集团,而孤身深入到了无人可及的境地。
在理论上,或者可以说在想像上,鲁迅以为革命主权可以对抗国家主权,但当革命从组织内部构成最高权力,从而对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造成损害时,他一样不能接受。今天的革命主权如何转变为明天的国家主权,这是鲁迅的预见性,也可以说是危机感。他反抗“元帅”、“工头”、“奴隶总管”,以及批判性阐释“国防文学”口号,其真正的意义,仍在于对个人性的最高价值的阐扬。
1935年12月,紧接着《理水》,在一个月内一连写了三个小说:《采薇》、《出关》、《起死》。从一个聚光点看,这几个小说都涉及到“统一”和“秩序”问题。《理水》除了文化学者、众多大员和群众代表的政治表演以外,最有意味的,是小说的结尾。因为禹治水成功,舜爷就下了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学习禹,不然就算是犯罪: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舜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
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称东方国家为“治水社会”,认为治水所需的权威、纪律和大协作,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鲁迅的小说叙述是一种巧合。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方式是非传统的,作风也很平实;待到回京以后,情况明显地起了变化。他遭到了新的“包围”,这种由个人到法令制度的变化极其微妙,既是一种起始,也是一种过渡,总之,国家将又恢复从前的样子了。
在《采薇》里,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因为不满国王“以臣弑君”,兄弟俩决计“不食周粟”,逃到华山里去采薇菜度日。他们的行为招致大批看客,包括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之类的非议。小丙君评论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阿金也几乎一式地问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可见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深入。两个坚守主义者听到这样一番“大一统”的论调以后,自觉无路可逃,最后只好一起饿死了事。
一切都属于国家,一切都可以“充公”,这是可怕的。《出关》里的老子,境遇十分奇特,既受优待,又被作贱,其实是颇受戏弄的。小说最后一段,写大家殷勤送走老子以后,关官关尹喜走进“公事房”,把老子的著作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恰好,他打发老子时,那些权当稿酬的饽饽,也一样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
《起死》以内容固有的矛盾性,写成了一个短剧。庄子表面上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比如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奴才也就是主人公,等等。可是,他能说不能行,本质上是一个秩序主义者。他身为“隐士”,却一心要见王者;以超脱自命,却备有警笛,遇到麻烦,即寻求官方庇护;斥人为“利己主义者”,自己倒是自私至极、虚伪透顶的反复小人。很明显,庄子是“第三种人”,以及平时并无连络而实精神相通的某类人物的讽刺性形象。
1935年以后,鲁迅为国家主权和革命主权问题所困扰。主权对人权的压迫,焦点在“统一战线”。所以,他坚决反抗那种试图利用主权,借“统一”之名而使任何个体尤其异端动弹不得的做法。他以为“统一”是有原则的,那就是“抗日”;在这一大的原则之下,则是民主化,众多团体与个体的平等兼容。“‘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他反对把“统一战线”当作国家主权的屏风,但也反对把它理解得过于狭窄,犹如“天罗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