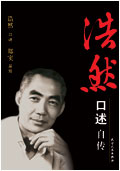��γ�������Դ�-��1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Ҫ�����������������֮�䣬�������ಡͻ�����������౾���Ͳ��ã������й��˴�С�����ھŴ��ǻ��У���Ȼ�ܳɹ���û�뵽���ȴ����Ժ�����£�����Ժ����Ȼ��������ҥ˵������Ҫ��������롣
����������һ�γ���ȥ�棬����ʣ����ҷ��ڿڴ����Ҳû�мɻ䣬�����������ҥ��˵����˽������˱����״������ܶ�ҥ�Զ�˵������ҩ��ɱ������ҥ��˵�Ǹ���������������أ���֮����ҥ�����𣬶���Ī���еġ�
����
���ް��ף�1��
������������һ������ң�������ɥ���Ǻܲ��õ����飬���ڹ���Ҳû��ʲô��Ҫ���飬������������ȥ��һ���顣�������Ҿ͵�����½����ıѧԱ������ࡣͨ����̨��ȥ���˶�������ѵ�࣬�����ı�ҵ���������ǽ�У���ľ��٣���ѵ������ѵ��Ļ����Ա��Ϊ���ĸ��¡������һ����ѵ����ר��Ϊ�й��˴���ģ��з���ѵ���γ̣�ʱ����̣�ֻ��ȥ�˽�������ָ�ν�������̨��ȥ�Ķ��Ǽ�λ�����٣��������������߿�Ԫ��
�����ص����ں��ҾͽӴ������ָ����ҵ��
�����ֹ���һ�꣬�������ң������굥����ʱ�䲻��̫���������ʧȥ��ͥϰ�ߣ�����л��ᣬ������ٻ顣����ʱ�պ���һ���е��ľ�Э���ٿ���ᣬ������Ҳ������֮�У��պ���̫̫�����������������ʹ�������Ů�������ף����μ���ᣬ�Ҿ������Ǹ���������ʶ���ģ�֮�����Ǿͼ������������������ձ������Ǵ�ѧ���ޣ���У�����������ϿΣ�������Ӣ���ϿΣ�������������һ�ҹ�˾�������������������Ǵ�ѧ�ϿΡ�
��������֮��Ҳ���������ʮ���꣬���밮��顣���ڸ��ս���֮ǰ�������Ѿ������ˡ����ҵ�״�����ԣ����Dz��ʺ��ڹ��ڽ�飬��Ϊ������ͺ����ܵ������������һ�㣬��Ҫ����������������ҵ����ѡ����¹��ĺ�ͬ���ֺܶ࣬��һһ���룬�����Ҿ;������ձ���顣�����ױ����֮������ȫͬ�⡣
�������밮�������ձ����������һ����������ʦ�ļ�ͥ���þ��л���ģ��������ò�����������ʿ�ֵļ�ͥ���ò�࣬�ݶ���Բ�ģ����ǵı��Ͷ��Ǵ�ʹ�ݵ�ְԱ�������ɷ�ִ����ʹ��֤���ˣ���������Ů����ȫ����֪���ġ���һ����Ů���⼮��ţʿ���dz����Ի����з������ǽ������Ů���������Ǵ�����������֮��ʹ�ݵ���ʮ������ְԱ���μ��˲�ᡣ���������֮�£�����ƽ���ȹ��˽�����
����������黹��һ����������ʱ�����Ѿ��Ǹ��൱��ҵ���ij��У����еĽ�������ʦ�ڼ�������ǰ��ҪԼ���á�������ʱ������𣬸�������ܲ��ܲ��ڶ�����飬��˵�������ԣ�����ʱ��ҪŲ������������ˡ������˵��������Ը���������һ�����������֮���������˵�������ڡ��л����������˵���������㵽�ձ���Ȼ����Ļ��ձ��˲������ġ�����Ҳ֪���Һ���������Ϊ�Ҵ���û�ж�����������ҽ�����˵�����ձ��Ǹ�������ᣬ�dz���ѧ�����㻹���ڵ������磬��˵һ�仰�����˾ͻ������˳�����������鶼Ҫ���Լ�ȥ��ͷ�����ο��ڶ���������˵һ�仰���ܳ��µġ��������������ң������ܲ��ܲ��ڽ������飬�ij�����ʦ�ļ�����л�����˵��������ҿ��Ժ���ʦ������������Ҳ���ܴ�Ӧ�㣬��Ҫ����ʦ����������ܾ�������˵�껰���Ҿ��뿪���ҵ�����ȥ��
����������ʦ���������Ҿٻ���ʱ����ʦ��ʾ�ȳϵĻ�ӭ����˵�������������Ƕ��ϵ۸�����������л����ԣ���һ��Ҫ�ڽ������Ұ��Ҳ�ǿ��Եġ����������Ǿ;�������ʦ������л���
��������ٰ�֮�����밮�����ձ������£������ձ�����ʤ�ż������չ⡢������������ձ�����һ���������ҵ�ʱ�䡣�ص�̨���;��д�ͳ����ʽ�������������˼ҷ�衣��������ǵĽ����̡�
�������״�С���й��������ֵ��ձ���ѧ�������Էdz���ֱ�����ʣ����˺�ϲ��������Ϊ�����������ٻ�������ͬ���ڸ�����ǰ������˵�ٻ�һ����
�����ġ��Ҷ�Т��
���������ʮһ�꣬Т����̨��������Т�ճ���������˵��һ�仰�������Ǽҵ�С�������������ջ����軵���˼Ҷ����ǽ��ҵ��ӵ����ǿ���һЩ������ӵܾͻ�����Ȩ����������Т���Ը���Сѧ��ҵ���ҾͰ����͵�����ȥ���飬����պø�������
����
���ް��ף�2��
Т�յ�������������������Ҳû���ر����Ӣ�ģ��ڼ������Ƭʱ���������С���������ö�Ӣ�ģ���ʱ����û�������IJ��֣�������Ҫ���������ͻᷭ���������������������У�Deer����field�������У�������ѧУ���dz��á�ѧУҪ���⼮ѧ��ÿ�������Լ��ı�����д�Ÿ���ĸ�����ַ�ʽ������ѧ�������Լ���ĸ�����ģ������൱������
����������������ʱ����һ��###��������������Ϊ���ʣ��������в���պ�Լ�������������������ӾͶ���У��������һ������ͬ�࣬һ��������һ�࣬��Т���Ǻ����ѣ����Ͼ������ĸ�����ͬʱ����Т�ա�Т���Լ�������������£����Һ�������¼�Ҳû�з�����
����Т�ո��б�ҵ������������ŷ�����У���Ϊ������û�뵽��������ʱȥ�������Ŵ�ѧ����ǰ���Ƕ���֪������Уԭ����ʥ����ǰ�Ű�����Ҳ����һλ���Ѱ�æ����һֱû����Ϣ�����Ƿdz��ż����������ʮ���¶�ʮ���գ��ҵ����Ѿʹ�绰����������Т����β�����ȡ�����ҿ��Բ��ֻ��������ԡ����Ǹ��˵ò����ˣ�ԭ�����ڶ�ʮ�������ϳ��������ľƣ��ڶ�ʮ���վ�������ףТ�ս��������
����Т���ڽ��Ŵ�ѧ��ɣ��������Լ�����Ȥ��Ҳ�����Լ���ѡ��ƽ���ҹ�����һ�������ɿ�ϵ����ҵ��ķ�չ����dz��࣬���������⡢������Ա������Ա��ѡ���Էdz��ࡣ���ڽ��Ŵ�ѧ�������з�����ҵ������о����Ͷ���ȡ�ý��Ŵ�ѧ˶ʿѧλ��Mster����of����Laws����
����Т�������о������ֻص�����������ŦԼ�ݵ���ʦִ�ա�ŦԼ�ݵ���ʦִ�շdz��ѿ�����ʮ�ΰ˴�δ��¼ȡ�Ĵ������ڣ���������������̬���أ������ѧ���ٰ���ѡ��ҽ���Т������ŦԼ��ϰ���꣬��һλ����ʦ��һ��һѧϰ�������Ժ���ȥ���ԣ������һ����ȡ��������Ƿdz��ѵõģ���ΪӢ��������������ͬ��
������ȡ��ʦִ�պ�Т�վ���ŦԼ����ʦ���Ҹ���Т�գ������ں��ң����Һܡ������������̫�࣬��һ���кڰ�������������У����Ƿdz�Ϊ�ѵġ�������ѹ�����ڰ�ѹ�����ټ��Ͻ�Ǯѹ������Щ���Ǻܼ��ֵ����⣬�����ҽ��������ڹ���ʵϰ�����ٻع���Т�������������������ǰ�꣨��ʮһ�꣩������������̨�嵱��ʦ��������������ҿ�����̨�壬��ʱ�����������Ȼ���һ����ʵ����һ���ͣ�������ľ����µò���ȷ����Ҳ�����죬�ҵ�����Ҳ��ͽ����ˡ�
����Т���Ѿ���飬����һŮ�����꣨�����ʮ���꣩��������һ�ӡ�
�����顡��������txtС˵�ϴ�����
½����һʦ��1��
��һ���ַ�����
���������ʮ�������Ӧ�ս������Ҵ����쵽�������������Ǵ��������ν����ķɻ������������ְ��ҽ��������Ͻ����ַ�������ҹ���������Ͻ���¤���������ط����ߣ��ڶ���һ���絽��ijһվȥ�Ӳ�ǰ�����ӣ��Ҹ��źν���һ��ȥ��Ҳ�����Ӳ������һԱ��ҹ��һ����ӣ����������Ӵ��ţ�����ʵ�������Ӳ첿�Ӽ��Ͻ�����ʱ�����糿����ӣ��Ҿ�����֣�Ϊʲôһ���ʹ����أ�ԭ��ʦ��������Ҫ�ĵ�����Ÿ���Ӫ�ĵ�����Ӫ�����������������Ҫ��ɨ���������������ϲ���ʱҪ�������ϳ���Ӫ���ϳ����ٵ��ż��ϳ������ʦ���ϳ������������ʿ������Ҫһ����������𣡵ڶ����糿����ӿ�ʼ����������������ת�ɶ�����ǰף��ȵ����˰����ͷ�����Ѿ��������ν��������½�̨ȥ�����ӡ������ν�������Ϊʲô��Щʿ�����۾��ġ�����ʺ����ô�࣬�������룬����һ����Ӿ����������Ѿ��ĸ���ͷ�ˣ��۾����ܲ��죬���ǰ�ҹ��û˯��ҿ�ʼ����Ϊ��һ������ȥ�����������ַ�ʽ�����IJ��ӵ������Ƿ��ʺϡ�
���������Ҹ��źν���ȥ�Ӳ��������ѧУ���߷�У����Уλ��������������Ϊ����¡�����ƽ��һ����������һ�������Dz��Ӽ��ϣ��Ӳ��վ��̨�ϣ�ָ�ӹٱ�������������ı������Ǿ�����ȥ�ı������Ǹ�������ȥ�ģ���������С��ξ����Ȼ�����������������ʵ�������Ѳ��õ��������ҡ�ÿһƥ������һλ����ǣ�ţ������൱���õ�ϰ�ߣ�����������ǰ�滹Ҫ��һλ����ǣ�ţ�ʵ��û�е�����������ǰһ�����Ƚ�һ�����Ǵ�����λ�����˵���Ѿ������ˣ��������Ų���������ȥ������Ȼ�����ˣ���������ȴ�������ǵ���ȥ�ˣ������ڹⱳ���ϣ���ƥ��Ҳ�ܾ��ˣ���ǰ���������������Ҿ������ֱ��������ӣ��������ȥ������ͷ������ͷ������������������һš������Ϳ���ס�ˡ�Ȼ���ҷ������������°������źã������Ǵ����ã�Ȼ�������������ǰ��Ķ��顣��ʱ�����˶�������һ���亹�������Ұ�������ס�����Ƿ׳����ҵ�������������������ֶ��й����Ӷ��˽���һЩ��
�����β����ߺ����Ͻ�������ȥ����е�⣬����ҫһ�������������صľ�е���ñ�����ʱ�������ɹ���֮����褵�һ���¾��Ǵ���ȥ���ֿ⣬��ʾ����֮���㡣��ʱ���ܻ�Ȩ�ܸ�������ȥ�ģ���λ�ⳤ�����������������ǵĻ��£���һ���ڱ���У�����ھ�е������һ�ֵ��������ǹ������ǹ���ϣ�һ����֪�������û�ǹ������ǹ���Ͽɵ��ػ�ǹ�ã��������ɵ����ǹ�ã�������û�б�ʾ�������Ҿ�����λ�ⳤ���������泤��������ͦ��ǹ�ж��أ��������˰����ش���˵������Ű˽��ͨ��һͦ���ǹ������Ҳ��ֹ�˹���ұ㻳�ɵ��ʣ�����ֹ�ɣ�����˵�����ϳӣ��ϳӡ�����ôһ����е��泤�����㲻�ǹ������ģ�ҲӦ��֪����ţ���������˵���������ϳ�����ģ�����˵��������һ����֪�������ٱ�����������ҫ���ľ�е�⣬���ȴ���ҷ������IJ���ˮ������˶��ѡ�������Ҳ�뵽����ô�����ڱ���Уȥ�ֿܲ��أ�˵�������������ڱ��أ���Щ���ǹ��������ҵij���ӡ��
������������ξ�ų�
���������ʮ�����£������Ͻ������ҵ���һʦ�����ŵڶ�Ӫ��������һ�ŵ��ų����ص��ڳ�ˮ���ӵ�������Ҿʹ����ˮ������ֻ����һ���̸Ǿ���һ��ůˮƿ����ʱʦ���ɸ��ٴ����������ң����³�����Ҫ�������̸Ǿ����Ҿ��ò�����˼���ҵĽ�����Ҳ�Ǻ��صģ���ֻ��һ��С��ξ���˼�����У����ô���������ö��������������Ҫ���ҵ�ůˮƿ����˵���Լ��þͿ��ԣ�������Ҫ�������ش��Ҽ�������ȥ�������ôһ��һ��֮�£�ůˮƿ����һͷײ�ڻ��ϣ�����ˮƿ���ˮ����������������ůˮƿҲˤ���������ˡ��������ǿ��ֵ��
����
½����һʦ��2��
���˻�վ�������һ����������˵��֪��һ�㡣��Ҳ�������������һ���û�������˵����û�У����ҹ���һ��������˵����������̺�ӣ�û�й�ϵ�����������룺������ԡ�����˯���Dz��÷���ġ����Ǿ���������ʦ����������ʱʦ������ϳ�ޡ�;�о���һ��СϪ��Ϫ����һ��С�ţ�С������һ����Ů��ϴ�·���������һ����鳴��·���������������ʱ���պ���λ��Ů�������Ű�ɫ���·����������Ű�鳴���ȥ����һ�����������ܵ����ţ��������������λ��ŮҲ�ܵ����ţ�������·�������һ��������Ϊ���£���վ�����ˣ���λ���ٴ���Ҳ���ˤ�����¡��ҿ������Ų��ߣ�����Ϫ���Ѿ�û��ˮ��ֻ��ʪ���������ҾϿ����������ס�����Ұ�����������������������������Ժ��ҷ�����Щ������������Ϊ������������Щ�������˶���Ҳ�����̣�����鳶��£�����ս���������ڵ�������ô�죿��������Ҿ��úܸп��������ĵ�һʦ������õ��ˣ�����������ѵ���������⣬���ǡ��������������������̡��������ҵ���Ӫ��֮����������һƥ������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