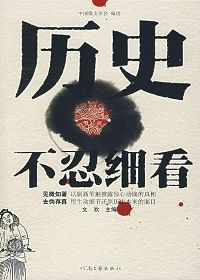访问历史-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序(1)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自序(2)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1)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
清晨先见到资中筠,原来陈乐民一早又上医院了。资中筠娓娓地回忆了清华园愉快的生活后,陈乐民才回来,略显疲倦,所以说得不多。陈乐民患有尿毒症,完全要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在医院里,他开玩笑说:“我的有效生命还剩下一半,星期一、三、五基本上干不了任何事情。”
墙上挂着陈乐民的书法,气韵清雅。空闲时,他会写书法,画国画,生病后手扎了针,对握笔有些影响。当年他在书画上练过“童子功”,后来忙于“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不大专注于书画丹青了。在维也纳时的顶头上司李一氓对他教益良多:“氓公兼通中西学问,雅好诗词,写得一手熔篆隶于一炉的‘李体字’,又是古文物收藏鉴赏家。我生性喜爱文墨,与这样的领导相处,追随左右,那种徜徉文事的氛围,自然如鱼得水,大大抵消了日常工作的枯燥乏味。”
房中还摆着资中筠的钢琴。她在高中毕业时开过一个独奏音乐会。进入清华园后,学校的音乐团体就来找她,大学生活是宿舍、图书馆、音乐室三点。有趣的是,在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工作的那几年,由于严守组织纪律,她很少沉浸在音乐世界里。半个世纪后旧地重游,目睹维也纳人古典音乐的普及程度,她有感而发:“从历史纵向而言,人家虽历经战乱,但没有经历过文化断裂。我国现在把‘高雅’、‘古典’与‘通俗’截然分开,并把前者与‘贵族’相联系,而所谓‘贵族’,其实就是昂贵的价格,为少数钱包鼓胀的人所享用,并不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贵族’。西方精致的文化开始也在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沙龙中传播,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日益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精致高雅的文化也就渗入百姓中。”
陈乐民和资中筠都钟爱读书。从他们的回忆中,我发现,早年两人各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资中筠感慨:“那时候泡图书馆太方便了,而且管理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很在行,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能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都对图书馆有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离图书馆太远,去不了,而且进去之后,手续太麻烦了。”
两人如今生活简单,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他们有一个喝下午茶的习惯,4点多钟喝红茶,吃点心。
1947年,资中筠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英语专业,1951年毕业。1949年,陈乐民考入燕京大学,两三个月后在校医普查身体时查出患有“肺结核”,回家休学,后入读中法大学一年,1950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法语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到1953年毕业,他像走马灯一样上了四个大学:燕大、中法、清华、北大。
李怀宇 你的父亲资耀华是金融家,著有《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
资中筠 我父亲原来是公费留日的,1900年出生,十七岁出去,在日本差不多待了十年,上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发表了一些在当时比较新的“如何办银行”的文章,被陈光甫看中了,陈光甫正在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找到我父亲,正好很谈得来,先让他做调研部主任,做各种调查。他们那个时候各种调查是非常细的,一块钱就可以立户,定位是为普通市民服务的。陈光甫是英美派,大概觉得日本留学的资历还不够,就把他派到美国著名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念了两年硕士班,但是叫他不要念学位,因为念学位就要为了学位而上许多不一定需要的课程,然后到美国银行去跟班学习,再到英国去考察。回来以后,陈光甫就让他到天津去开分行,所以我们全家从此就在天津。我小时候在天津上过一个学校叫耀华学校,刚巧跟我父亲的名字一样,只是巧合。这个学校非常好。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2)
李怀宇 小时候英文念得好吗?
资中筠 念得不好。抗战的时候,我们在英租界,开头还没有感觉到日本的影响。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势力就进来了,学校里逼着非得念日文,基本上不念英文了。但是大家都对日文反抗,不愿意念,上课的时候就捣乱,总之我们念了五年日文,现在我只记得字母(笑)。那时候是这样,谁要是把日文念好了,大家都看不起他。日文没有学好,英文底子也没有打好。
抗战胜利的时候,正好是我从高一到高二的那年暑假,还有两年要考大学了,我们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就拼命补,高二高三在课外我也请老师补英文。我的数学特别好,国文底子也还好,就是英文差。那时候我们考大学也是特别难的,特别是国立名牌大学。第一年我没有考上清华大学,所以上了燕京大学。那时候考大学是错开的,可以考好多学校。我脑子里就想着上清华,当时是西南联大三校联合招生。复员后的1946年、1947年这两年特别难考,因为原来只在内地招生,这时是全国招生,而规模没有扩大。国立大学是不用学费的,燕京大学的学费比较高,当然也有奖学金。
李怀宇 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以后,怎么去考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 上了燕京大学以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小,而且比较晚熟,不大善于交际,比较孤僻一点。我还是不甘心,第二年还是下决心要上清华,就去考转学,就是上了一年级以后,可以考清华的二年级。但是有一点,你要考清华的转学,就必须从燕京退学,才能拿到学历证明去报考,不能给自己留后路,不能脚踏两只船。后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退学了。那时候我在燕京已经成绩非常好,下学期可以得奖学金,免学费了。但是我不管,我去退学,学校教务处的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一再警告我:这样你就回不来了。我就不知道哪里来那么一股劲,非要退不可了。但是退了以后,我没有把握,万一真的考不上,我就什么学校也没有了。考完清华以后,我舅舅在上海,我又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结果那一年我三个学校都考上了,我就赶快回去上清华了。
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平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李怀宇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