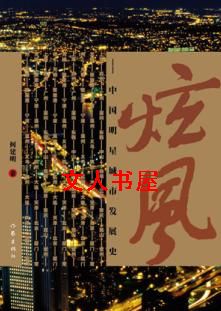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曲。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
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
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①
1902—1903 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这一体
系超出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 1908 年后宣传地方
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
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
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
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
的基础。②从 1924 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
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
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已经
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①
在定县 20 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
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 1922
① 《翟城村志》,第 44—47 页。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 146—165 页。查尔斯?海福德:
《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
②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转载于《翟城村志》,第 314—328 页。
① 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第 145—147 页,有关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绍。
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 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1930 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
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
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 60 个村庄和集市镇的
“实验区”。截至 1932 年,在定县开办的 440 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
管理的仅为 20 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②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
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
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
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
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
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
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
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
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
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
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①
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
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 1915 年到 1917
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
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
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 20 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
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
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
之后,于 1927 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
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
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
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
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 240 个村庄中组织
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
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
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
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
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 1930 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
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①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
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
②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 112 页。
① 同上书,第 67—69 页。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① 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 320 封信。
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 1931 年在邹平
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 1937
年超过 70 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
权,在 1933 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
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
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
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
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
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
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
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
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
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
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
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
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
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
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
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
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
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
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
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①
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
方组织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
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
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
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
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
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
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
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然而,尽管它
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
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 1929 年促成他与王鸿一
(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
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
①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 287—288 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第 75—76 页。上述关于邹平的说明
得益于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特别是第 238—278 页。
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
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
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
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
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
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 1930 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
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
在 1933 年被“土匪”暗杀。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
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难存在下
去。①
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
“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
改革的公开样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
的样板。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 CC 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
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
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
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
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
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
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
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
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 1936 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
“实验”地位旋即撤消。①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
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
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
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
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
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
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
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
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
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
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