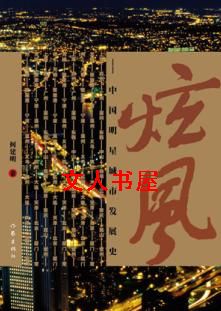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只有硬着头皮,拼着命去死读。陈鹤琴回忆:“全校五六百个学生中每天起得最早的总是算我了。功课虽考不着第一,起早的头名没有人敢来抢的。”②《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在圣约翰,陈鹤琴所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又是英文。与蕙兰不同,圣约翰的课程除国文外,理化算学历史等都是用英语讲授,课本也采用英文教材。此外,因为是中途插班,大学一年级上半学期课程没学过,他感到有些吃力。经过一个阶段适应环境,他依然像在蕙兰读书时那样的坚忍、勤奋与刻苦,终于跟上了课程进度。两周的试读总算通过,但拉丁文课程却让他吃尽了苦头。他写道:……只有一门功课倒苦死我了。什么功课呢?就是拉丁文。拉丁文字母也没有学过,先生就要我读拉丁书的下半本呢,况且拉丁文比英文难得多。所以,我一方面补读上半本,一方面赶读下半本。这位教拉丁文的先生又来得凶,他的名字叫巴顿(Barton)。他的声音怒貌,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筋中!他看见我回答不出,总是突着眼睛,伸着手指严厉地说道:“e on! e on!”意思就是“快点说出来!快点说出来!”不过巴顿待我还算好。他知道我没有读过上半本,常常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补习。②一年的功课须半年学完,陈鹤琴读得实在辛苦。到了学期结束,各门功课成绩下来,陈鹤琴每门都及格,惟有拉丁文一门考了59分,下一学期需要补考。可惜,因为转学,他把这个记录留了下来。
对于卜舫济校长,陈鹤琴一向怀有景仰之心。他写道:卜校长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数十年如一日,把梵王渡一个小学校变为一个国内著名的大学,五十余年来,桃李满中国。现今在外交界、政界、商界、学界服务的不知有多少。他对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宏大。卜校长不仅介绍西洋文化,而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宣扬圣道。他总是苦口婆心,劝人从善,仁爱精神,以身作则。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如此吗?这是我当初对于卜校长的景仰,并从景仰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想。《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然而,圣约翰校园中的另一番景象,却使得陈鹤琴对自己所怀有的这些景仰产生了怀疑。一方面,这所以培养教会领袖人才的高等学府,藉以激励、感染青年信奉耶稣并接受“基督化的品格”,并在将来走向社会时发挥“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作用;另一方面,在圣约翰校园中存在着种种不平等,令人产生出愤愤不平的情绪。在圣约翰,一般学生不注重中文学习,因此教中文教师的待遇很差。校中外国籍教师的待遇大大优于教西文的中国籍教师,而教西文的中国教师又较教国文的中国教师要好。教员所住的房子、所享受的薪金待遇分三个等级。国文教员住的是又旧又小的中国式房子,而外国教员住的则是又新又大的小洋楼。
圣约翰的学生中,不乏父母是洋行买办或官宦人家的阔少,平日里出入学校以黄包车和汽车代步,他们根本不把国文教师放在眼里。上国文课的时候,不是在底下读洋文功课,就是看小说。台上的国文教师像是低人一等,靠着桌,低着头,盯着书,讲课时连头也不敢抬一下。有的时候,卜校长走进教室查看,那些不听讲课的学生才收敛一会儿,装模作样把国文书摊开。更有甚者,这些学生给国文教师“捣乱”。有一天,上国文课时,几个顽皮的学生,在讲台上的桌子三只脚下都垫了砖头,另一只脚悬空。当国文教师讲课时,将两只手臂靠在桌子上,稍有前倾,桌子就从台上倒下来。被学生捉弄的国文教师只好赤红着脸,尴尬不已,而那些学生却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中国人欺侮中国人,学生捉弄先生,陈鹤琴对这种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愤不平。他写道:“这种怕外国人而欺侮中国教师的奴隶心理,我今日思之犹愤愤不平呢!”《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卜舫济,这位曾经令陈鹤琴崇拜、景仰的外国校长、虔诚的基督徒却在15年后的1925年6月,做了一桩令很多圣约翰校友感到蒙羞的事情。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全市人民###、罢市、罢课。6月3日清晨,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师生在校园中重新升起了被校方取走的中国国旗,闻声赶来的卜舫济恼羞成怒,当众从旗杆上强行扯下,引起了在场师生的一致抗议。人们气愤得跺脚、痛哭。据记载,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您是校长,我们应当尊重;但你是外国人,不应该抢夺我们中国人的国旗。”在卜舫济交还了国旗之后,人们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校方命令学生们到礼堂受训,但当校长和外国教授到场时,学生们并没有像平日一样起立欢迎。震怒之下的卜舫济校长立刻宣布学校停课,所有学生马上离校,学校设施全部关闭。在场学生中的553名本科与附中部学生当即宣誓永远与圣约翰脱离关系,以后再也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然后列队离开。孟宪承、钱基博、张振镛等17位中国籍教师以辞职方式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久,离开了圣约翰的师生们另组了光华大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圣约翰“六三事件”,6月3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光华大学的建校日。
三 北上京城(1)
宣统三年(1911)6月间,初夏时节。陈鹤琴的小哥鹤云从报纸上看到清华学堂在国内招考的消息。清华学堂是由用美国所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廷为选拔留学人才,在全国各省招考。按规定,凡年龄在15岁至18岁者皆可报名投考。初试由各省提学使主持,复试由学部尚书主持。这是清廷所举办的第三批选拔留美学生的考试。这时陈鹤琴已超过了19岁,经不住小哥和蕙兰的几位老同学的怂恿,他把年龄少报了一岁,终于报上了名。那时,浙江省报名的考生一共只有23人,主考官是提学使,姓袁,监考官是浙江巡抚增蕴。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算学。23名考生中取前十名,陈鹤琴位居第九,幸运地通过了初试。
过了几天,通过初试的考生每人领了路费20银元北上京城参加复试。杭州到北京相隔千里,路途遥远,通常要经上海转乘太古邮轮到天津上岸,再由京奉铁路乘火车到达北京正阳门。正阳门车站与天安门遥遥相对,始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称为“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这是陈鹤琴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从前他最远的地方只去过杭州。在蕙兰同学杨炳勋、姚天造的介绍下,陈鹤琴住进了京城里的仁和会馆准备应考。考试分两场,共进行一星期,头场有国文、英文、算学,第二场有史地、科学。按考试的规矩,如头场考试不及格,第二场考试就不能参加。参加考试者既有从各省保送的学生,也有直接在京城里报名的,一共一千多人,座位挨着座位,考场里人头攒动,可谓“百里挑一”。开考那天,陈鹤琴早早就出了门,因为有了在蕙兰和圣约翰打下的基础和参加初试的经验,他并不感到紧张。进入考场,站在那里,定了定神。主持考试的是曾任清廷驻美公使馆参赞、游美学生监督、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学部丞参上行走、游美学务处总办等职的周自齐。只见他高坐在台上,头戴大红顶子,身着绸缎马褂,端端正正,面色威严,桌边摆着一本报考学生的名册。负责唱名的官员高声把名字一个个唱了出来,主考官用大红银珠笔在名册上一个个做着标记。按点名的顺序,学生在座位上依次坐好,随着一声带有山东口音的命令,考试开始。
自1909年8月首次招考庚款留美学生,此次已是第三次招考,对考生要求,不仅通晓国文、英文,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曾受业于蕙兰和圣约翰,又生性活泼、开朗的陈鹤琴,并不对此感到担忧。头场考试下来,一共取了160名参加复试,陈鹤琴位列第82名;复试下来,取了100名,陈鹤琴位列42名。考试结束后,陈鹤琴在同学姚天造的引荐下,找到了本地有名的士绅范烟泰先生作保,终于被清华学堂录取,成为第三批庚款留学生。
清华学校地处京城西北,原为清漪园和圆明园等几处皇家园林遗址的一部分,相传是清道光皇帝赐予其五子的小五爷府。某日,朝廷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带着随从路经此地,抬头望见乳白色的西洋式拱形石门之上,镌刻着由军机大臣、中堂尚书那桐手书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园中古柏林阴,亭台楼榭,还有一条清澈的溪流穿园而过,宛若仙境。于是,范源濂上奏朝廷准予在此建校。这便是最初的清华学堂。
三 北上京城(2)
陈鹤琴写道:清华学校原是一个某王公的花园。有荷花池,有假山,有溶溶的清流,有空旷的操场,有四季不断的花草,有崭新巍峨的校舍。环境之美,无以复加。《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六七月的北京,正值盛夏,城里的气温很高,西郊就成了避暑的好地方。从城里通往海甸、颐和园、香炉峰有一条大路,要经过西直门。在这条路上,赶路的马车、驴车和挑担子、推小车的人们行色匆匆,有去避暑的达官贵人,也有进城卖菜、打零工的乡下农民;有去西山八大处、妙峰山朝奉的老人家,也有回娘家的新媳妇儿。由于距城里较远,清华的师生出校进城只能靠乘驴车、骑毛驴或步行。校园的旁边就是有“万园之园”之誉的圆明园。据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火燃烧至清华园外时渐渐熄灭,有人说是园内有乾隆亲书“水木清华”匾的灵显之功。
流经园内的溪流源于万泉庄引来的活水,而工字厅则是由一条彩绘木廊连成一体的前后两排房屋,形成工字状,因此得名。庚子赔款后,清廷外交部设“游美学务处”于此。北方晴朗的天气和阳光使初到京城的陈鹤琴豁然开朗,如沐清风。进校不到一个月,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在8月27日孔子诞辰日,全校师生,西籍教员除外,一律须去同方部“祭孔”,向孔圣人的牌位行跪拜礼,届时政府派大员前来监祭。同方部是清华校园北面一座简朴小楼,灰砖墙,红瓦坡顶,典型的欧式风格。“同方”二字取自《礼记?儒行》中“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句,有“志同道合者相聚”之意。这里也曾是清华园内最早的礼堂。祭孔之命使得曾受过洗礼的陈鹤琴和其他来自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拿不定主意。于是,他们找到了学校监督唐开森先生请示,唐先生待人十分诚恳、亲和,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很受师生们尊敬。此刻,唐先生也正左右为难,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身为学校监督,怎么可以不去参加祭孔呢?陈鹤琴和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不去参加。至于那天唐先生有无前往,不得而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封了大都督,革命军挥师北上,清朝廷摇摇欲坠,京城里乱作一团,人心惶惶。清华宣布停学,学校发给每位学生路费20元,学生们纷纷离校南返。起初,陈鹤琴对时局没想到过会有多么严重,仍独自留在宿舍里专心读书,后来,在同乡杨炳勋的一再催促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清华园,踏上了返乡之途。此时,水陆交通都很吃紧,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转乘太古邮轮南下。因为没买到舱位票,他们只好买了货舱票,睡在舱里的一口棺材旁边。船上甲板、船舱、通道上到处是逃难的人们,拥挤不堪,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陈鹤琴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的逃难。”《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经过几天海上航行,终于到了上海,然后从陆路回到杭州家中,陈鹤琴见到久违的母亲、小哥、小姐夫妇,全家团聚。在这次回家期间,他请母亲将20年来一直与他相依为命的辫子亲手剪掉,以作为自己旧的人生完结,身心轻松地走进新的天地。他写道:这条辫子是母亲赐给我的,是母亲每天早晨替我梳打的,现在我奉还给她。她老人家把它好好儿保存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不久,陈鹤琴告别家人去了上海,回到圣约翰继续学业。12月25日,隆裕皇太后诏告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这一天也是西方的圣诞节。在悠扬的圣诞歌声中,紫禁城的大门被重重关闭。次年,民国成立,清华登报重新开学,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陈鹤琴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