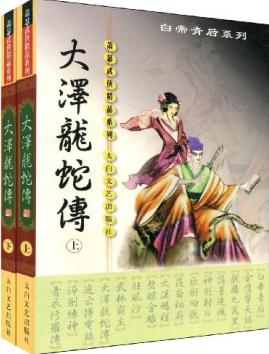浩然剑-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扇碧纱窗半开半合,隐约可见一双人影:端正向东而坐的是那眼神肃杀之人,对面一人身形修长,两颗小指大东珠掩映发间,正是他父亲介花弧。
介花弧虽然对他从来放任,他却也畏惧这个父亲。少年停住了脚,正听得他父亲开口:“。。。。。。当时对你手段,确是激烈了些,只是若非如此,以你个性,并无他法能将你留下。而今你是罗天堡中人,自然要换个礼数相待。”
那人冷然:“赌约中我只应过一生留在罗天堡,可未应过做罗天堡中人。”
介花弧笑道:“你留在罗天堡一辈子和你是罗天堡的人,有甚么区别?”
那人一怔,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几句话听得介兰亭莫名所以,心道这人不是罗天堡的贵客么?正寻思间,忽听一声门响,却是介花弧推门走了出来。
那人也起了身,却站在当地未动。
介花弧推门见了是他,也不吃惊,只微微一笑道:“来了很久了?也罢,想见谢先生,为何又不进去?”
介兰亭伸一下舌头,只觉当真甚么事都瞒不过自家父亲,却又忍不住好奇心,于是推门而入。
介花弧笑了笑,转身离去。
这一进门,便觉一阵暖风扑面而来,此刻已是初夏时分,室内却仍生了火,隐隐传来一阵草药气息。
介兰亭拉过一把椅子,径直坐下。此刻相距既近,他仔细端详谢苏样貌,见面前这人身形单薄,轮廓生得甚是细致,虽是神色委顿,一双眸子却如琉璃火一般,清郁夺人。
谢苏也自坐下,另取一只素陶杯,斟了一杯茶递过去,并未言语。
介兰亭也不接茶,一眼瞥到谢苏废掉的右手,心中又是一奇,看了对面的人问道:“你就是谢苏?”
谢苏以左手拿一块软布托了面前素梅陶壶,正自续水,听得这一句,他动作未停,点一点头。
“你是个残废,怎么杀的疾如星?”少年的声音再度响起。
谢苏抬首,面前少年俊美面容上目光烁烁,虽是单纯好奇所问,却也丝毫不曾顾及他人感受。
面前灯火忽然一黯,介兰亭眼前一花,一柄寒光闪耀的短剑已经架到了他颈上,竟是他腰间佩剑。不知怎样竟到了谢苏左手上。再看谢苏依然端坐在座位之上,实不知他方才如何动作。
“现在明白了么?”谢苏平淡道,他声音谙哑低沉,若非介兰亭就在他面前,实难相信这样一个人声音竟是如此。
介兰亭大惊,又想到白日里谢苏莫名消失,叫道:“邪术!”竟不管颈上剑刃,反手向谢苏持剑手腕抓去。
这一招正是介家世传的金丝缠腕手,动作巧妙迅捷,风声不起,介兰亭虽然年少,这一抓亦有七分神似。
谢苏却也暗自点了点头,却未避闪,直至介兰亭将触及他手腕之时,左腕轻挥,剑锋仍不离他颈项,同时无名指与小指微屈,风仪清逸。介兰亭这一抓力度不小,却在谢苏这一挥一带之下偏了方向,全数打到自家右臂上。疼痛之极。他“啊”的一声,惊疑不定。
“这不是邪术,是武功。”谢苏神情淡然,手腕一翻撤回短剑,递了过去:“剑不错,收好了。”
介兰亭茫然接剑,见谢苏虽是身形单薄,却是气质安然,宁定如山,心头没来由一跳。
他随父亲一起,也曾见过不少江湖高手。可是那些人中任谁和面前这人站在一处,单气度二字,已都被比了下去。
“难怪洛子宁说父亲特别看重他。”他心中暗想,却仍是不服,口中道:“是武功又怎样,我将来定可胜过你。”
谢苏却不再理他,静静地又为自己倒了一杯茶。
“洛子宁,洛子宁!”次日清晨,刚要出门办事的罗天堡总管又被拦在了半路。
“你昨天说的那个谢苏,他怎么杀的疾如星?”
洛子宁一愣,未想介兰亭对谢苏倒在意起来,但介花弧已然严令禁止堡内提到当时之事,只得斟酌一下言辞,答道:“谢先生在红牙河上以冰凌为刃,刺死了疾如星。”
这一句未免太过简单,反勾起介兰亭的好奇心。他追问道:“你说谢苏是父亲的贵客,可疾如星是父亲亲信的杀手,谢苏为什么要杀他?”
洛子宁自悔昨日多了一句口,道:“那是谢先生未入罗天堡之前的事情。”
介兰亭道:“他与罗天堡有仇么?”
洛子宁心道按堡主那等做法,就算原来没有现在也有了,不过依谢苏性子,真留在罗天堡也未可知。他心中转念,口中却道:“以前是有一些误会,不过现在早已冰释前嫌。”
介兰亭想到昨夜听到谢苏与自己父亲对话,半信半疑,又待追问。却闻身后一个熟悉声音,深沉中带一分淡薄笑意:“岂止疾如星,我不是也几乎败在他手里了么?”
二人一惊,同时回身,却见日光下一个修长身影站在那里,面上笑意吟吟。
“父亲!”
“堡主!”
…… ……
继续在堡中转着圈子,介兰亭一抬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静园门前。
方才介花弧将谢苏入堡的经过统说给了他,虽未说明迫谢苏入堡之前因后果,但事件本身已是惊心动魄,少年只听得手心里满是冷汗。
他抬眼看向洛子宁,洛子宁苦笑着摸一下颈项,当日金刚玉留下的疤痕赫然入目。
“父亲,有件事我不明白。”
“恩?”
“那日雨夜中,若谢苏和其他侍卫一般下去拿伞,父亲还能不能认出他?”
“多半不能,”罗天堡的堡主却也是微微苦笑,“那夜我全神贯注在下面诸人,又兼心思纷扰,他若不是举止有异,我不会去留意身后几个护卫。”
“那他为什么不去呢?”少年大是不解。
介花弧不答,反问道:“兰亭,若是你,你去不去?”
介兰亭答道:“去啊……不对,”他犹豫了一下,“我当时也未必能想到该下去拿伞。”
介花弧一笑:“正是如此,那个人太骄傲,他也想不到。就算他想得到,他也做不到一个侍卫该做的事情。”
少年哼了一声,心中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 ……
静园本有门户,介兰亭却不愿进,老样子翻墙而入,里面寂寂无人。他绕了几个弯,来到昨夜所至精舍前,那扇碧纱窗依然未合,他向里张望,见窗下一炉灵虚香青烟袅袅,谢苏着一袭月白长衫,正自执笔写字。
介兰亭一眼看过去,只觉谢苏写字的样子有甚么地方不对劲,又看了一会儿,忽然明白过来,叫道:“我知道你怎么杀掉疾如星,原来你是用左手的!”
谢苏早就发现介兰亭在窗下,听他在外面大呼小叫,也不理会,只起身来到窗前,“啪”的一声合上了窗子,几乎把介兰亭的鼻子夹住。
介兰亭一惊,正要发作,却见房门打开,谢苏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下次记得走门。”
少年想还一句口,一时却不知该说甚么,只得先走了进来。
此时谢苏那一张字已然写完,他凑过去看看,见字迹刚正清劲,并看不出是左手所书,心下又生钦佩,面上却仍不愿表露出来,道:“你左手剑很厉害,听说父亲也几乎败在你手里,但我将来一定能胜过你。”
这话他昨夜说过一次,此刻说来却又不同,神态郑重,便如立下誓言一般。
谢苏淡淡道:“胜过我也没甚么了得。”
“甚么?”
“我只会三式左手剑。”
“啊?!”
谢苏并没有说谎,他少年时一直用的是右手剑,直到二十岁时见到一个高手执一对淡青匕首,凌厉如电,心有所感,暗忖自己虽然习练左手剑已晚,但若只练数式,亦可有所成就。
浩然剑法共有三十六路,谢苏从中选出三式杀手,红牙河上杀疾如星,深夜雨中刺介花弧,正是这三式左手剑中的两式。
此时已是正午时分,有用人送上饭菜,谢苏道:“加一副碗筷,打一盆热水。”
介兰亭只道父亲要来,正想着要不要离开,东西已经送了上来。谢苏一指,道:“净一下手,坐下来吃饭吧。”
他举止自然,仿佛他面前对的不是介花弧之子、罗天堡少主,也不是昨夜那个出言不逊,又曾向他出手的少年,而是自己一个熟识晚辈。
介兰亭怔了一下,他母亲早逝,父亲对他放任,不甚关心。罗天堡其余人等则是对这位少主必恭必敬,便是这样一句寻常关怀言语,他也极少听到。
他指指自己,“你说的是我?”
谢苏奇道:“这里还有其他人么?”他起身检点笔墨,见介兰亭佩剑上的璎珞不知何时落在地上,便顺手拾起,递还给他。
介兰亭接过璎珞,道:“我甚么时候说过要留下来?”一面说,一面却过去洗手。
吃过了饭,谢苏铺了纸在书桌上继续写字,介兰亭心道这个人怎么写不厌呢?他坐在一边看了一会儿,午后的阳光温暖照到身上,竟是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这一觉直睡了一个多时辰,他伸个懒腰,见头上淡青幔帐晃动,身上却盖着他父亲的银狐披风,一时间神志有几分恍惚,抬眼却见谢苏坐在床边不远处,手中拿着书本,见他醒来,道:“醒了?茶刚沏好。”
一只素陶杯再次递了过来。
介兰亭起身下床,不由自主伸手接住。
从无一人对他这般平和相待。
随后的几日,静园内时常可见罗天堡少主的身影。介花弧向来不怎样拘管他,有时他在谢苏这里一混就是大半天。奇怪的是,这些时日介花弧竟也没有过来。
谢苏其实不大理他,依旧同平日一样读书写字,只是他在倒茶时,从来会为介兰亭推过一杯。
介兰亭再没拒绝过他的茶。
偶尔谢苏会亲自下厨,做一两个小菜,介兰亭第一次见到时吓了一跳,他从未见到哪一个江湖高手自己下厨,做的菜居然还很好吃。
谢苏再未显露过武功,他最常做的事是习字,介兰亭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写字写上一两个时辰,虽然谢苏的字确实漂亮。
一次谢苏说:“介兰亭,你写几个字看看。”
介兰亭未做犹疑,起笔便写,才写两个字谢苏便皱起了眉头,这字虽然不能称之为鬼画符,可较之鬼画符也强不到那里去,大概可以称之为人画符。
他叹口气:“介兰亭,你名字何等雅致,若能在书法上下些工夫,日后以右军笔法书兰亭集序,岂非也是逸事一桩?”
介兰亭虽不知“右军笔法”“兰亭集序”为何物,也知道谢苏这句话不是在夸他,不服道:“我将来是罗天堡之主,练字有甚么用!”
谢苏正色道:“正因你将来亦是一方之主,这等字迹,如何拿去见人!”
这句话说得甚是严厉,介兰亭也从未被人如此对待,冲口而出:“字写得好又怎样,你还不是一样被父亲抓住关在这里!”
谢苏脸色骤然一变,握着笔杆的指关节变得煞白。
介兰亭一语既出,也知自己说错了话,二人相处这些时日,谢苏虽然言语不多,其实对他照顾有加,在介兰亭心中地位早已分外不同。此刻他见谢苏神色不对,心中愈加后悔,却又说不出甚么。
这一日傍晚,介兰亭身边一个侍从慌张跑到静园,道:“谢先生,少主忽然发了高烧,口中还一直念着您的名字,先生能不能过去看看?”
谢苏怔了一下,便随着那侍从出了门。
三月来,这是他第一次走出静园。
居室里光线昏暗,介兰亭躺在床上,脸色绯红,双目紧闭。身上盖了厚厚一层被子,不言不动。
谢苏走近床前,看了一眼,问道:“他病了多久?”
“从中午起就这样了。”
中午,那时介兰亭刚和自己吵了架离开静园,谢苏心中思量。
那侍从道:“少主想是心中有事,生病也还记挂着先生。”说完向介兰亭处看了一眼。
床上的被子似乎动了一下。
那侍从又道:“先生就算心中不快,看在少主病着的份上……”一语未完,却被谢苏打断:“你家少主可有服药?”
“啊?”那侍从显是未料到有此一问,支吾道:“好象有……”
“那药不管用,我开个方子给你。”
那侍从似乎并未想到谢苏有此一说,又向床上看了一眼,道:“我……我去找纸笔。”
“不必。”谢苏淡然道:“我这方子简单的很,黄连二两,滚水煎服。现在就去,煎完马上让他喝下去。”
一语未了,却听床上有人叫道:“我可不要喝黄连水!”却是介兰亭掀开被子,已然坐了起来。
谢苏无声叹口气,走了过去。
“为什么装病?”
“因为你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你生气又不说出来,我那话是无心的,你对我好我知道!”
骄纵任性,性子别扭的罗天堡少主,终于大声喊了出来,眼神却转向一旁,不看谢苏。
谢苏一怔,这般既在意又率直不加掩饰的言语,从前只有一个人对他说过。
只是那个人对他说话的时候,一双清澄凤眼总是笔直看着他,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