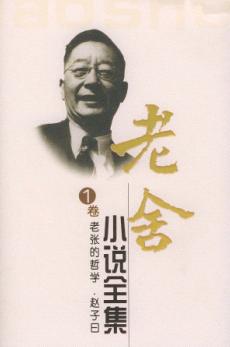黑杉霞-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边香风忽到,一袭黑纱拂上他双肩,他被这股力道轻轻一撞,又向后倒,忙伸臂死命撑住身体,这一撑,左肩伤处不禁发疼。好几句咒骂同时涌到口边,总算应双缇平日管教严厉,又不自觉缩了回去,只气得原无血色的脸上一阵泛红。
他狼狈不堪,旁边一人忍俊不禁,笑道:「殷家小兄弟,你好好跟我说一会儿话,不必急着动手。」灯烛下这人眼波盈盈,丰满身躯裹在夜空般的黑色罗衫里,斜倚几旁,正是方才挥袖将他打倒的冯宿雪。
在殷迟心中,天留门除了一个文玄绪外,余人虽无死罪,但也与无宁门大有仇冤,何况自己手上还带着他们九条人命。他见室中竟只有她与自己两人,大是奇怪,心想她为何犯险与我独处。冯宿雪历练比他多上不知多少,见他眼睛急转,已明其意,说道:「他们怕你蛮来,我却不怕。你得罪了我,还想拿到解药么?你朋友身中文玄绪口中毒针,那毒是慢性的,潜伏肌肉之中,逐步侵蚀,待到侵入脊骨两旁大穴,便要瘫痪。」殷迟心想:「我所料不错,天留门的毒药,还能是甚么好东西?听她语气,倒是愿意给解药,只不知道那九条人命怎么办,我何时才能去救康大哥?」顺口问道:「你怕我逃走,所以这室中还是放着少量昏睡麻药?」
冯宿雪道:「嗯,小兄弟见事明白。其实你也只知其一。这药物的学问可大了,迷倒你之时,需得先用少量诱导,见效方深,也于身子无损。其后你昏迷一天一夜,倘若径自醒来,而非逐步降低药量,不免也会功力大损。我们天留门人下药迷人,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此待遇。」殷迟道:「哼,原来你倒是对我另眼相待。」口中倔强,心中却不由得暗暗佩服。
冯宿雪眸子原本深邃,此时若有所思,更加深不可测,殷迟侧目凝视,怎么也看不出她内心想法。只听她说道:「你反应机灵,手下又狠,虽不是西旌中人,倒是倒是」殷迟脱口而出:「西旌是我仇人,莫要拿我与他们相比!」
冯宿雪一愕,说道:「是你仇人?」殷迟定一定神,道:「是。我一家不幸,全出西旌所赐,赤青两派都不是甚么好东西。我与西旌乃是死仇。你我不知你与西旌赤青两派有何干系,但我总之也伤了你门人,落在你手中,我甚么也不必瞒你。」
殷衡与江?当年追查黑杉令下落,虽遇见天留门人插手干涉,但其后两人一死一隐,钱六臂只由殷衡处隐隐得知文玄绪与天留门人勾结,见到天留门人围攻江殷二人,但这三人却谁也不知内情为何。仅知天留门既非赤派,也非青派。殷迟自然也对天留门动向一无所悉。
冯宿雪自见殷迟以来,始终见他一身蛮劲,年纪轻轻却爱逞英雄,在她看来,自是颇为幼稚。但方才他说到这几句话时,丝毫不带怒色,更无凄惨之情,却有成熟之态。她留上了神,问道:「你是一心一意,要报此仇?」殷迟淡淡地道:「是。」冯宿雪又问:「你今年多大了?」殷迟心想这也没甚么不能说,便道:「十四。」答了这两个字,凝望着冯宿雪双眼,神色奇怪,却不出声。
冯宿雪见他灿若天星的双眼忽阴忽晴,显是在对甚么大事犹疑不决,却听他忽又说道:「我到此地,除了为朋友求药,原本便是便是求艺。但一路分说不清,我已经伤了人,因此因此」便难以说下去了。
冯宿雪微笑道:「是你小兄弟先动手打伤人的哪。」她这一笑全无阴森狡诈之意,但话语中却不让步。只见笑靥在柔润双颊绽放,和暖融融。殷迟从未见过人们说这等话时,脸上能有如许笑容,心中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微微慌张,抗辩道:「你们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便毒死了我的座骑,一看见我,挥剑便刺,我又怎能容情?」
冯宿雪心知殷迟武功尚不足以收发自如,同时天留门隐情甚多,确然容不得外人入山滋扰。她轻轻「哼」了一声,表情却无丝毫不悦,随即低下了头沉吟,一边伸出手臂,取过几上烛剪,轻轻剪去过长的烛心。
殷迟见她手臂伸到自己身旁的小几上,黑色衣袖里露出浑圆皓腕,他生长边地,所见民族颇多,早在疑心这女子是胡汉混血。烛火之下,只瞧见她肤色极度白皙,手臂上几点小小褐斑,她身形虽丰满,手指却相当瘦长,怎么也不似汉人女子。殷迟心想:「姨婆终身不愿提起天留门这一支派所干何事,冯宿雪这只手不知杀过多少人?做过多少邪门勾当?」心中虽如此想,那只手臂搁在几上时,他心里却不知怎地,砰地一跳。
冯宿雪抬起头来,缓缓说道:「你手上带着九条人命,我是天留门主,这事如何了断,总要凭众意裁决才好。照理说,将你在那厅上凌迟,也就罢了,但是」殷迟左手在羊毛毯子下从未放松过自己的短剑,听得此言,全神戒备,冯宿雪续道:「还有一个方法,却不知你肯不肯试?」
殷迟听她一句不提画水剑谱之事,也不意外,说道:「你岂有容我拒绝之意?」
冯宿雪嘴角浅笑,轻轻摇头,道:「我确是不容你拒绝。但像你这样,身陷重围至今,只叫了我一声冯门主的人,我却也没见过。你跟我来。」说着一拨长发,站起了身,黑色长裳在殷迟身畔垂下。她这几下动作,殷迟微微闻到一股温馨香气,却不是麻药,也非上山途中的甚么毒药,心中又是砰的一跳,走下地来。那麻药作用尚存,脚步还颇感虚浮。
冯宿雪带着他穿过几道暗门,在曲折如蚁穴通道的走廊中前行。山壁上都点了绿焰灯,一入地道,方才斗室中烛火掩映的温暖气氛荡然无存。殷迟对机关构筑之学一无所知,钱六臂所精者只是戏法相关,他从未见过这样迷宫般的阵仗,而暗门关节又是以极轻质的金属所铸,发动间并不会震动山壁,这等巧技,不但在无宁门的庄子从未听闻,即使他自幼在无宁门诸人指导下,对王府、皇宫、门派地形背诵熟习,也未有印象。暗道:「若是他们不放我,我也逃不了。」
行进之间,殷迟隐隐听见前方有嘻笑奏乐之声,那声音愈走愈响,地道突然走到了尽头,冯宿雪却左拐一弯,消失不见。殷迟忙跟上去,原来地道在此处折成直角。一个左转,便到了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冯宿雪转过弯后便停在门边不动,殷迟险些撞上。冯宿雪微抬左臂,挡住了他身子,殷迟闻到那温馨气息正便在自己脸侧,心里又是一愣,忽然想起:「她这一抬手臂,倘若径以肘锤撞我身上穴道,岂不危险?此人心意未明,本领也必定十分了得,随时都可能杀我,我行走在敌人身旁,怎会如此大意?」
但眼前所见,?时令他忘却了心中疑惑。房内绿焰灯火通明,异香扑鼻,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个脸带微笑的天留门人,此外又有十多人正在纵歌起舞,急转不休,韵律有致,辨不出是何地舞蹈,似乎随兴而起,偶见散乱。舞者个个大汗淋漓,脸上却满是欢畅,也不闻丝毫气喘之象。墙角坐了四五个各持乐器的门人,神情也是这般喜悦不禁,乐声渐乱,已奏不成调,却不知为何仍甚协调。
殷迟入山一天一夜,除去昏迷之时,见到的天留门人总是面无表情,杀气腾腾,几曾想过他们也会如此松懈狂欢?绿焰之下,这数十人欢欣已极的表情,透着说不出的诡谲。他心想:「这几十个人都醉了?但酒醉之人哪有这样精力十足的?」他眼光一瞥,见奏乐者身旁躺着一男一女,正自互相靠近搂抱。殷迟脸上一热,移开目光,却见房内好几名男女门人早已成双成对地缠在一起,身上衣着虽仍整齐,但隔着衣衫摩娑的态势太过露骨,与衣衫尽除也无太大分别。
他自幼在一群叔伯中长大,出身正派的母亲应双缇严加管教,自不用说;无宁门一群叔伯尽管绝非谨严君子,移居黔西后也颇有浪荡事迹,但担心耽误殷迟练功,在他面前便尽量少提男女之事。殷迟自己,也从未对无宁门庄子左近的当地少女动过心。彷佛他生来便只要练功报仇,无欲无求。蓦地里见到了如此淫乐场景,惊愕反感之余,却觉身上越来越热。
忽然颈旁气息细细,冯宿雪凑过脸来,低声问道:「你觉得如何?」
殷迟正惊讶得手足无措,并不答话。冯宿雪又低声道:「出来说话。」转身回进了地道之中,走出二十余步,才停下来。
殷迟随之走出,临去前忍不住又望了房间两眼,只见狂舞中的门人有的彷佛抵受不住炎热,正在除衫,有几人传递着一个酒瓶子,急匆匆地往嘴里灌,不知里头究竟是酒是水。地上肉色隐隐,交缠中的男女忙不迭解衣撩裙。殷迟不敢再看,匆匆走到冯宿雪面前,努力收摄心神,沉声说道:「你让我看这个干么?」
冯宿雪见他慌乱后突然变得极为郑重,嘴角挑起,轻轻笑了几声,才道:「我想跟你商量件事,你若应承了,不但能拿到文玄绪毒针解药,更能享受你方才所见的人间至乐,那九条人命,也包在我身上一笔勾消,天留门人决不与你为难。这三件好处,你说怎么样?」
殷迟听见「人间至乐」四字,又觉那房中欢悦无涯的声音仍隐隐传入耳中,心想:「她给我这么大的好处,要我去做的事,就定然对我有极大坏处。她不是要我死,却会是甚么呢?」脑中忽地灵光一闪,也不及细思理路为何,顺口便说:「你天留门剑术高超,甚么西旌的人会杀不了,要我去杀?」
冯宿雪款摆身子,向他走近两步,注视着他道:「你的确聪明。我同时与西旌赤青两派为敌,但我不是要你杀一两个人,我是要你入我天留门下,学全了画水剑谱,替我冯宿雪办事。你敢不敢?」
此语大出殷迟意料,他一听到「学全了画水剑谱」,报仇的热念上涌,再听到冯宿雪相激之言,差点便要当场答应。忽听得那房中琴音渐促,铮的一声断响,却是有人奏乐之时琴弦断了,瞬即想起:「天留门人不知有甚么邪术,瞧那些人意志昏聩,狂舞不停,大庭广众之间解衣淫乐,绝非酒醉。」退了一步,问道:「你说人间至乐,便是刚刚所见那样么?那究竟是甚么?」
冯宿雪摇头道:「你未入我门,我不能说。」忽然举手挥灭了身旁山壁上一盏绿焰灯,两人脸上绿油油的光亮不见了,冯宿雪背着光亮,在暗影中轻叹了一口气,道:「殷迟,自从我见到你,始终见你神色抑郁,似乎胸中有许多未足之事,你年纪轻轻,何以如此伤怀?想是仇恨太重,割舍不下了。这世间多么苦,倘若能忘却那些愁苦,片刻贪欢,不是很好么?」
殷迟回想房内诸人神情,的确便像是了无挂碍,无拘无束地超脱凡俗,做尽清醒时所不能为之事。冯宿雪又道:「你入我门来,既能学艺报仇,又能享受到凡人没福气享的乐趣。再说,天留门人出手,哪有留情?爱怎么杀,便怎么杀,我瞧你也是个使情任性之人,你不想要这样的日子么?」
殷迟鼻中闻到她身上幽香阵阵,耳里听到的是房内的放浪之声,心中三分期待,三分羞愧,剩下的却是恐惧,只想:「那究竟是甚么滋味?那究竟是甚么滋味?房中那些人此时在想甚么?还是他们真的甚么也不用去想?我若学成画水剑,又有天留门诸般毒药作为后盾,到那时横行江湖,想要做甚么,便做甚么,日子是不是便快活得多?」身子微颤,只想马上体会这般快意人生。
冯宿雪不再劝说,静待他答话,却又向前走了一步。殷迟背后的绿焰灯映在她脸上,灯色虽然黯淡奇特,在殷迟眼中看来,却只留意到她的丰唇泛着诱人光泽。
他闭上眼睛不看她,又想:「这当中定有阴谋。有阴谋又如何?她说的不正是我想要的?」
正在他彷徨无措,几番要答应入门之际,房中乐舞笑闹声已渐渐低了下去,只剩下男女欢好之音,断断续续,竟变得难堪刺耳。殷迟猛然想起:「他们终究要从这极乐之境中醒来。」
一想到此,便自然想下去:「醒来之后,难道不会思念那样的快乐?这样人生便更苦了,只有身中那极乐之术的时候,才能有一晌的解脱。便如去过一趟仙界,哪里还会想回到人间?到那地步,除了一死以外,又怎么过下去?天留门人对冯宿雪死心塌地,难道是为了她这独门秘术么?」眼前忽然出现文玄绪在日光下怪病发作的模样,「他那怪样,不知与这邪术有没关系。像他那样又有甚么好?」
他睁开眼睛,又看见冯宿雪那慵懒的神态,心头仍在怦怦乱跳,说道:「一件事换一件事。我为自己也为你杀尽西旌赤派青派,但你须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