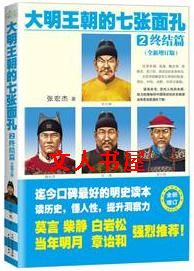大明1937-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盏雪亮的车灯照耀下,十几个穿着深色海军制服的女孩子恐惧、不知所措地挤在一起,试图躲避着周围无数条目光。还有一个躺在地上的担架上。向小强悄悄数了一下,连同躺在担架上的,一共是十二个人。
然后,她们被喝令站成一排。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慢慢地从她们面前走过,打量了每一个人,最后在一个女孩面前停下,指了指她。
立刻从旁边过来一个大兵,抓着她的胳膊,在一片惊叫声中把她拖了出来。
“喂,不会吧……”小强张大嘴巴,几乎要绝倒,“不会这么猴急吧,连审问也不用,这就开始挑选啦?这……这我可怎么救啊?”
……
“哎哎哎,干什么干什么,侬啊晓得啥子是教养啊?”
军官扶了扶金丝眼镜,出言教训那个出手拉人的大兵。
这军官有六十多岁,头发花白,地道地苏沪口音。长得慈眉善目,干瘦干瘦的,弓腰驼背,夹着个公文包。要不是这身军服和肩膀上的少校军衔,那就十足一个教书先生。
“嗻。”大兵低下头,讪讪地退到一旁,周围一阵小声哄笑。
“偶跟侬岗(讲),偶叫侬请人侬就好好请,不要那么拉,哎,那么拉不好。人家姑娘都是通情达理地。哎,以后跟人家好好岗(讲),晓得不啦?”
周围又是一阵窃笑,那大兵忍住笑,又说了一声:
“嗻。”
“嗯。偶来看一看,”老少校又仔细打量一下那个女孩,怜爱地摇摇头,“老可惜了哦,啧啧,尬水灵个小囜,当兵打仗,侬爸爸妈妈不心疼吗?”
那女孩揉着胳膊,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瞥了他一眼,没理他。
“嗯,好,好,”老少校点点头,慈祥地问,“偶来问侬,侬啊是艇长?”
“嗯!”女孩点点头。
“嗯,好,好,”老少校又点点头,叹了口气道,“小小个年纪,不懂事啊,嗯,到阿拉这里就没事了,待会问侬啥子,侬好好岗(讲),侬再把那个保险柜给开一开,偶跟上面岗(讲)一岗(讲),好好放侬回家。哎,尬小个年纪,家里面爸爸妈妈要担心死喽……”
“你为什么要当汉奸?”
女孩突然张嘴问道。
“啊?”老少校昏老的眼中射出一丝光芒,“侬岗啥?”
“你明明是江南口音,为什么要跑到北边来当汉奸?”
“嗯,好,好,”老少校又点点头,“好,好,到了这里就没事了……待会问侬啥子,侬好好岗(讲)……老可惜了哦,家里面爸爸妈妈要担心死了……”
他打了个手势,旁边的卫兵立刻围上来,用刺刀顶着她们,分别上了两辆卡车。卡车发动。
“向左向右——转,跑步——走!”
两派卫兵枪上肩,齐刷刷地转身,护着卡车两侧跑步而去。
……
“我靠……这帮狗日的可算走了……”
人散了以后,船台又变得一片漆黑。向小强艰难地爬上船台,扑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连打哆嗦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辈子没这么受罪过。第一件事,找衣服穿。第二件事,找东西吃。
寒风吹来,向小强一阵猛烈地咳嗽,江水在舰体和船台之间“啪啪”地拍着。
真他妈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可是,”他近乎垂死地抬起头,望着这片黑乎乎、死气沉沉地大镇子,“衣服到哪里找,饭又到哪里吃呢?”
第5章 粘杆处
“噗通!”
一个踉跄,女孩被猛地推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摔倒在地。
屋里一片漆黑。地上好象是木地板,上着蜡,很滑。
她惊魂未定地爬起来,摸到墙边,双臂放在胸前,防卫着。
“啪”,灯被拉亮了。
门口出现一个年轻军官,鹰钩鼻子,满脸横肉,狞笑着望着她。
女孩吓的脸色惨白,慢慢地退到写字台的椅子后面,双手紧紧抓着椅子靠背。
“你……你干什么……”
那个鹰钩鼻子军官却没有进来,掏出一支烟点着了,靠在门口,一边抽,一边恶狠狠地盯着她浑身上下看。
女孩被看得全身都是鸡皮疙瘩,一股冷气从脚底窜到头顶,又从头顶窜回脚底。
这样僵持了好几分钟,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鹰钩鼻子军官马上把半截烟扔到痰盂里,“啪”地一个立正,站地笔直。
“来来,坐坐,勿要客气。”
老少校夹着公文包,笑容和蔼地走进来,指指沙发,示意她坐。
女孩一阵虚脱,两腿一软,顿时有种得救了的感觉。在船台上还觉得这个老头恶心得要命,现在却怎么看怎么亲切。
鹰钩鼻子军官恭敬地跟在老少校身后,接过公文包,又把他的军大衣和军帽挂在衣架上。
“坐呀,勿要客气,呵呵,”老少校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一指对面的沙发,“到阿拉这里跟到家里一样。”
女孩拖着酥软的双腿,挪到沙发前,慢慢坐下,后背已被冷汗湿透了。
鹰钩鼻子军官端来两杯热茶,又端了一盘瓜子放在茶几上。然后,退到老少校身后,斜抱双臂,倚坐在写字台上。
“来来,勿要客气。”老少校把茶和瓜子推到她面前,热情地让着。
女孩揉着摔痛的膝盖,悄悄打量着这间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相当朴素。墙上刷着白石灰,下半截的灰绿色油漆已经有了斑斑驳驳的起皮。天花板上点着一支四十瓦的灯泡,暖黄暖黄的,显得很舒服。窗户都用黑色的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好象是怕一丝光漏出去。角落烧着一只煤球炉,洋铁皮烟筒信道外面,屋里暖烘烘的。
相当显眼的是,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副玻璃镜框,是一个瘦削男子的油画像。他穿着笔挺的陆海军大元帅服,挂着勋章和绶带,扶着佩剑,戴着圆框眼镜,脑袋像萝卜头一样,大额头,高颧骨,表情严肃。
她认得那是宣统皇帝溥仪,当今清朝嘉德皇帝毓畴的爹。
“看看,阿拉这间办公室怎么样啊?”老少校由着她打量了一圈,然后笑眯眯地问道。
女孩没说话,眼睛却努力地往老少校的肩章上看去,想分辨上面是什么图案。
她知道和明朝、日本不同,清朝在亚洲大国中维新算很晚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搞洋务,建立新军,上世纪末光绪帝戊戌变法,才算是从体制上开始正式维新。至于宣统帝溥仪二次维新,剪辫子、遣散太监、军队近代化,只不过是最近二十几年的事。清军也是仿照其它国家,在肩章上用杠加图案区来分军衔。明军肩章上是杠加铜梅花,清军肩章上是杠加铜星。但眼前这个老少校肩章上却既不是梅花也不是星,而是两条杠加一只小黑蜻蜓。
看她没说话,老少校又笑道:
“侬弗(不)讲阿拉也晓得,侬嫌阿拉这里老寒酸,呵呵,阿拉大清穷哦,比弗了侬明朝,‘苏湖熟,天下足’,钞票老足格。”
女孩盯着那只小黑蜻蜓,心里掠过一个念头,眼珠转转,试探地说了一句:
“难道,‘粘杆处’也会寒酸吗?”
“哦?哦,哈哈哈哈……”
老少校转脸和鹰钩鼻子军官对视一眼,都仰天大笑起来。
“呵呵呵,好好,”老少校收住笑,怜爱地点着头,夸奖道,“啧啧,小姑娘尬灵巧哦。”
果然是清廷最可怕的特务机关——“粘杆处”。
浦口在后世是南京的一个区,但在这个时候,却成了清朝的一个大军镇。由于这里能够直接眺望明朝的首都——南京,军事位置无比重要,清朝在这里驻有重兵,修筑了工事、军营、机场、仓库、重炮阵地、机务段、船坞和码头,在这里的驻军比当地的居民还多好几倍。一到节假日或周末,满大街都是当兵的,反倒没几个老百姓。
在驻军司令部的围墙里,有一栋灰色的二层小楼。这栋小楼和司令部内的其它办公楼相比,可谓毫不起眼。但是从军官到小兵,对它都是敬而远之,能绕过则绕过。就是不得不从它前面经过时,也会低头噤声,加快脚步,好象它随时会张开大嘴,将自己吞噬了。
这便是“粘杆处”在浦口的分支。
据说这个“粘杆处”当年雍正帝创立的,原来只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胤禛还是皇子时,他的府邸内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都有鸣蝉聒噪,喜静的胤禛便命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禛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禛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打着“粘杆处”的幌子,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雍正登基后,粘杆处成立机关,正式开府办公。民间广为流传的“血滴子”,说的就是粘杆处里的杀手。
雍正帝死后,乾隆帝为了对付南明活动频繁的厂卫,“粘杆处”不但没有裁撤,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光绪帝变法,将人人谈虎色变的粘杆处换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名字:“皇室奏事署”。到了20世纪,皇室奏事署(粘杆处)已经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后来的克格勃)一起,被并称为在“全世界最恐怖的两大特务机构”。
粘杆处的内部人事情况一般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里面全是旗人在做。
……
这时,另一个年轻的军官喊报告进来,呈上一份文件和一个大信封,对老少校耳语了几句,又好奇地看了女孩几眼,退了出去。
老少校向后示意一下,托津点点头,拿起那份文件,念道:
“秋湫其人,生于大清宣统六年(1915年),即伪明德永十四年,南京人氏,乃伪明天地会南京总舵负责人秋老虎之女。彼因与其父不合,离家考入伪明宁波海军大学校修习潜艇指挥,于大清历嘉德元年(1934年)完满学业,领少尉衔,至伪海军长江舰队南京江心洲潜艇基地服役,先后见习于潜艇‘螳螂号’、‘黄雀号’,嘉德二年六月衔升中尉,任‘蚱蜢号’侦查潜艇指挥官……”
老少校一边听一边将大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一件一件地慢慢玩赏。一枚刻着一串编号和“秋湫”二字的洋铁小牌,一支自来水笔,一块防水怀表,一串钥匙,一只指甲刀,一把小梳子,一对发卡,几只别针,几枚明朝硬币,一只浸湿的小钱包。翻开钱包,里边没有几块钱,倒是本该放情侣照片的地方,却放了一张憨态可掬的米老鼠画片。老少校微微一笑,放下钱包,饶有兴趣地从这堆零碎中捏起一枚银质的梅花形勋章,把玩起来。
秋湫一颤,低下头去,喃喃地道:
“那是我的……我的勋章……请你放下!”
第6章 审讯
“……秋湫任艇长六个月来,执行江面任务七十二次,其间我浦口码头和舰艇屡遭其侦查和袭扰。今年十月四日午夜,以鱼雷击沉我‘巴鲁图号’驱逐舰,致使我官兵阵亡十余。伪明海军部对其进行嘉奖,并授其‘梅花勋章’一枚……”
“哦呵呵,原来是南京秋公的女公子,失敬失敬,”老少校放下把玩半天的勋章,笑吟吟地换上一副地道的南京口音,“既然秋小姐是南京人氏,那我们还是用你家乡话聊吧,方便一些。”
“啊,原来你不是……原来你是……”秋湫惊诧地望着变口音就像变戏法一样地老少校。
老少校满意地看着这一手的效果,笑吟吟地道:
“呵呵,这样不公平,是不是?好,我们认识认识吧。”
“我,”老少校笑嘻嘻地指着自己的鼻子,“叫尼玛善,是大清皇室奏事署,哦,也就是你说的‘粘杆处’,在浦口的分署长官。”
“他,”他又指了指鹰钩鼻子军官,“叫托津,是老朽的副官。”
托津笑嘻嘻地冲秋湫拱拱手。
秋湫像触电一样,垂下眼睛。“粘杆处”全部都由旗人掌控,这一点她早该想到的。
尼玛善微微颔首,风雅地笑道:
“呵呵,‘秋湫’者,秋水也,好名字。‘蚱蜢’者,‘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嗯,也有出处。难得,人与艇的名字都很雅致。……唉,可惜啊,现在艇,已经变成一堆废铁,面目全非了。人嘛,还是要好自为之,不要也……啊?哈哈哈……怎么样,托津,那我们就开始吧?”
托津连忙一拱手,坐在写字台后面,摊开纸笔,准备记录。
一小时后。
……
“尼大人!尼大人!您没事吧?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气,我马上收拾她……”
托津大声呼喊着瘫在沙发上的尼玛善,用力掰开他的嘴,从小药瓶里倒出一粒药丸,填在老头舌下。
“嗯……”
老头虚弱地哼了一声,微微张开眼皮,刚看到对面的秋湫,立刻又怒火攻心,抬手微颤颤地指着她:
“你……你让她……再说一遍……”
“嗻,”托津转过脸,对秋湫吼道,“尼大人问你最后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