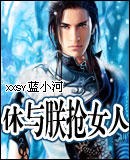干城兄的女人-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年来,做了十次的复检,都相安无事,要复发早就复发了。”雷干城言下之意已不在乎自己的命了。
“你心存这种侥幸的观念是错的。当初因为及时割除你胃部的癌细胞,没让你吃到苦,反让你看轻癌症的可怕,你是非‘贱身养癌’到成了末期病患后才甘心是吗?”
“好,好,好,别催,我刚练完拳一身汗臭味,你总得让我梳洗一下,咱们一个小时后见。”雷干城迅速收线后,顺手一扬将机子拋还给邢谷风,吹着口哨径自往个人专用的三温暖室走去。
半小时后,平头整面的雷干城换上一套光鲜笔挺的黑色手工西服,神采奕奕地在三位弟兄的陪同下,坐进防弹轿车,任司机载往佟玉树服务的医院。
一路上,看着飞逝而过的树影,想着眷村旧事。
雷干城与佟玉树是从幼稚园、国小一路念到国二的同学,两人在学校的表现可说是平分秋色;前者是代表学校对外参加水墨画及书法比赛的模范生,后者则是老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事便在课堂上拆古董教育招牌的资优生。
要不是艺术天分特强的雷干城在国三开学不到一个月时,在毒贩组织卧底的警察父亲未能及时揭发出官员和黑道勾结的内幕,就被人出卖、误逮、送进牢房,最后在狱中惨遭加害,因而自暴自弃留级两年,外加断断续续休学养家的话,他可以和青年才俊的佟玉树一样前途无量,甚至有可能成为台湾当代新生艺术家。
可惜,这种风流雅命他无福消受,当佟玉树医学院快念完时,他才勉强地从高中夜补校毕业,和其他念补校人手一机的叔叔、阿姨辈同学一样,也是边念书边赚钱。
首先,刻得一手好篆体的他白天到一位印章师父那里打工,依客人的要求设计字体,晚上则是将临摹的假古字画放到中华商场去寄卖,四年之内从不识货的美、日观光客那里赚足小本,正当他的模仿手笔愈来愈纯熟,替古人落款“背书”到几可乱真的地步时,一张“甲种体格表”和“金马奖”当兵通知单下来,才收拾家当,报销国家米粮、浪费死老百姓的税捐去。
当兵从伍期间,只要一有空,他便守着收音机调波频,当同僚下棋、打桌球、听着流行音乐,翻看小报杂志时,他则是拿着报上的金融版,守在公共电话旁,拚命记下股数,然后从裤袋里掏出一双纸钞和铜板;纸钞是买退正在跟情人热线传情的同僚用的,铜板则是拿来打电话给股票市场的操作员,指示股票交易。
两年十个月后,他退伍葬了病累的母亲,以全身仅有的现款在大学城附近承租场地,将几颗俗不可耐的水晶球往天花板一吊,打上艺术镁光灯,专业音响一放,固定开办纯粹提供学子发泄考试压力的地下舞场。但那时蒋经国先生还没走,严也还没解,学子在校外跳舞是触犯校规的,而开设地下舞场,在家长、学校和教育单位眼里简直就是干下妨害风化、出卖色情的事。
所以他被假道学的邻居告了几次密,不得不收山潜伏几个月,好在被压到谷底的股票突然解套、反弹,进而狂飙让他发了一笔小横财,最后他顶下在公馆三总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小酒吧,将内部改装成校园民歌餐厅,挂上了“学生情人”斗大的招牌,把在电子公司做装配员的三等亲婶婆请来当主厨,雇请一些长得不差、歌喉又不赖的学子歌手来驻唱,至于清洁工、酒保、侍者到经理等职,则是被他一人统统独揽下来。
人活到二十出头,能拚出如此成绩,照理该是心满意足了。可惜,雷干城还是没有享这种安居乐业的命,他与长他七岁的大哥雷从云打从父亲被宪兵押入牢底、未能保全名节后,尝尽亲戚邻居、学校老师的人情冷暖。
早在他十五岁时,就深刻体验到这个社会是笑贫不笑娼的。表面上你可以光鲜有办法,私下贩毒、卖笑任眼红的人去猜到脑中风也都没关系,但就是别被逮,一旦被逮,所犯下的罪不再是自己一肩扛,你的妻子、儿女连带要被烙上罪人的印,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连同宗血脉都把你当麻疯病人似地唾弃。
从那时候起,雷家两兄弟的失志是要出头,管他什么仁义道德,有钱有权的人才玩得动筹码,拿那四维八德的礼教去吃人。
于是雷家老大走上黑道亡命生涯一途,专与警、政作对,某日突然吃错药在罪恶渊薮的组织里搞了一个窝里反,把北台湾专门走私毒品帮派龙头老大及一位跟黑道挂勾的警界高官做掉后,成了黑白两道上的头号通缉对象,逃到日本不过半年便被人发现溺毙在东京郊区的一条河沟里,死时年仅二十九,生前在台北所打下的地盘登时土崩瓦解,逐渐被蚕食鲸吞。
消息传回台湾后,雷从云堂下照拂的几十来位弟兄,不是被警察盯住捎,就是被仇家逼得走投无路,竟无一人能到东京警局收尸。最后,雷干城是在诸位匿名的黑道兄弟及好友佟玉树的掩护下逃过追踪眼线,从高雄搭上走私渔船到香港,再从启德机场飞抵东京,和雷从云在日本拜把的兄弟碰头,无奈仍是慢了一步。因为雷从云的尸体早在消息发布的当日就被一个自称是雷从云的未亡人领走了。
听日本警员的说法,来认尸的人是个浓妆艳抹的烟花女,身边还带了一个理了平头、不及五岁的男孩。由于这一妇一孺突然冒出来,心有案底的日本警察竟不知如何将这出戏演下去,反倒是亲眼目睹遇害多日的冷尸,因为亲骨肉的现身而七孔溢出血来,怜悯之心大生。
邪门也好,亲痛仇快也好,办事员见多了这檔事,要不迷信都难,当场接过女子呈上的文件去影印。文件副本不仅有女子与雷从云在日本注册的结婚证书,更有日本国护照及户籍联络地址,但事后经过查证,才赫然发现所有文件都是伪造的。
雷从云的尸体就这么地随同女子和小男孩离奇失踪。
由于雷从云非日籍帮派人士,再怎么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也不关他们的事,更何况当时台湾与日本之间并无签订引渡条款,坏事干尽的黑道分子生前都引渡不走,死后也不必太追究。
在返台的飞机上,雷干城与雷从云的拜把兄弟皆面如槁灰,心上不乐观得很,他在途中一直问自己,如何才能摆平这件事?到他们下了飞机,从接机的兄弟口里得知,江湖杀手已蠢蠢欲动,放出眼线探寻雷从云五岁大的后嗣时,他知道,不介入江湖已是不可能的事,他雷干城这辈子是别想回去过善良小老百姓的生活了。
想到此,他不觉轻叹一口气。
阿松趁这个时候,问了,“城哥,树哥的医院到了,要照惯例停在对街吗?”
“不,直接开下停车场。”雷干城心不在焉地回答,回头继续想着好友。
在良民病人与护士眼里,拥有医学外科与肿瘤学双料博士头衔的佟玉树,是仁心仁术、活人无数的俊俏医师。
这年头日子好过,命却难捱,人一有微恙,就往医院跑。照理说,医生行情该是年年涨停板、拉风得很,衰就衰在佟玉树这个活菩萨上辈子没将正果修到圆满,今生注定有他这样一号在黑道上混吃等死的损友做程咬金。
打从实习结束被分发到医院就任,佟玉树所服务的医院的停车场三不五时就会冠盖云集,不是得为胸前绽了肉的皮缝回去,就是得在中了弹的三头肌上挖挖补补,有时下夜班还得权充“难丁哥儿”,出入枪林弹雨之地给他送药。
九年来,佟玉树起码换了五家服务单位,中间还因大力拥护、请愿健保制度的细故,没有任何“私立庙院”肯收他这个和黑道沾上边的泥菩萨,使他不得不出国进修一年。
这样给损友一折腾,他的饭钵已从金、银、铜、铁贬值到锡了,被摔得坑坑洞洞不说,升官之路早荆棘满布。
好在两年前有独具慧眼的仁人志士,以大财团名义出资盖了一所慈善医院,事先理出一整楼的地盘,把佟玉树挖去当外科主任和防癌专案小组的召集人后,他这棵医术高人一等、霉运多人一倍的枯木才算逢春。
如此为损友两肋插刀一辈子,仍是无法展现他“神”的地步,最神的是他老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臭皮匠个性。
约莫六年前吧!二十八岁的雷干城将兄长分崩离析、兹尔多事的小组织运横起来,重新拟下帮规戒条,执行严禁买卖、走私毒品。由于他下这道禁令,砍断的不仅是帮内的财路,更牵惹到其他山头及黑白两道的大盘既得利益者。
正巧初时,尚有不服气、毒瘾又重的年轻成员“扳手”受到外面大帮分子的煽惑,想搞内讧,在仓库集会时预藏枪枝打算将雷于城做掉,却没想到才开了一枪,连他的杂牌旧汗衫都没能侵害到,就吃了其他有备而来的兄弟射子弹,从右肩臂至右胸膛处,一共三发,不用高官政要嘉勉,自动跳级成三星烈士,足下一坪大的水泥地,当下被他流出的鲜血滴成满地红,昏迷的身子被送到临近两家医院,皆被医护人员以急诊室床位已满,打了回票。
人走到穷途末路时,有时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本已和自己约法三章,不再麻烦好友的雷干城只好在午夜时,将奄奄一息的兄弟扛往佟玉树的服务单位去。
刚下了小夜班的佟玉树见了枪伤,连来龙去脉都省了问,马上跟上级主管查询是否有空出的手术房可救急,要不普通病房也成。
上级主管记忆力超人一等,连行事历都不用看,就跟他说没空房,摆明不愿收人,并且警告他已下班,别再惹是生非,因为一旦收了枪击患者,就得报警,届时消息见报会为院方招来不便,影响声誉。
佟玉树闻言,二话不说,哂然冲着主管笑,笑到对方心虚目逃后,才甘心认赢地将白大挂一脱,扔在主任办公桌上,转身离去。
那时怕担心好友的事业又给自己拖累,雷干城在走廊处板住他,劝了,“没关系,我们再找医院好了。”因为佟玉树的碗这回是用锡补的,再下去,已没值钱的金属可任他洒脱地当(DOWN)下去。
岂知老兄故意曲解他的话,硬是要砸掉自己的饭碗,“也好,反正这家医院是死店活人开,待久,不得风湿也会成强尸。”
“不,你还是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多救几条善良老百姓的命吧。”雷干城拍拍好友的肩,说着以眼神示意,要弟兄们将人抬回车上。
佟玉树在冷冷清清的急诊室门前对着雷干城的背影讽了一句,“命到死神手上还有贵贱之分吗?我以为你很重义气。”
雷干城的一名绰号叫阿猴的手下忍不住回头开口解释,“树哥,你不知道,这中了毒瘾的‘扳手’受了外人的怂恿,打算出卖城哥呢,要不是我们事先有做防范,找了一件防弹背心让城哥穿上的话,躺在这里的人会是城哥了。”
佟玉树冷冷地质问:“那又如何?‘扳手’的命就不如城哥吗?还是城哥忌惮他被救活后,又来行刺?”
阿猴连想都没想,就说:“话不能这么说……”
但被雷干城拦了下来,“阿猴,没关系,树哥若想试,就让他跟上来吧!”
佟玉树提了公事包跳上雷干城的发财车后,喧宾夺主地要司机兄弟照他的指示,在暗夜里抄阗无人音的小径,一路杀到万华,在外公和二位舅舅合开的中医院门前叫停。
他回头对雷干城说:“你挑三、四名较壮的兄弟留下,其余的,叫他们回去等消息。”
话毕,他大步奔进院门内,才贬把眼,便领着一行人,出现在轰隆而开的两扇门前,十万火急地将大肆、半昏半醒的“扳手”挪到一张洁净的急救床上,往院里推去。
佟玉树的大舅趁佟玉树和雷干城一行手下在洗手台前上皂消毒时,先以针灸为“扳手”止血,将沾了血块的丝质花衬衫剪除后,退了出去。
佟玉树先观察“扳手”的伤势,然后以非常严肃的口吻问:“你平常嗑什么药?用量多少?”
“扳手”没有回答,只是以左手捂着双目,一劲地哭。
反倒雷干城的一名手下小刚替他回答了,“这小子瘾头重,有什么就用什么,红中、白板、吗啡、安公子、海洛英、古柯碱统统来。简直不像话!
难怪会让人牵着鼻子走。”
佟玉树看着才刚二十出头的“扳手”,放软语调,“事情已发生,后悔也没用。城哥为人阿莎力,要保你的命可以,问题是,你自己究竟想不想活?”
“扳手”已哭得不成声,佟玉树只能依稀听着他抽搐道:“城哥……我……怕痛…
…”双眉紧连在一线的雷干城上前紧握住“扳手”晃抖的手,给他鼓励,回头轻问佟玉树,“能上麻醉吗?”
“没验过血很难说,不过照小刚的说法,他神经中毒的情况挺不乐观,就算打了止痛、麻醉剂也没用,增加用量可能危及性命。”
“扳手”不懂他们的话,只听到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