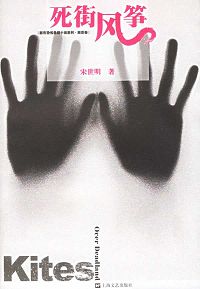欢醒街-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1章
如果非要将生命中的时段命名;那么我近来的日子应该叫“没头脑”或“不高兴”。大学毕业几年了,我还是那个不见长进、面恶心善的姑娘。薪水不见涨,名字还经常被人拿去恶搞。
纽芬兰,这个名字是我妈给起的。没出生那工夫,我爸本来给起的名字叫纽静,虽然这名字巨通俗,可毕竟是个人名。就在给我上户口头一天,在一段《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我妈听到一条关于加拿大领导人访华的新闻广播,知道了在那个遥远的国度有个地方叫纽芬兰,于是,便执拗着非给我以此命名。起初我爸不干,后来怕我妈生气上火导致没奶水才应允下来。出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会说话,我爸为此还怪过我妈是不是图便宜吃了劣质的避孕药。
我想不明白我姥姥挺靠谱儿的人,怎么会生出这么一没谱儿的闺女。不过后来也挺庆幸,幸好当时我妈听到的是一条关于澳大利亚的新闻,要是条关于美国的,没准儿我名字就成纽约了。
顶着这个不像人名的名字活了二十多年后;大学一毕业我便取消了毕业旅行的计划,直接拖着行李箱来到了这座城市,投入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生活中。
在这座城市中,我有些自己的小幸福、小不纠结,偶尔发挥一下小宇宙。我一直自认挺靠谱,可总被他们认为不着调。这个“他们”的范围包括我爸我妈、还有大学时代几个猛人姐妹儿、哥们儿。其中一个叫王以慧的,还曾经怀疑过我的智商不高于60。
起因是某个暑假我去王以慧家玩,聊的正兴起的时候,以慧爸突然回来,我张嘴就叫了声“阿姨”,正尴尬地脸通红的时候,以慧妈又出现,我顺嘴叫了声“叔叔”。
事后我反思,以慧家长回来我如何至于那么紧张。又不是去男朋友家鬼混,何况我和王以慧之间又没有私情,我俩的性取向都正常。如果不是因为智商低,这事情确实解释不了。
王以慧口无遮拦把我这个段子四处传播,我威胁数次未果,于是动了和她断交的念头。从大学毕业直至此后九个月,我没给她打一个电话,直到那个周末,王以慧风风火火打来了电话,好像此前的不愉快从来没发生过。她掩不住噌噌往上窜的荷尔蒙,问我接吻是什么味道。
我告诉她接吻的味道全凭个人体验。老实说,我也好久没干那缺德事儿了,自从和夏讯分手后,我身边就没有过从甚密的男友。我猜想王以慧是恋爱了,我想不明白的是怎么会有男生喜欢她那种超级柴火妞儿。王以慧的后背上要是贴上两粒葡萄干,可能会分不清反正面。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接到以慧的电话。不知道是她洞察到了我的酸葡萄心理,还是这丫头沉溺于恋爱的小情小调中无暇旁顾。总之我为此纳闷了很久,可能还夹杂着一点怨怼。这种怨怼一直持续到接着以慧妈电话的那天。
如果知道那次以后我将再也听不到王以慧的声音,我一定八婆至极的跟她闲谈爱情的糟糕与美好;搜肠刮肚地给她分析接吻这件事,从形式到内容、从介质到实质,从现状到下一步发展趋势。我甚至怨恨自己毕业时不该跟以慧搞了恶作剧,不让她送我而独自离校。
毕业那次分离,我只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电影散场,惰于告别。该再见的,总会再见到的。我是这么以为的,王以慧也是这么以为的,可能我们都是这么以为的。
第2章
刚上大学那工夫,我加入的体育社团叫“欢醒街”,社团的主题是音乐和篮球。我们的社团只有五个人,四女一男。王以慧、李渔、徐蔓、丁当和我。在外人眼里,我们是最不像篮球队的一支队伍,身高参差不齐,造型各异。
虽然人数不像别的团体那么众多,但人数少更利于存小异、求大同。那时的我们,像极了社会主义公社里的红色分子,除了男、女朋友和安全套,其它基本都是共享通用的。
我们时常坐着公交车进行对这座城市的旅行。在街上看到貌似可怜的小孩子时,会很滥情的捐出身上的每一张人民币、连同钢蹦儿,因为没钱买车票而步行回学校;然后为几十块钱的学校乱收费与官方交涉数日;自费几百元给球场换上自己看着顺眼的吊灯。
这种漫无目的幸福日子一直持续那个夏天,我们毕业离校的日子。从那以后,夏天在我的生命里成了一个很敏感的符号,认真又潦草。拿到毕业证那天当晚,我们几个决定去集体发一次情,去校外吃顿小范围散伙饭。
刚进饭店的门儿,迎面碰上另一个女寝的一伙,曾和我们发生过群挠事件,战火源于抢占学校女浴室的一个水龙头,双方伤势最重的成员都曾脸被挠成粉丝状,差点破相。我们友好地打招呼,就跟什么事儿没发生过似的。
我们5个人要了5瓶啤酒,后来又叫了多少就不知道了。我们五个在一杯酒入胃后,就回忆起了欢醒街不太显赫历史。五个人当中唯一的男同学丁当说欢醒街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回忆了半天,没搜索到关于起这个名字的片段。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当时正值青春亢奋期的我,不太可能起出这么朴素、低调的名字来。但如果不是我,别人的可能性好像也不大,这种近似风雅的伪文学小事儿他们又都不乐意干。
欢醒街在学校篮球界虽然战绩不佳却也很有名号。由于队中有了一名男生,我们成了各种篮球社团中最具特色的一只。我们四女一男应战对方六女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丁当在场上时常被二个女生前后夹住、发挥不得。那时的他一定还不懂得如何合理而又巧妙的吃到豆腐。他在球场上走的绝对是驯良路线,每场下来,全队犯规次数最少的就是他了。
我们也偶尔和校内的男子篮球社团打打比赛,对方讲究一点的,会自觉地少上一至二个人;如数五个全上场的,我们也从不就对方的人数提出质疑。打球的乐趣在于球在经过大家传递之后,落进篮筐的那一刻。计较太多,想要的乐趣必有所损耗。
那天的散伙饭吃到最后,王以慧一把鼻涕一把泪抓着我的袖子说,有件事放在她肚子里三年了,还没告诉我。我以为是她想说曾经挪用过我的饭卡买了四个茶蛋。没想到,她说的是:我暗恋了你们家夏讯二年多。我说你搞错了,夏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美男可能也像社会主义公社田地里的玉米似的,指不定是谁家的呢。夏讯是我在大学那几年里的男朋友,在拿毕业证前刚刚分手。
几年里,头一次见这些平时喝饮料都要男生给拧开盖子的姐妹儿对着瓶子喝,结果就是,纷纷把自己灌倒。我想,我们各怀心事。有的是为了没着落的工作,有的是为了刚刚开始就死去的爱情。
散伙饭的收尾场面自然是男男女女痛哭流涕抱作一团。淑女不必再扮纯,善良男也可能转眼成禽兽。丁当端着酒杯绕到李渔后面敬酒,谁都知道他喜欢李渔、但李渔不知道。两人的酒杯没等碰到一起,李渔倒地昏迷,丁当一头载到蟹黄豆腐里。我扮做深沉状接过徐蔓递过来的一只烟,却没选好方向,冲着风差点被呛成哮喘,并立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抽烟,从此没再碰那玩意儿。
临散伙前,王以慧又说她其实最喜欢的是建工系的“绝对高度”。我问她,你刚才不是还说喜欢夏讯么,王以慧说喜欢夏讯的时候是两年半,近一年半就光是单恋“绝对高度”一个人。她说已经和“绝对高度”约好了一场篮球比赛,五年后的6月30号进行。如果那时候还能见到“绝对高度”,就告诉他,她曾经多么*的暗恋地他,不管那时绝对高度有没有女友,都要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就此我断定暗恋这事真是一场无比纯真的闷骚。但我们还是特欣然的接受了这场比赛。那时我以为王以慧一定有向“绝对高度”表白的那一天,我是这么以为的,我们都是这么以为的。
那个夏天是最牛的夏天。五年后的6月30日也因为那个了不起的约定而变得金光闪闪。 。 想看书来
第3章
吃完散伙饭,姐儿几个抹干满脸纵横的香泪,一摇一晃、相互搀扶着走回宿舍。我晕头转向跟她们回了宿舍,然后又想起我本不想回去的。我一头钻进学校的放映厅,准备看最后一场录像,几年里,我和夏讯在这儿渡过了许多个周末的夜晚。
管放映那老师刚接这摊儿的时候,总装文化人儿,放映前还总是介绍一下影片的拍摄背景、历史渊源,碰到奥斯卡经典片子,还溜达出几句英文,目的是寓教于乐。学生们的素养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反正这家伙曾创下了连续五天被哄出去直接到门口卖票的记录。到了第六天,他直接放电影,屁都没放一个,估计是伤心至极,懒得与这帮粗人为伍了。
那天,放的又是《铁达尼号》。以前和夏讯来看这片子,第三遍的时候我还抓着他的袖子哭个不停。在学校的检阅台上,我们不知多少次的表演船头飞翔一幕。我是为了满足青春期浪漫无限的愿望,夏讯后来亲口坦白,他是借机量量我的腰,我们都乐此不疲。
这一次,我看铁达尼号没有哭,还差点笑出声音来。珍妮那妞儿就是一*的主儿,刚认识就让人家给上了;最愁人的是那个傻波杰克,为了泡一个刚认识的妞儿把命都搭上了。
和夏讯分手后,我脑袋顶上的天空是有点变色,但世界观没发生变化。我仍然是唯物主义者,仍坚信有精神图腾的存在。那时候,我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崇高得能像格拉瓦的头像一样,被人们穿在胸前、抽雪茄时不自觉地想起。后来我发现,世间凡竭力为某高尚事之人,即便背影引人瞻仰,其下场也多半憋屈。我的爱情曾经很高尚,但爱情不是一个人高尚的事儿。我仍然善良,却无法高尚。
放映室的黑暗中,我回头扫一眼那些学弟、学妹,许多个我在纯情地哭着,许多个夏讯在陪着哭。
从放映厅回来钻进寝室的时候,王以慧还躲在上铺的蚊帐里苦练吹口琴。王以慧那天晚上吹的歌依然跑调得厉害,但我还是听得出是《祝你一路顺风》。半年前,做了腿部肿瘤切除手术的王以慧变得更加安静,不再喜欢运动,每天用更多的时间呆在屋子里,她那时就流露出宅女潜质。吹口琴成了她的癖好。五音基本不全三音的王以慧说,欢醒街每个人走的时候,她都要在站台上吹这首歌。
我的记忆库里不愿意储存一些不快乐的记忆。为了跳过忧伤那段,我宁可记忆出现断层。
在告诉所有的人坐第二天晚上的火车走后,第二天一清早,我一个人站在了站台上,踏上了远去的列车,一路飘移。
第4章
在那个崭新的城市我生活的不算很好,可也不是太糟。至少遇到了两个可以温暖相处的邻居,步维和小耕。
步维是个男文青,是文艺男青年,不是文学男青年。他每天和声音打交道,睡觉时却拒绝任何声响,多数下雨的夜晚都会深度失眠,不论暴雨中雨还是小雨。
小耕是个自闭症小孩,轻度抑郁症人士。他比我小四岁,却总固执的喊我小丫头。小耕在这座城市学语言等着签证,然后滚蛋,去美利坚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虽然小耕时常说出“I am who ah ”,“good no good?” 等句式,我还是觉得他英语水平不错。
为了打发时间,小耕找了份工作,在公司里他一贯沉默,谁都以为他静如处子,可没想到实则动如脱兔。公司大BOSS在场上会议上,小耕会说出几个新华字典上找不到的字,因此从来没加过薪。
在与步维的相识后,我对生命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我那些狼藉的灰暗时段总会被他碰到?
其实,为了让那些狼狈的情形不让第三人知道,我真应该像警匪片中的某个场景一样,杀人灭口,一木棒把他打的倒地昏迷、口吐白沫;或者天天祷告他一跤摔到完全失忆。但哪样我都不忍心,更为主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灰暗终有变粉红的一天,而步维无疑是见证的最佳人选。
与步维的相识的日子,正是大学毕业那年离校的火车上。
我刚在火车上坐稳,几个人有说有笑地上了车。整整的一横排座位,只有我一个是陌生人,其余的全被他们占领。其中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子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没有看脸庞,只觉得男子的气场是我不讨厌的。
他刚坐下,隔着一条过道的座位上,一个抱着LV包的女孩站到了我面前。“我们换一下座位好吧?”我正视女孩眼睛时,才发觉她是在和我说话。白皙的脸,并不挑恤的眼神。我刚想起身,一只手横摆在我身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