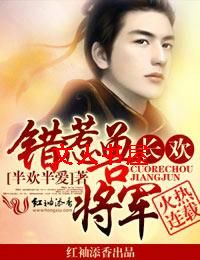理事长-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重新跌入困境。假若为一个残疾人安排一种能胜任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就不会存在生活难题。一个盲人通过实施手术重见光明就可以自食其力。一个暂时有困难的残疾人,如果掌握一门谋生技能,或得到一笔政府无偿提供的贷款,他就可以用能力和财力或扩大生产或养猪喂牛,自己摆脱困难……
“九五”计划的核心是增强残疾人自食其力的造血功能。理顺了这个思路,马良把县残联近期的工作定在了劳动就业和康复扶贫两大点上。
就在这时候,国家残联关于统一制发残疾人证的通知和举行第六次全国助残日的文件发到县上。同一时间,县残联关于召开二代会的申请获得政府批准。西川县残联的工作在这个温暖的春天里,进入空前的紧张忙碌中。 。 想看书来
理事长 二十(1)
程灵敏和冯兵并肩走在宽阔平坦的县城西大街上,如织的人流和穿梭不息的车辆以及街两旁琳琅满目的橱窗,从他们眼前匆匆闪过,两个年轻人没有任何兴致欣赏近在眼前的街景,紧张的工作为两张青春飞扬的脸庞抹上一层少有的凝重。他们迈着急促的脚步,向着目的地七里原奔去。
这次下乡,原本没有程灵敏,马良指派的是冯兵和蔡丽芸。县残联已提前对全县残疾人建档立卡,核发残疾人证的工作也仅剩*检核查和填送报表,程灵敏一人绰绰有余。老资格康正年则全力筹办县残联二代会事项,为加大助残日宣传力度,马良让冯兵和蔡丽芸下乡采访几个有突出成就的残疾人,整理出典型事迹材料,由县广播站同期播出。在这之前,经与县委宣传部协商,县残联和县广播站联合开辟了一个“同在蓝天下”的栏目,集中报道一批残疾人先进人物。
就在临出发前,程灵敏提出与蔡丽芸对调了工作。究其原因,一来细心的程灵敏发现蔡丽芸来了例假,与冯兵一个大男人结伴,定会有诸多不便。二来程灵敏的心头不知从何时产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总想和冯兵待在一块儿。
连自己都不晓得这个奇怪的念头是何时产生的,是两人到残联报到时冯兵的那讪讪一笑?是冯兵跟马良工作中的默契?是冯兵与康正年的数次争吵?是冯兵与女同事的嬉笑打闹?是冯兵头回下乡的工作实效?是冯兵那张刚毅的脸庞?是冯兵随机应变的幽默谈吐……
是,似乎又都不是。这一切的一切翻搅在程灵敏的脑海里,短短半年中与冯兵接触交往中的点点滴滴像电影画面,顽固地闪现在她的眼前,挥之不去,过目难忘,折磨得程灵敏食不甘味彻夜难眠,二十三年平静的心田里,掀起了潮水般的波澜。
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不,不会的。*心魄的爱情决不会如此简单明了,如此平淡无奇。圣洁浪漫的爱情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是*摄魄的痴痴迷迷;是风花雪月的生生死死;是撼天动地的可歌可泣……程灵敏在心里一次次地反驳着,可脑海中却顽固地闪现出这两个奇幻的字眼,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无法把持自己,想接近他,想和他多待一会儿,想弄清他的身世,想知道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有哪种业余爱好……凡是任何涉及冯兵的细微枝节,片言只语,都会让她竖起耳朵,想听个明白。在经过数个辗转反复的不眠之夜的折磨后,程灵敏决定,捡个两人能独处的机会,和冯兵好好谈谈。
现在,两人已走到了西关正街,照去七里原的线路,必须穿过马路,顺着天柱路南行。就在踏上人行横线时,冯兵敏捷地紧走两步硕壮的躯体护在了程灵敏的左侧。程灵敏不觉心头一热,但她还是试探着问:“冯兵,我可不是小孩子,用得着吗?”
冯兵紧拥着程灵敏,一边走一边摇晃着脑袋,风趣地说:“保护女人是男人的天职啊,谁叫咱是个男子汉哩?!”
“扑哧——”程灵敏笑了。这家伙可真心细啊。
下了不足五十米长的天柱路,越过一〇八省道,在朝阳村南,穿越狭窄的横水河谷,爬上了七里原。
五月的七里原,一派生机盎然,大片大片即将抽穗的麦苗,墨绿油亮,如一方硕大的绿色地毯铺陈到遥远的天边。麦田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数片金黄的油菜花,在晚春灿烂明媚的阳光下,黄绿交错,醒目*,仿佛一幅浓墨泼洒的巨幅画卷,真切生动,赏心悦目。柔和的春风,轻悄悄漫过绿毯,越过黄浪,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麦香。 。 想看书来
理事长 二十(2)
两个年轻人被迷人的乡野风光,吸引得凝神敛气,看个不够。随即,冯兵像受惊的小鹿,撒开脚丫,大喊大叫着飞跑起来。
“噢!七里原,美丽的七里原,我来了!”
程灵敏一溜小跑,气喘吁吁地撵上冯兵,拽着他的衣袖问:“冯兵,你没来过农村?”
仍然陶醉在大自然神奇造化中的冯兵,头都没回随口说:“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哦,多么神奇的乡野!多么美丽的风景!”冯兵说着,抛下程灵敏,自顾疯跑起来。
“七里原,美丽的七里原,我爱你,我爱你!”
直到累得筋疲力尽,冯兵才停住脚步,干脆大叉开双腿坐在土路上,抹着满头满脸的汗水,瞧着远远落在后面的程灵敏。
程灵敏仍在一溜小跑着。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女子,一米六五的高挑身材,圆脸细眼,一头瀑布般的披肩长发,弯弯的刘海儿湿漉漉地贴在额颅上,汗淋淋的双颊红扑扑的娇艳妩媚,一身粉红色中式罩衣,紧裹着发育得匀称完美的窈窕身子,微风拂动着黑亮的发梢,绿海衬映着青春的身姿,乡路托举着年轻的脚步,像水中荷花,如枝头红梅……
冯兵看呆了。直到程灵敏跑到跟前捶了他一拳,方才醒过神儿。
程灵敏喘着气,不无气恼地问:“冯兵,发什么愣?”
冯兵像被人窥探到了心中的秘密,一下子脸红耳赤,极不自然地掩饰道:“哦,七里原上的风光真美哟!”
程灵敏抿着嘴偷偷地笑了,但她还是忍不住埋怨:“还大男人呢,丢下人家,自个跑了,像个疯子。”
“对不起,灵敏,我不是有意扔下你,实在太高兴了,二十三年啊,头一回身临乡野,又是这么美的风光。”言罢,冯兵爬起来,拍打着裤子上的尘土问:“唉,灵敏,你家在哪儿?”
程灵敏的心头咯噔了一下,但她还是老实地回答说:“就在西川,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川儿女!”末了,程灵敏反问:“你呢?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冯兵回过头,好奇地望了程灵敏一眼,随即涎着脸说:“这个,天机不可泄露啊!”
程灵敏不满地撅起了小嘴。
冯兵思谋了一阵,打着哈哈问:“灵敏,如果我告诉你,我父亲是个普通工人,你会相信吗?”
“不会的。”
“这就对嘛。其实,父母做什么,在我看来与子女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不对?”
程灵敏认真地点点头,忍不住又问:“冯兵,你喜欢农村吗?”
“喜欢!”
“真的?”
“千真万确!”
程灵敏咧开嘴,不出声地笑了。
他们继续赶路,笔直白亮的乡路把两人引到一个村庄。冯兵发现村口有座修缮一新的青砖祠庙,就蛮稀奇地奔过去,趴在条形木窗上向里面张望,殿堂正中是尊极普通的泥塑神像,与众不同的是这位古人(或是神仙)右手紧握着一只笔杆样锋利的竹签,左手托举着一片粗糙的树皮。冯兵左瞧右瞧,百思不解其意。
程灵敏凑上前,打趣道:“喂,天之骄子呀,看出名堂来没有?”
冯兵搔着脑袋说:“似乎有点印象,可实在记不清了。”
“告诉你,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创造者——仓颉。”
“噢呀——”冯兵大叫一声,有点狐疑地问,“史料上记载,仓颉庙不是在西京省东部的白水县么?”
“不错呀,白水县是仓颉的墓地,西川是祠庙。两者有本质区别。”
冯兵转过身,喜形于色地说:“还在读中学时,我就知道了仓颉造字的典故,做梦都没想到,西川县是他缔造汉字的地方。”
程灵敏乐颠颠地问:“你除了仓颉造字的故事,还晓得些什么?”
“你指哪方面的?”
程灵敏指着庄严肃穆的仓颉像说:“人在哪儿就指哪儿。”
冯兵摊开两手,连连摇头。
“典型的书呆子!”程灵敏一针见血地点拨道,“其实,除过史料所载,西川民间还有许多与仓颉有关的传说。”
冯兵冲动中抓住程灵敏的手,央求道:“灵敏,讲一个听听,解解馋啊!”
于是,两个年轻人紧挨着坐在祠庙门前的青石台阶上,程灵敏手托下巴,眨动着妩媚的细眼,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传说很早以前,为造汉字,仓颉辞掉黄帝的史官之职,骑着一条毛驴,走川过县体察风土人情,记录方言土语,所获资料以不同的符号用刀刻在树皮上。当走到七里原上时,毛驴累死了,仓颉就近在村头寻了间茅屋住下来,开始紧张繁琐的造字工作。一天夜里,屋旁涝池里的青蛙,不合时宜‘呱呱’乱叫起来,仓颉被吵得不堪其烦,一气之下就用准备写字的竹签饱蘸着以民间锅墨合成的墨汁,向窗外的涝池中甩去,零星飞洒的墨点不偏不正刚好溅在池里的青蛙嘴中,青蛙们不叫了。从这以后,涝池里的青蛙全成了哑巴,且嘴巴上满是黑色的墨点。这就是西川妇幼皆知的‘仓颉墨点青蛙’的故事,《西川县志》就有记载。”
“太有趣了。涝池在哪儿?咱们快去看看。”
程灵敏站起来,一脸忧患地说:“那个涝池如今成了村民的宅院,墨点青蛙已在七里原绝迹了。”
他们几乎同时叹息了一声,默默地进了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理事长 二十一(1)
韩黑儿是七里原上的名人。仓颉庙村及周围四邻八乡的大人小孩都晓得,这个腋下撑着双拐的残疾人,本事恁大,一张白纸上随便划拉上几行字,盖上政府的红砣砣,用几分钱的薄纸信封发出去,不仅名字登上报纸上了广播,邮递员还会把稿费给送进家里。这种本事,除了传说的仓颉,七里原上老几辈还没出过哩。远古的仓颉虽说创造出了神奇的汉字,可到老死也没换得一两银子。这韩黑儿莫非仓颉转世,专来世间捣鼓文字的?!
仓颉庙村的父老乡亲都眼馋韩黑儿坐在家里就能挣回公家的稿费,却没人细究,韩黑儿发给市县报纸电台的消息、通信以及隔三差五登在《农民报》上的民谣、快板、顺口溜换回来的那三块五块的公家稿费,连母子俩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这一日,韩黑儿听村人传言,邻近的苏家庄有个老头把儿女们给准备过七十七岁大寿的数百元钱全订成了报刊,供村人阅览,凭多年积累的新闻敏感,韩黑儿觉得这是个新鲜事儿,弄好了能上市报头条。他就早早起来,喝了碗娘做的麦面拌汤,拄着双拐,挪动着笨重的躯体赶到苏家庄,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采访,又向村民进行了核实。而后匆匆返家,铺开稿纸,趴在土炕头上一气呵成写出了《七十七岁苏老汉,不办寿酒订报刊》的新闻稿件,待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才从兴奋中回过神来。他突然发觉,炕头上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仔细察看数遍,原来是窗台上那一沓书稿不见了影儿。这可是他多年积累的习作草稿,是他的命根根哇。
韩黑儿焦急中翻下炕,架着双拐挪出房门,冲后院喂猪的母亲喊道:“娘,我窗台放的书稿哪里去咧?”
娘提着脏兮兮的猪食桶边走边说:“黑儿喊叫啥哩?那东西都搁那儿好些年啦,吃不得穿不得的,我早上拿出去换成东西了。”
韩黑儿大叫起来:“娘啊,你真糊涂,这不是害我哩嘛!”
娘放下猪食桶,撩撩额前的白发,迷惑不解地问:“咋?娘把你从一尺长挖抓着养这么大咧,咋能害你?明着说咱晌午没盐啦。”
韩黑儿望着娘皱纹密布的眼睑,面对一字不识的娘真是欲哭无泪。等回过神,一言不发地挪动双拐,急急向村口追去。
还好,那个收破烂的老头儿正在村口吆喝着招揽生意,韩黑儿磕磕绊绊挪到跟前问:“大叔,我娘卖给你的烂货呢?”
老头见来了个空着双手的残废人,知道没啥生意,满脸不乐地回嘴道:“你娘?!我哪晓得你娘是谁,咱可只认破烂不认人啊!”
说话的当儿,韩黑儿已在乱七八糟的烂货中发现了自己那一厚沓扎得整齐的书稿,就伸手擒起来央求:“大叔,这就是我的,能不能退给我?”
“那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