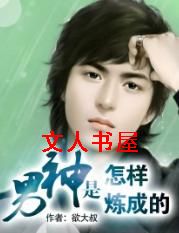我是怎样走上自杀这条路的-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叫雅的女孩最终出了国,她有足够关系,终于可以逃脱时代对她的魔爪。而我父亲没有,人生对于他依然是暗无天日,远大前程,宏图大志,全成了泡影。如今恋人也没有了。他随手捡起我母亲,就像捡起田里任何一根麦穗——娶谁不是娶呢。至少我母亲是热的,也许有一天他那头会被她焐热了,24岁的父亲有时会怀点柔情地想。
结婚第二年他们就有了我。我父亲给我取名为思雅。十几岁时有一天我和母亲一起清理旧物从一只木箱底发现了一摞书信。提头都是“雅”,我扫了第一封,把剩下的都从母亲手里抢过来,不给她看。
“我早就看过了。”我母亲轻声说,然后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继续收拾。
当天夜里我在台灯下将那叠情书一字不差地读完。真够火 辣呵。从那个雅出国以后都在不停写,包括与我母亲结婚之后。整整齐齐地按时期顺序码好,折角都没有一个。倾诉他的不舍他的思念,每当他看我母亲不顺眼时,他就用这些寄不出去的倾诉,对着他理想的情人,在想象中补偿他的勉强和落寞。
“我给我女儿取名为思雅,就是为了思念你。”我看到这一句时一阵恶心。多年后当我熟谙男女之时,我能更清晰勾勒出父亲伏在案前写这句时那被柔情激荡得潮红的脸,恶心加剧。
我的母亲该如何心如刀割?这么多年我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原来一直是一个活动的伤害。并且这个伤害一天天在长高在壮大,她眼睁睁看着却不能灭绝。有时候我在纸上一遍遍写我的名字,一遍遍瞪着它,憎恶它就像憎恶我自己。
“妈!你还给他留着,你就该撕个粉碎!”我质问我母亲。我的母亲不说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生意(4)
6)我母亲在首次向我父亲示爱后被铁锹割伤腿哭不能止,一定是因为她已预感到她的无能为力,预感到他日她再努力她的爱也是不得其所。最痛苦的事莫过于预感到痛苦,却又不能绕它而过。
我母亲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她和我父亲的差距,但还是忍不住要向它挑战。
我父亲出生名门,父亲是美院的名教授,留过洋,画花鸟画,后来成了资产阶级腐朽右派,还在上学的我父亲于是受了牵连。落入淤泥后不影响我父亲依然像高贵的莲花,远远的高高的,照的我母亲更抬不起头。
结婚那天我的外公一直阴着脸,老秀才已开始为他女儿的高攀忧心忡忡。这个他们村最后一代私塾先生,我外公在“批林批孔”中也被冲了门抄了家。同样拿教鞭,同样被斗,同样低头认罪,但抬起头时一定是美院教授高人一等。老秀才有先见之明,也有自知之明,他只希望他女儿嫁个平等的人过得幸福安稳。
我母亲只跟我外公学了孔孟老庄,识得的几个字让她能在村里当小家碧玉,但在我父亲眼里跟文盲无异。她听不懂他吟诵的唐诗宋词,不会像他一样能出口成章,更不会遛两口英文。
生下我之后我父亲更不愿把脸对她,只给她脊背,用脊背传达他的冷漠或不耐烦。夜阑人静时他向他那位听的懂他的爱人倾诉悲曲,给她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抒私情或抒怀才不遇。他还给她用英文写雪莱的《心之灵》,他与其是在悲怆禁于修道院的爱米丽,不如是在悲怆被禁的自己。
他一定觉得是我母亲囚禁了他,他一定觉得没有破禁离她而去是对她最大的善意。
我的母亲丝毫不介意。她一如既往地仰望他,在他念诗的时候垂手而立,竖着耳朵努力吸收,在他马上要转给背时立刻识趣地退出去。她像个丫环,连妾都不如。她又远比丫环做的有感情。她每天盯着她的老母鸡,每早要掏一个鸡蛋给我父亲做营养早餐;我外公起早贪黑匝回的泥鳅小河蟹她抢一大半过来给我父亲滋补。
“唯养女无用哦。”她瘦的皮包骨,腿上泥还没干的老父亲直叹气。
“我就是爱你爸爸有才,他画画好。”我母亲总对我说。
我冷笑。我笑她那个爱字。我连对陆平都只说过一次爱。
我的母亲说爱这个字时嘴唇很小,很朴实和洁净精微的样子,但又像珠落玉盘一样清楚。这就是她对我父亲的爱:不宣扬,谦卑的,但一点不含糊。就像她伺候我父亲完后烧的那些小瓶子,那些乳白色的观音宝瓶,长水滴样的两公分大小,不起眼,但每个环扣和弯曲都纤毫清晰。
她烧那些彩色玻璃时神情极专注,仿佛把对父亲的爱也融入那些玻璃里,她眼含笑意,镊子在她手里灵活运转,而每次她手里都能绕出一个小动物或小瓶子,都跟她原来想要的一样。
她只有在这些玻璃里才能如愿以偿。
我有时在想,她会不会有时在跟它们沟通,而且沟通很好,她一定期望她和父亲之间能像她和它们之间一样沟通好——一种精神的弥合,她也许曾经暗暗奢望一次。
我一天天长大后渐渐通晓,男女之间不仅有精神的弥合,还有肉体。这多少有点解开了我对我父母的疑惑。我的父亲对我母亲不理不睬,竟也跟她过了十六年。精神的弥合双方对彼此都已无指望,多少会有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也许在身体的交战时我母亲是个够格的对手。
我的母亲,当我第一次以大人的眼光审视她时,我发现她原来那么美。娟秀的瓜子脸庞,皮肤白晰,乌黑的眼仁和红嘴唇一小点,就像她的名字,有兰花的清雅之气。她的身材在年轻时应该更是苗条丰满的,褪去衣服在床上坦诚相对时,我骄傲挑剔的父亲也许能发现她竟符合他的审美。
我又想起我五六岁时深夜里那场暧 昧的晃动。还有再往后我有时清早见到母亲走出卧室时她脸上的笑容,哼着小曲。蕴藏和涌动了一夜的笑容和曲子,早上散发出来时还冒着热气。我的父母用身体找到了交好的方式。十六年,白昼死一般冷寂疏离,夜晚过年一样欢愉亲密。人生真够奇异。。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五章 生意(5)
7)我有些累了,被回忆消耗的。我的思绪纷乱,往事像蛾虫一样纷纷扑打在我的回忆之窗上,我不知道看哪一只。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它让我得以解脱片刻。
但它不是我生命将终还在期盼的那个电话。不是,不是我听到了才能瞑目的消息。
“宝贝,你今天过的如何?”老周的声音使我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来。
“是你啊。”我轻松地说。巨大的失望同时也包围了我。
“怎么听着很失望的样子?是在等别人电话吗?”
“我还能等谁电话?我不是被你全包了吗?”用这种模式跟他对话我有某种快意。
“又来,哎。”老周在那头叹气。
“怎么又叹气?”我不耐烦地问。那是上个周末,冬日早晨的阳光透过这栋高楼65层的玻璃墙射在我的座位上,我眉皱的更紧,我一向讨厌阳光。
“因为你总不肯正经说话。”他说。
“我很正经呵,你不觉得我说的都是事实吗?我们之间的关系。”
“又来又来,咳。”
东升的旭日移到他头上,映出他的几根白发。我不忍再气他,手伸过去摸他的头发。他定期染头,说是显的年轻些,不至于太折磨我的眼睛。这一次白头发抢在他行动之前先活一天是一天。
“你看,头发又被你气白了几根,真不嫌我老啊。”他打趣。
“不嫌。”我说。
他一听更开心,有点孩子气地把头凑近了些让我摸。我心里升起一层淡淡的温暖,这样的调 情就已很好。
可怜的老周,不知道我出院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攒地西泮片,100粒够长眠不醒了吗?还是200粒?想到这里我把老周的头搂紧。
“喲,大庭广众也不知道含蓄一点!”车小梨格格的笑声在她之前先到我们座位边。
“还就不想含蓄!”老周把头钻出来,索性抽出手臂将我揽进怀里。我也泰然自若小鸟依人地像依偎在终身依靠一样依偎在老周怀里。我有时候喜欢他这样老夫聊发少年狂。
“哈哈哈。”林福海跟在车小梨身后。
“福海我要喝酸奶,原味的!”林福海颠颠地先去取餐区取酸奶。
“选哪一套选哪一套?”车小梨没等落座就把一本光溜面的彩书铺开在桌上,翻开给我看。
“精装修,跟这图拍的一样,就在朝阳公园边上,350万拿下。”
我浏览过去。“都挺好。”
“你给我拿拿主意呗!你比我有品位。”她敞开脸对我笑。
“周总你不是也想给思雅买一套嘛?正好今天就挑一套,我们还能做邻居!”
老周捏捏我肩膀,朝照片努努嘴,潇洒地说:“要不就选一套?”
“不了。”我说。突然厌恶涌上我的心头,黄连一般苦,沤在那里不散去。老周每个潇洒的样子都让我厌恶,它们提醒了我,原来我真的是卖了价格。
老周不再勉强。我的那些心思逃不过他眼睛。他这点不错,聪明,让玩伴省心。
林福海颠颠端着酸奶回来,车小梨接过来一口气喝了两口。
林福海和车小梨看上去像真夫妻,都是福态憨厚的无锡阿福相。车小梨这一年日子过的舒坦,胖了不少,双下巴微微挂下来。她现在地位已固,皮相已不那么重要。林福海广东农民出身,炸过矿石卖过假药,在深圳盘锯多年,后来靠开连锁餐饮发了家,一路过来也是腥风血雨,憨厚也只是表象。但他没读过多少书,会写的字不比他名字多多少,比不上老周名牌大学生物学博士。
我看看林福海,再回望老周,还是老周更胜一筹。我轻叹口气,竟有点侥幸,我竟也不至于沦落到底,老周有的至少能满足我的虚荣。
车小梨也只是母鲨暂时收起牙齿而已。这一行不是好干的营生,血淋淋斯杀中闯过来,牙齿早已磨得锐利。
第六章 生意 (6)
8)
我有点怀念刚认识时候她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俩都还干净得像新开的天与地。林福海那时候还瘦,扁平的鼻子占了黝黑的脸大部分,七零不到的个子顶着四方脑袋隔一个礼拜来一次。来去都风尘仆仆,走的时候车小梨倚在门口依依不舍望着,那情态像一对并肩打拼的患难夫妻。
有一天她门口来了一队壮汉和妇女,气势汹汹,由中间一个中年妇女领着,跟林福海一样扁平鼻子和精瘦。一张厚嘴唇的阔嘴开口就骂,一边骂一边给开门的车小梨一记耳光,将她扇回屋里,她的随从一拥而上。
一会儿屋里传来车小梨凄厉的惨叫声,伴随着有东西像水从四面八方泼到水泥地一样清脆的碎裂和四溅声。
屋外很快站满了同楼层的居民,交头接耳但都站着不动。“又是一个大奶找上门的!”“我猜对了吧,那女的果然是干这个的。”“干哪行不好干这丢人现眼的,活该!”叹口气,笑笑,看差不多了后搓手走开。
后来我是在床头柜的墙角边找到了车小梨。她瑟瑟发抖缩成一团,两只手臂紧紧交叉着护着胸部。衣服几乎被撕的稀烂,一块布片耷拉在她手背上,露出白晰的胸部几道像刚用红笔划上去的刺目的血印。她不说话,眼睛直愣愣地盯地上。
几分钟后我才发现她的下身下面的白瓷砖上印上了血,血不停从她的裤裆往外渗。我扶起她艰难穿过屋里的废墟将她送到了医院。她后来在里面住了半个多月。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车小梨恐惧的眼神。
“喂喂,你盯着我这么出神干嘛呢,我又不是你的老周。”
“啊。”我回过神,傻笑。
手机这时铃声大作。“思雅姐——我是小雪。”那头传来甜腻的声音。我有点厌烦,最近这个小女孩隔天就给我电话。
“嘻嘻,我是想问问马总的事。他最近有时间见我了吗?”23岁的小女孩从来就直奔主题,一点不浪费青春。
“噢,”我说,用一副为她着想的语气,“你不觉得马总年纪有点不合适吗,45岁。。。。。。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不会不会。。。。。。男人嘛,年龄不是问题。思雅姐您不也夸马总优秀有魅力嘛。我相信您的眼光。我还盼着见见他,多跟他学习学习呢。您。。。。。。”
我有些头疼,不想再费口舌。“我现在说话不方便,回头打给你。”
“唷,拉上皮条啦!”车小梨嘻笑。
“跟我们不一样,人家那是可以明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