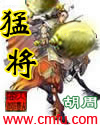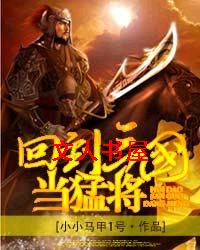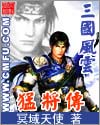猛将-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世友住在南京时,聂凤智隔三差五要去看望他,陪他聊聊天,或是一道坐在池塘边钓钓鱼。后来,许世友提出要找几个人帮他写回忆录,从筹组写作班子,安排写作计划,到解决写作班子写作和生活上的种种具体问题,均由聂一手操办。
对回忆录的送审稿,聂凤智谈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最后全书定稿,也主要是由他拍板。许世友本人非常满意,未加改动,他除了讲之外,只在首页签下一个写得大大的“许”字。
许聂之情,胜过兄弟。
许世友喜欢狩猎,在晚年,就是身患重病、步行困难时,也要坐在车上指挥身边人员进行狩猎。他说:“狩猎可以减少身上的病痛。”
可他终究老了,身体不好,因此,“打猎”也只能在汽车上“打”,渐渐,除了手下几个秘书、警卫外,没有人愿意陪他去。因此,他常常邀聂凤智陪他一同狩猎,以减少病痛。聂凤智体谅老司令的心情,尽管自己不仅有肺气肿,而且还有癌变的病灶,连呼吸、行路都感到困难,老司令有求必应,他必定驱车陪同他去郊外狩猎,就是时间一长,老司令没有来“喊”去打猎,他倒反过来,在老司令那里坐一会,坐着坐着,“兴致大发”地说:“老司令,好久没出去了,您是不是陪我出去一趟呀?”
“去哪?”老司令懒懒地问。
“去打猎玩玩,好久没去了,心里就是想。”
这下许世友高兴起来了:“明天早点起床去!”
知情人说:“聂凤智对老领导具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29。老首长与老部下的一次“推心置腹”
刘奎基是当年在周村战斗中率领73团7连突击队首先攻入城内的战斗英雄,他是聂凤智的老部下,也是他的爱将之一。1988年,刘奎基去拜访老首长聂凤智。
这次谈话,聂凤智“屏退”了所有的工作人员,与刘奎基“推心置腹”。
他说:“奎基啊!古人云:人之将老,其言也善,我久卧病床!时常陷入反思之中。我这一生要强逞能,没有遇到难倒我的仗,随着仗越打越大,人也越打越聪明,官也越当越大。才能,我有那么—点,功劳,也有那么一点。可是怎么认识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怎么摆正自己在胜利中的位置,这不是个容易的事啊!我深深感到,若以功臣自居,背上这个包袱就太重了!”
“老英雄”刘奎基被“老首长”提出的问题所震动,说:“首长戎马一生,打了那么多的胜仗,我们永远忘不了首长的功绩。作为您的部下,我们都感到骄傲。”
“唉,刘奎基,你不懂。27军是个好部队。我和你们共同战斗的岁月,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历史。我对27军有强烈的感情。27军的历届首长和老同志,也多次邀请我回部队去看看,我很高兴,可是,正因为有了这种感情,我也时常提醒自己:27军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它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假如我们这些老家伙老是念念不忘那是我的老部队,而且把关系拉得很紧,总想去左右他们,这就超出了正常的感情了。也难免有那么一些人,又口口声声地称自己是某人的老部下,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几百万解放军会成了什么样子呢?”
他略微停了一下后,又一字一顿地说:“这就是拉山头了!这是后患无穷的事呀!”
言罢,他言犹未尽地摇摇头,自言自语似的说:“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军队要搞五湖四海’。”
聂凤智的话讲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原则问题。他是有感而发的,可他又不便细讲。刘奎基领悟到老司令的思想,但还是想把老司令从这个严肃的问题中引开来,半开玩笑地说:
“首长,人家也说您在位时,用了不少27军的人呢!可是,27军不少的老同志对您还一肚子意见,说您不关心部下。”
“是啊!”老司令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位时,确实任用了一些27军的干部,可也怠慢了不少27军的好同志。用之得当的有,不争气的也有,可是哪一个我也没有把他当成我的人。相反,我退下来后才发现,该用的而没有用的也不少。我时常为这事责备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议论,大胆录用,在这个问题上,我缺少了战争年代的气魄。”
接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要是他这个将军与他的士兵、他的部下的关系。最后,他说:“将军与士兵的关系,能不能摆正,也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
“仗,是士兵打的。胜利,是士兵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再好的指挥员,没有士兵的冲杀,还是纸上谈兵。我非常感谢英勇善战的27军的广大指战员。没有他们,就没有我这个将军。我写了本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这个战场的大舞台,主角是千千万万勇敢的士兵。在赫赫的战功面前,在耀眼的荣誉光环里,往往看不清这个问题,摆不正这个位置。我已是古稀之人了,经常回首往事对这个真理问题,看的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将军征程百战多,有的人争功、抢功,把自己仅仅参与的战争的胜利全归功于自己,有的人在某场战斗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把胜利的根本往自己身上“挪”,一个政委的作用超过司令员,一个参谋的贡献比首长还大,甚至一个后勤人员在一次具体的战斗中对于胜利的贡献超过前线的战士们,而聂凤智,一位从15岁开始,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东南沿海的与美蒋较量,他是从打老蒋到打日本鬼子,再到打美国鬼子,我军每一个时期的重大战事,他都参与,并且有重大贡献,战场造就了一位将军,但是他却把自己归功于自己的士兵,在耀眼的荣誉光环里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难得的品质。聂凤智的话是情深意长,也可以说是对自己一生成就最深刻的总结。最后,他对老部下说:
“对27军的同志,你替我捎个口信,问他们好。告诉他们,27军是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部队,我祝贺他们取得的新胜利。告诉他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切莫骄傲啊!”
停了一会,他又长叹一声:“人的一生,在党的培养下,在人民的哺育下,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功劳。我想,当要离开人世时,还是不要背着功劳包袱走,功劳归于党,功劳归于人民,功劳归于千千万万的士兵。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小时父母去世,跟着叔伯长大,没上几年学,一切都是党给的。所以,还是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去见马克思,去见毛主席好。”
这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他的心声,也是一位将军对自己的人生、对社会和人事、对党对军队的最深刻认识。这也是将军最内在的情怀。如果说,聂凤智一生战功赫赫,少有人及,但他这番对于“功劳”的认识,更是少有人及的。将军之所以成为将军,他征战一生,为官多年,没人骂,没人恨,并且被人们敬仰,这大概就是他办事公道、处事公心的根源吧。
。 想看书来
30。将军暮年情
(1)
1982年,在北京开会时,聂凤智病情较重,哮喘厉害,严重缺氧。
由于会议比较重要,聂凤智坚持参加,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在下榻的京西宾馆做输液等治疗。一日凌晨4点多钟,他起床去卫生间,一下子摔倒在地,面色紫绀,肥大而发紫的舌头几乎堵住了整个口腔。呼吸和心跳十分微弱。护士一边忙把氧气送至他的鼻腔,一边向外间随行人员的卧室跑去。
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正好出差在北京,在他的指挥下,将聂凤智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聂司令员醒过来时,开玩笑地说:
“你们大惊小怪,我只不过是睡了一大觉。”
这次会议后,由于病情反复的频率加快,次数增多,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难以适应工作需要,就主动向军委递交了请退报告。
开始,军委没有同意,挽留他说:“你是司令员,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了,多注意休息,还可以再干几年。”
但是,聂凤智说:我退了,有利于年富力强干部上来,对部队建设有利。”还是连续递交了第二、第三份请退报告。
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聂司令员的身体状况,为了他的健康,批准了他退居二线,进入中顾委工作。
1982年10月,聂司令从南京军区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
(2)
1986年6月,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癌,病情恶化排痰困难,切开了气管,住在北京301医院。当年的警卫员单文忠去看他,聂凤智一见他就问:“你怎么也知道了?”
单文忠说:“老团长孙同盛告诉我的。”
“怎么,都害怕了?认为得了癌症就得死?”聂凤智非常有信心地说,“死不了,两个月就回南京,哪有那么简单就死了?过去打仗那么危险都过来了,这次死不了!”
结果,两个月后,他真的回南京了。半年下来,竟出人意料的好了,生命又延长了5年之久。
(3)
—次,聂凤智的老战友贾若瑜去南京,给何鸣通电话,询问聂凤智的身体状况,问她什么时间去看望他比较方便。何鸣告诉说:
“老聂正在治疗,待治疗后我告诉他后再定。”
贾若瑜说:“现在不要打扰他,待他结束治疗后,我再去看望他。”
谁知,聂凤智一听说贾若瑜到了南京,治疗刚刚结束,就到华东饭店来看他。他是步行上楼的,呼吸都十分困难。这使贾若瑜十分感动,说: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应该是我去看你的。你是重病号,又是老大哥。”
他笑着说:“我虽是个重病号,但还能走得动。你远道而来,我更要亲自来看你。我的病,我自己心中有数,你不用替我担心。”
其实,他的身体己被病魔折磨得十分虚弱,十分消瘦,由于肺癌,他的喉头下方的气管已被切开,插上管子,固定在脖子上。他曾经若无其事,幽默地对人说:“你看,我成了无孔不入的人了。”
聂凤智病成这个样子,仍时时关心着他人。他听说南空原司令杨焕民重病住院,套着脖子上插管,硬是坚持着,专程到空军454医院,爬上三楼,看望了杨焕民。他这副打扮还到南空大院,看望了吴肃(原抗美援朝时期的空联司参谋长)、叶泰清(原空联司副参谋长)、王明礼(原南空副参长)、张雍耿(原空军顾问)、李发应(原南空顾问)等老同志、老的战友。
(4)
1986年,聂凤智被301医院诊断为肺尖癌变。因长期患慢性支气管炎,两肺纤维化不宜手术,只能放疗及化疗,以后又进行气管切开。自他退下来到病逝,长达10年的时间,不要说因肺癌而进行的放疗及化疗,每天多次打针,吊水,只说气管切开后,气管切开的套管随着他喉部的动作上下移动着,都难受。
套管每日要清洗,一天4次更换管子,仅从1989年10月20日到他病逝的895天里,共更换了3580次。如果再仔细计算拔出1次,插入1次,就是7160次之多。护士都无法想像他是如何忍受这样痛苦的。一天,见他精神尚好,护士向首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每次给你更换管子,你都像没事似的,难道不疼吗?”
这时,聂凤智说:“我问你,如果你的小手上插了一根刺,扎进去和拔出来痛不痛?”
他又接着说:“那么粗的管子在刀口里抽出插进,每天8次,哪有不痛的?然而,病痛对革命者来说,它就像你拉橡皮筋那样,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人的意志坚强了,是可以战胜外来困难的。再者,现在的痛苦比起战争年代的艰辛,又算得了什么呢?”
(5)
1992年临终前的一天傍晚,聂凤智已处于昏迷状态,神志不清,突然挣扎着要下床。护士不让,他就大吵大闹说:
“现在是建国30周年,敌人在千方百计企图侵略和破坏我们的国家,这个情况我要向小平同志报告。”
护士说:“你现在生病,不能起来。”
他说:“不就是战伤吗?没关系。”
在弥留之际,他想的仍然是党的事业、国家的安危。
1992年4月3日下午,聂凤智战斗的一生戛然而止,终年78岁。
。 最好的txt下载网
1。洞房花烛夜逃出家门
1913年8月,周希汉出生在麻城县周家坳。他的父亲叫周祁耀,30岁前曾娶妻并生有一子。可惜那孩子两岁时暴病夭折了。不久,妻子也贫病交加,不治而亡。
几年后,周祁耀才“疗”好伤,续弦娶了李氏;然后,夫妇俩租种了本村地主的几亩山坡地,早起晚睡,不分白天黑夜干起来了,可是劳作一年,还是难得肚子饱。脑筋活络的周祁耀不甘心,在农闲时,又干起了打铁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