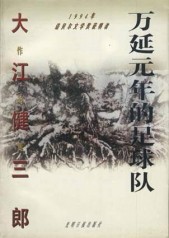女子特警队-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木板瓦房,中间夹着一条泥土翻浆的小街,就是几座大山的行政中心,一条前年为了致富才修的土路从乡里穿出去,打屁般的拖拉机用最快速度开,也得跑将近五个钟头才能抵达县城。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衰朽的老关帝庙大院里,各个与农业有关的基层机构中,也不缺乏武装部,大院中间是石坪,院子里鸡啼猪跑,一张红纸贴在武装部房间的窗框边:“保家卫国,参军光荣。”说明每年例行的征兵季节到了。
耿菊花赶到关帝庙时,正看见十多个少女在武装部的窗口前排着队,她赶紧侧身挤进去,老老实实地站好。她穿着一件脱了线的红毛衣,山里的日子虽说不富裕,但青春的身体还是发育得很好,如俗语说的,是处在“喝凉水都长肉”的花季,胸脯把毛衣撑得满满的,脸蛋红扑扑地冒着一层油汗,几粒浅浅的雀斑分布在鼻子两旁,不但没破坏什么,反而显得更加生动和纯真。她看前面的姑娘,人人脸上洋溢着笑意,听说这次是招女兵,是么子特种军队,肯定是大碗吃饭,大盆喝汤,啊哟我的娘老子呃,这会为贫寒的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巴,也能顺便去看看山外好大好大的世界,这是多么子有意思的事情。
阳光把姑娘们的影子在石坝上拖得好长,她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时不时互相捅一下身体,笑得捂嘴扭腰,无拘无束。耿菊花与这些姑娘都不认识,她自顾沉浸在粉色的遐想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惜耿菊花的好心情未能持久。一个少女从不远的“乡党委办公室”出来,姗姗走向这里,她表情倨傲,似乎是这个山区的公主,对大多排队者不屑一顾,一看就知道是乡干部的女儿。排在前面的几个姑娘立刻给她让出一个位置,笑脸里带着毫不遮掩的阿谀。末尾的耿菊花为此大为不满了,她虽然住在山旯旮里,但也有一股大路不平旁人铲的脾气,她直率地叫道:“咦,讲礼性哟,先来后到哟。”那个少女慢慢转过头,蔑视地扫一眼她,问旁人:“她是谁?”给她让位的姑娘们都摇摇头:
“谁知道,天还没亮就来了。”
“看那样子,一定是鸡鸣乡那块鬼都不下蛋的穷村来的。”
那姑娘两眼看天,问耿菊花:“也想当女兵?”耿菊花也两眼看着天,回答道:“那又怎么样?”公主哼一声,不紧不慢地说道:“满口包谷味,也不在水塘里照照自己是什么模样。”耿菊花没想到这个长得不难看的姑娘会是这么说话,吃惊使她一下子找不到反击的武器。公主胜利地笑了,添一句道:“不要随便做梦,回村挖你的月亮锄去!”耿菊花胸脯起伏,突然一声大叫,冲向少女,用着蛮力一摔,少女立刻跌个嘴啃地,两人马上在地上扭成一团、少女被压在身下、苍白着脸大喊:“打人啦,山蛮子打人啦!张妹儿,刘小梅,你们就这样看稀奇啊?”
几个观战的姑娘一拥而上,抱的抱扯的扯,耿菊花不是对手,顷刻之间反被压在众人身下,但她毫不屈服,声嘶力竭地反抗着,撕打着。
五十来岁的乡武装部长从室内跑出、他胡子拉碴,披着一件象征着他在山里的特殊身分的褪色的黄军装:“干什么,干什么,啊?再这个样子,我一个都不登记!”
姑娘们慢慢从耿菊花身上爬起,耿菊花坐在地上,一脸土灰,脸上是不屈的表情。她突然一跃而起,对着部长嚷道:“你凭什么不给我登记,你一个大人也欺负我?我比她们都行。”部长本没把她当回事,一听这话反而注意到她,说道:“呵?还有脾气。那你说,你比她们哪里行?”耿菊花眼睛四面搜索,看见了院子边上丢弃的一扇石磨:“我们来举那个。”部长转脸问刚才压着耿菊花的几个姑娘:“比不比?”几个姑娘望而却步,那个打架的姑娘却不服输:“比就比。她先上。”
耿菊花上前抱起石磨,一使劲,举过头顶。
姑娘走上双手抱住石磨,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完了,只举到胸前,她那一方的姑娘齐声大喊:“李琼,加油!李琼,加油!”她涨红着脸,吸口气,再一使劲,石磨被颤巍巍地举过头顶,为她加油的姑娘们一时欢腾雀跃。
她拍着手上的灰尘,骄傲地喘着大气问:“还……还有吗,鸡鸣乡的……人?”耿菊花眯着眼睛,慢慢从身上掏出一根铅笔那么长的橙黄发亮的竹管,向武装部长道:“我可以站在这儿,不用手,把那个打下来。”她指的是二十几步外房檐下挂的一串红辣椒。部长不信:“你?”姑娘们起哄:“吹牛不打草稿哦,快点快点走开哦!”
耿菊花不理她们,从地上捡起几颗包谷籽,吹去浮土,含在嘴里,咬住竹管,猛然一个狮子甩头,噗地发力吹出,几粒包谷籽疾箭一样射去,只听“绷”的一声,拴辣椒的细绳被打断,辣椒刷拉拉地散落在阶檐上。
一瞬时,整个堤坝鸦雀无声,只有阳光中的山风呼啸而过,吹得衰朽的房檐上空一根伶仃的电话线发出豁朗朗的响声。
部长盯着耿菊花,惊讶中掩饰不住赞叹,“好。”他一锤定音,“后天去县里目测,我在这里等你。”
后来几天在耿菊花的感觉里,极像一首欢乐的山里小调,那么轻快、那么惬意地飘荡在生活中,她跟着武装部长去县里,尽管经过精心收拾,她还是显得很土,但县武装部里一个说着远方语言的“军官叔叔”详细听了乡武装部长的介绍,又叫她表演了吹管射物,再让她跑、跳、爬树、上墙,直把她折腾得精疲力竭,都以为自己要坚持不下去了,那个军人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好,”他说,“等着明天体检。”体检一过,紧跟着又填写无数的单子。终于,今天她到乡里武装部去,从胡子拉碴的部长口里得到准信,她被录取了。
这个夕阳衔山的黄昏,耿菊花爬上一道山梁,飞跑下沟,顺着石板小路走回自己的茅草小屋。在山垭上她碰见了既是本村村友又是初中同学的王改英,王改英听说了耿菊花报名当兵的事,大为赞叹,王改英是村里一支花,长相在山沟里独领风骚,那双秋水葡萄般的黑眼珠向男娃们一瞟,把他们的心尖尖悠得生疼。王改英家境贫寒,她说她也要到千里之外的省城去发展,是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去那里的建筑工地,王改英与耿菊花约定,到了省城,各自好生奋斗,不混出个人模狗样那是枉做了一辈子女人。
迄今为止,耿菊花还没有把报名的事讲给爹和哥哥听,她尚未拿定主意,到底是走之前给家里留一张纸条呢,还是临离开的头天晚上再告诉。她回到光线幽暗的屋子,看见长着绿苔的水缸里的水已经不多,立刻挑起水桶去担水,从几十米高的坡下挑着百余斤的水桶回来,她嘴里竟哼着自编的小调。将水倒入水缸后,又一蹲身在地上铡起了猪草,她从小苦惯了,做活儿是她的本分,不做活儿反倒浑身难受。
里屋内那张破旧的木板床上,躺着生病呻吟的爹。肮脏的土墙上,挂着两支生锈的猎枪,许多年前,爹是一个山里远近闻名的好猎手,后来野物被山民杀光了,再后来爹为撵可能是山里最后一只野獐子摔了岩,成了终身残疾,爹就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废人。爹也苦啊,下星期离家前,还是应该先给爹说一声,至少,我是他的亲生女儿呀。
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从门前的小道一摇一摆地走上来,耿菊花一眼看见,好心情立刻荡然无存,妇女是卧牛乡方圆二十多里地名声不小的徐媒婆,她也看见了耿菊花,多皱的脸上立刻展开了笑颜:“菊啊,你爸在家吗?”耿菊花鼻子里毫不掩饰地哼一声,转过背不理睬,手里的刀舞得更加有劲,嘭嘭嘭的铡草声在空旷的大山里碰出恶狠狠的回音。
徐媒婆大人大量,宽容地一笑,进屋去了。恰在此时,耿菊花的哥哥背着一大背柴回来,看见徐媒婆的背影,赶忙跟进去招呼:“徐三姑婆,你坐你坐啊。二妹哩,”他张望着向外急急地道,“给三姑婆喊一碗茶来。”耿菊花不理,埋头铡自己的猪草。徐媒婆大概对此类事经得多,见惯不惊道:“耿家大哥忙啊?上回说的那个事,成了。”菊花的哥哥欣喜地搓着一双大手:“我们过两天要好好道谢徐三姑婆哩。”徐媒婆成竹在胸,又要装出一副任重而道远的艰难模样,瘪瘪嘴道:“人家愿意把三妹子嫁给你家,不是想你们这儿山好水好有吃有睡,我直肠子放粗屁,你们这个穷窝窝,哪个闺女想来啊。”菊花的哥哥知罪般地赔着笑:“那是那是,让徐三姑婆受累了。”徐媒婆一扬脸:“不过人家黄家有个条件。”
床上的父亲撑起半边病体,一脸的惊骇:“还……还有条件呀?”
徐媒婆用眼向门外的耿菊花一抡,姑娘健壮的身体在秋日阴黄的寒天下是那么饱满,仿佛一汪蓄满了青春汁水的静湖,只要有人开闸,就会流泻出势不可挡的洪波巨浪。徐媒婆收回盯视耿菊花的眼光,拿捏着说道:“人家那边也有个大哥,那边的条件吗,跟你们鸡鸣乡一样穷,也不好娶媳妇啊。”父亲问:“那他、他黄家的意思是?”徐媒婆伸头向着父亲,隐藏着略带狡黠的神情,压低嗓门道:“换亲。黄家的三妹嫁过来,你家的菊妹子嫁过去;这不就两全了吗?”父亲和哥哥一愣,一时开不了腔。父亲大声咳嗽起来。
屋外的砍刀声刷地止息,哥哥不安地伸头向外一望,只见妹妹把铡刀往砧板上狠狠一甩,刀锋嵌进木砧,颤巍巍地抖动,发出一丝刚性的啸音,耿菊花跳起身,耸身向屋后的大山深处跑去。
哥哥是知道妹妹的性子的,妹子平常话不多,但一旦有了主意,那是九条大牯牛也拉不回的,他赶紧追到屋外喊:“菊花,二妹!”
山风呜呜,耿菊花的身影跑过小道前面的一堵石壁,茂密的山石树木后只传来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哥哥不敢怠慢,这不只是关系到妹妹的脾气的事,而更是关系到他娶不娶得上黄家的姑娘来当媳妇的大事!妈妈生病死得早,爸爸又摔岩伤了身子,妹妹终究是别人屋里的人,这个家没有个女人,谁来承接耿家的香火,谁来支撑缝补浆洗的一摊子家务杂事。哥哥向徐媒婆道一声得罪,嗖地一声窜出门,向大山上追去。
耿菊花的身影在荒草丛中闪现,哥哥边喊边加快自己的脚步。当然,论起山里的起居坐卧,女人一般不是男人的对手,哥哥跑起来如同敏捷的羚羊,逢沟跃沟,遇坎跳坎,终于把一味疯跑的妹妹堵在一道三米高的崖坡上。
耿菊花往崖下看了看,犹豫间,哥哥已站在面前,哥哥喘着粗气,妹妹也喘着粗气,两人对视着,白云从他们墨黑的瞳仁里飘过。“二妹,”哥哥仿佛理亏一般,说话时没有了追妹妹时的那股硬气,“你……你就成全了哥哥吧。”耿菊花倔强地拧着脖子道:“不。”哥哥苦着脸:“妈死得早,爹又瘫了,你终归是要嫁人的,以后你走了、没有一个女人,谁来伺候爹?”耿菊花犟着脸道:“那也不能把你的亲妹子往火坑里推,他黄家大狗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好吃懒做在卧牛山一带出了名的,哥,你就饶了妹子吧。”哥哥凄苦地垂着头,半晌道:“你不去,哥哥也娶不上他家黄三妹,你不看在哥面上,也要看在瘫了的爹身上啊。”耿菊花向后退了半步。伸颈向再无退路的崖坡下一看,突然就跳了下去。
哥哥大惊,冲上去大喊:“菊花!二妹!”
耿菊花在下面已爬起来,脚脖子拧了,但她倔强地一瘸一拐地向远处走,嘴里竟胡乱吼着一首三十年代这里闹红军时流传下来的一首山歌:“咦哟……老子本性生得犟,家住川东巴山上,是死是活跟红军,要把白匪消灭光。咦哟……”她一边全力吼唱着,一边流着愤怒的眼泪。
哥哥看天上,太阳晃眼,他双膝一软,跪在山风呜呜的荒草中。
第二个星期说来就来,同时来到的还有连绵不断的山雨,在这座大山里,秋天是霉雨的季节,淅淅沥沥,无穷无尽,有时要连下大半个月,下得人的脑子深处都要长霉。
这个雨天里,耿菊花的哥哥在服侍爹爹喝药,他从火塘上端起药碗,走到父亲床边,刚让爹干缩的嘴唇沾住碗沿,就听外屋猛地一声响,他们同时一抬头,原来是一身稀泥的耿菊花抱着一包东西冲进堂屋。
哥哥生疑地问道:“你搞什么名堂,拿的什么?”耿菊花幸福地憨笑着,一层层打开,原来是一套武警新军装。“哥你看你看。”她忘情地叫他们,“快看呀。”哥哥上去抚摸着,眼睛都直了:“这么好的料子啊,怕要值好多钱呢!”耿菊花道:“所以不能叫它淋湿了。”父亲在床上叫:“菊花,菊花哩。”
耿菊花边揩头发边应着进去,说道:“爹哩,我们发衣服了,明天就到乡上,然后去县里集中哩。”父亲咳嗽了一阵,好不容易说道:“娃儿哩,这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