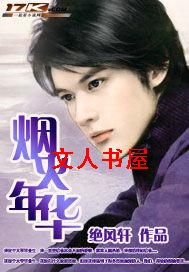北京胡同年华,那些不得不说的事-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序
现在北京还有多少平房?还有多少胡同?还有多少大杂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都在慢慢减少,慢慢的消失不见。在我心中对于平房大杂院的生活总存在着一种复杂又微妙的感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强烈,这种强烈的带着浓厚个人色彩的怀念之情促使着我写出了这部小说。在动笔写这部小说之前,我考虑了很久,我在想我到底该把这部小说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在开始写前几章的时候我并不是很确定,可越往后写我越加确定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这部小说的关键词:
老北京的胡同。
老北京大杂院春夏秋冬的生活。
在平房长大的八十后的一代。
青春。
这部小说是以回忆的形式写的,故事开始在二零零一年,结束在二零零二年,书中的内容一半是虚构的一半是真实的。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更加确信小说是绝对来源于生活的。书中的主人公是几个青年人,之所以选这个年龄段的人作为主角,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他们想到的完全是和成年人不一样的,从他们身上更能完整的折射出胡同大杂院的生活,另外在人物对白上也会显得更加自由和诙谐幽默。
把这部小说献给那些在胡同里生活过或正在胡同里生活的人们,献给那些对胡同大杂院生活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们,献给在胡同里长大的八零后的一代,献给那些曾拥有“恐龙特急克塞号”和“变形金刚”童年的一代,献给那些曾经在胡同里丢沙包跳皮筋的一代……
零 琐碎的记忆,崇文区东打磨厂儿
二零零一年。
夏。
北京市。
崇文区。
台基厂。
东打磨厂儿。
打磨厂儿是一片平房,在这片平房中穿插着很多条胡同,我总是习惯把打磨厂儿叫做打厂儿。
在我的头脑中有时会突然出现时间和空间的短暂混乱,但这种混乱只是瞬间的,这种状况一旦发生,我就会搞不清哪些是发生过的,哪些是没发生过的,更为奇怪的是我也能预感到哪些是即将要发生的,而这种预感转变成真实的概率也很高。我在想,过去与现在是相互对应的,之所以有了过去,才会理所应当的有现在。而过去这个抽象概念的词语看上去是显得那么的空洞。
已经过去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瘪球,软弱而无力趴在那里,里面的空气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个瘪汽球里面几乎已经没有空气了,你只有费很大力气用力吹它,把它吹大,里面的空气才会膨胀起来,才会想起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的余悸。
要讲述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二间左右发生在北京胡同里的那些事情似乎是件很难的事,我头脑里关于那时的记忆已经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被暴烈的阳光晒干了,蒸发掉了。我凭借的只是我头脑里残留的记忆,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些记忆有些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而另外的一些,我不能保证它们的真实性,它们或许真的发生过,或许是在我梦中发生过,也或许它们压根儿就没发生过,而我却固执地认为它们肯定发生过。
二零零七年仲夏的某个晚上,我去崇文门新景家园找三百,在路过小区门口时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她很像林朵,我顿时开始慌张起来,我很想叫住她,想确定她到底是不是林朵,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如果她是林朵,如果她看见了我,她会怎么做呢?而我又会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
我到三百家后对他说了这件事,我把那个女人的外表向他描述了一番,之后我俩又进行了很多推测,仍然无法确定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林朵。
那晚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记忆又出现了瞬间的混乱。
我和林朵初次相遇的时间是二零零一年夏天,地点是Howso,位于磁器口附近的一家迪厅。
我叫蓝小雨,曾经的北京胡同串子。
打磨厂儿是一片平房,在这片平房中穿插着很多条胡同,我总是习惯把打磨厂儿叫做打厂儿。
我有时会因为自身的毛病或缺陷而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安一般会发生在一件或几件让人头脑兴奋的事情后;比如在厕所一边大便一边抽完烟后,比如在胡吃海塞一醉方休之后,比如在床上慌忙*之后,在这些情况下我都会感到焦虑不安,这种感觉会使我的身体微微颤抖,同时会觉得刚刚做过的事情是一件多么危险多么愚蠢的事情似的。
我喜欢胡言乱语,而且说过的话很快就会忘,接下来将是语无伦次而且仍然喋喋不休,我不喜欢小动物,看见狗就害怕,总觉得它会向我扑来然后胡咬一气,记得西游记里管某种动物叫孽畜,不知道它做了什么而管它叫孽畜,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儿。我小时候经常左手拿着苍蝇拍右手拿着杀虫剂在院子里转悠,看见苍蝇落下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杀死它,杀死五只后我会用纸把它们包起来,然后点燃,我认为这是一种乐趣。
我没上过几天幼儿园,因为我不爱和其它小朋友说话,他们玩他们的,我自己站在一边发呆,那时我喜欢一边发呆一边把手放在小鸡儿鸡儿上,如果我不把手放在上面,我会担心小鸡儿鸡儿会消失掉。
上小学我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我无比的高兴,但戴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每天戴这个玩意儿是个累赘,而且还得想着一周洗一次,那时我嫌麻烦索性戴上就不拿下来了,晚上睡觉都戴着,这般如此戴了一星期后脖子上磨出了一道儿印儿,之后以至于我极其厌恶戴红领巾,想起它就头疼。
上中学后我是全班最后一批入团的,我本来是不想入这个的,也许老师是因为要凑数,就把我给凑进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不定期的交团费,一直交到现在还在交。
中学毕业那年我第一次和异性亲嘴儿,那时我家旁边有块儿工地正在施工,工地上放着几个水泥管儿,是那种特别大的能钻进去人的那种,那女孩是我一个学校的同学,我俩钻进那个水泥管儿里亲嘴儿,这水泥管儿里有股怪味儿,我们一边儿闻着怪味儿一边儿亲嘴儿,足足亲了得有五分钟,如果不是有人打断我,我想我会一直亲到十分钟,一个警察站在水泥管边上问我家住哪儿,钻这水泥管里干嘛呢,我心想你都看见了还问我干嘛呢,我说外边热,这里面凉快,他问我家住哪儿,我说就前面,打磨厂儿。
我又语无伦次胡言乱语了。
我要说的事儿是在二零零一年,那年我刚成人,那年我个性很强,那年我性裕也很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 褪色的胡同
二零零一年的打厂儿跟其它城市里的小街道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北面是一小片楼群,而南面是一大片平房,这条街就好像中间的分界线。我觉得这片平房的年龄比那片楼群大,从我小时开始记事起就把这楼还有这平房记了下来,模糊的儿时的记忆感觉眼前的楼群是一片山,一片高大而不可逾越的山,这山里或许住着神仙,或许住着妖怪,或许住着外星人,或许住着地球人。记得也听说过这楼里闹鬼,小时也曾以讲这楼里闹鬼的故事为乐,这群楼就像一大片纪念碑一样,矗立在我的记忆里不会抹去。
楼对面的那片平房,在群楼面前显得有些卑微,交叉在一大片平房街区的街道中,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交结在一起,中间的空白处就是一户户的人家,他们多数都是从生下来就住在这里。那时的北京像这样的平房街区真的已经不多了,即使是现在走在那些残留的平房街区中也会发现有些墙壁上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外面再加个圈,活像一头等着屠宰的又白又胖的猪,上面盖上了一个淡紫色的戳:“合格!”猪也好,平房也好,无疑都是同样给判了死刑,一只猪死了,还有千万头猪,一间赋予了生命与感情的房子消失了是永远不可能再复生的。它们都在被写字楼,商品房,娱乐场所这样的大型建筑侵蚀着,而且早晚也会被侵蚀干净,一点儿渣儿都不会剩下,因为据说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社会的进步。
我家的院子是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不少人家,无论是院子里的屋子还是院子的过道它们都是同样的窄小。
打厂儿在雨后显得很清澈,是那种没有一点瑕疵的清澈,用脚使劲地跺一跺仿佛可以听到咚咚的回响,就好像碧绿的海面上产生了一道道的波纹。只是一场雷阵雨,很快就过去了,乌云像是被人用手抹去了一样散开了,太阳用力地挤了出来,重新把阳光散在了地上。
我在盯了一下午的电脑后,眼睛感觉就好像有一群苍蝇飞了进去,这群苍蝇把我的眼睛塞满了,撑得眼圈异常的宽大,而脑袋感觉就像让人给了一记闷棍,弄得我脑仁儿生疼。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来势汹汹,噼里啪啦的一通猛砸,震耳的雷声很好得配合着雨声,就好像二重唱。
这场雨让我感觉很爽。就像刚洗完澡后马上被空调的冷气吹过一样的感觉。
我关上了电脑。
有时电脑确实能让人发疯,当你累得要死的时候,它却一点事儿没有,看着关机前闪烁的电脑屏幕,它仿佛是在向你微笑着说,接着玩我啊。
我正要出门,电话响了,这声音特尖锐,响一声还带着一声回音,我家有两间平房,一屋一个电话,一来电两个屋子的电话同时响,很是热闹,两个电话吼着刺耳的铃声,好像都在抢着让你先接。
九十年代中期,电话开始在千家万户中普及,我家这片儿的平房特兴这种一屋安一个电话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好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了周围的几十户人家,我在胡同里闲逛时老能听见这刺耳的电话铃声,几遍重复的铃声后紧跟着就会传出一个底气十足的喂。
要出门时电话响起是挺让人起急的事,我急忙一路小碎步冲过去接电话。
是飞狗。
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喊,你丫在家嘛呢,晚上出来,烤串。
不问找谁直接奔主题,这声音就像重金属乐的第一个强力和弦,倍儿直接的告诉你这就是嗓音。
我没事儿,家待,在哪儿烤。我说。
还有哪?房顶!你就现在出来吧!
飞狗。我的发小之一。丫说话从不用大脑。
住平房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上房,虽说不是所有的平房的房顶都能上,但在我的打厂儿的生活中有一个房顶能上就已经感到挺满足的了,那些从一生下来就住在楼房的孩子肯定没有享受过这种感受。小时候有好几间平房的房顶都是我要征服的对象,只要一提征服这个词,所折射出的另一个词就是代价,征服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房顶也不例外,我也付出了挺惨痛的代价。
小时我和飞狗经常在一起玩,八零后的孩子们没有六零、七零后的孩子们玩的方式多,那两代才是真正聪明的一代,我们八零后的一代是挺懒惰的一代,就连玩的方式也创造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玩的都是人家玩剩下的,记忆中的那些游戏已经有些退色了,模糊得甚至想不起来,现在偶尔看到街上那些孩子玩的游戏,或许是有一些小时似乎同样也玩过的感觉。
从八十年代起,我家的这个院子就是这个样子,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没变样,典型的大杂院,住着八、九户人家,刚一进院过道的宽度跟煤气罐横过来的宽度差不多,再加上横七竖八堆了七、八辆自行车,道路所剩无几,走过时经常能碰到墙上的残灰,拐角处正好有一个大井盖,那时经常在想如果这里只有井没有盖,有人走到这里突然就消失了,只留下了“啊”的一声惨叫,这他妈多像一部悬念电影的情节,说消失就消失,小时候我经常为我有这种想象力而感到自豪。
这个院子没有中心,一条过道深又长,一边往里走一边向两旁看会发现都是一扇扇的门,就像逛菜市场一样,院子里的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也特像菜市场里卖菜的,特能让人身临其境地感觉就在菜市场。
二 开始了
小时候我和飞狗觉得玩拍洋画,弹球,砍包都不够刺激,就决定把我们的足迹留在这个院子的所有房顶上,这几间平房的高度都是一样高,全是连着的,区别就是攀登上去的难度。
“你先试试往上爬,我在下面等着你。”飞狗一边晃着他那大脑袋一边咬着小豆冰棍儿对我说。
“那你怎么不先上去?”
“你不是想当小飞侠吗?小飞侠得胆大,你要是真上去了我就把附近的小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