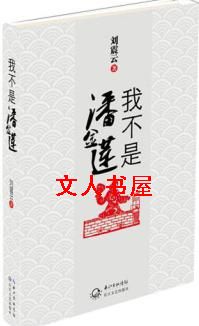我不是慕容冲-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万岁!万岁!万岁!”
燕军屡败屡战,本是士气低迷,至此方为之一振——慕容冲剑光指处,皆声势绵延,那声浪将整个白鹿原碾的瑟瑟发抖,似乎连远在百里外的长安城都能清晰耳闻了。
慕容永策马跟在后面,远远地望着那道夺目的身姿,默默地打量着四下里激动汹涌的人潮:还是得慕容冲——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行!鲜卑慕容嫡出皇子,除了慕容冲,谁能这般号令大燕军队?!
而逆光下的任臻,因隔得甚远,面容表情皆看不真切,但他嘴角边噙着的那抹从未有过的兴致盎然的笑,却让他平生一种头晕目眩的熟悉与震撼。
整军回城已交申时,慕容永正要下令造饭,忽听外报:“长安遣使而来!”
任臻奇道:“秦军近来常胜,怎么反倒先抹下面子来使通信?”慕容永想了想,冷笑道:“苻坚不愧真帝王也,能屈能伸——他必是想趁胜求和,劝我们东归,他便好腾出兵力来对付盘踞陇西的姚苌了。”
任臻命人宣召,心中却暗自摇头:若苻坚和慕容冲真有那么段往事,则再能屈能伸也无法低下这个头来,可若是特特派个使者来谩骂斥责,似乎更无必要了。
说话间那秦使已是从容入内,看他服饰,乃是个内宦,因知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故能昂着脸道:“天王有诏 ~”
拔高的嗓音嘎然而止,因为全场人都木然且略带不耐地看着他,他只得咳了一声,挥挥手,命跟着的侍从将手中漆盘捧上。
任臻看了呈到自己案几上的锦袍,伸手去捡那袍子——那是块稀世罗绡,通体云绣龙纹,宝光流转,却又轻盈透明,敷于掌上,肉体肤色纤毫毕现,于一派华贵中难掩奢靡冶艳之色,想来乃当年秦宫之物。任臻心中一动,觉得此物似乎颇为眼熟,但何处见过,却又记不真切了。心念电转间听那内侍又道:“卿,远来辛苦,只怕衣食孤寒,赐卿锦袍一袭,寥寥旧物,明朕心迹,卿当记取当日赠袍故事,恩爱情深,何至兵戎相见,刀斧加身?”
一时众人皆听呆了,慕容永大怒之下就要拔剑,其余人皆是能躲就躲,谁不知道这些话是虎须,轻易捻不得的。任臻呆却是他忽然明白苻坚的意思了——挟胜求和是假,羞辱挖苦是真!这袭半透红绡只怕曾经被他亲手覆在慕容冲赤身裸体之上,而后于他是百般恩爱,于慕容冲却是切肤怨恨——从皇子到娈童,从也由不得他说一句不!无怪当年的慕容冲无欲无求不为天下提兵直取长安只要复仇!他忽然有几分明白了慕容冲心中的怨毒愤恨,一把攥住了慕容永的手腕按下,转头朗声道:“请传话天王,朕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之小惠。若真有心修好,便君臣束手,早送长安,朕自当宽宥苻氏,方不至满门皆灭国破家亡!”
话音铿锵,语气决绝——慕容永似乎从任臻的双眸之中看见了——慕容冲的影子。
“他们这是一零之争。”事后,被抓去练箭习武的任臻还很认真地和慕容永分析了一下,“两个都要做一,互不想让,可不就打起来了!”
“???”和任臻呆久了慕容永已经学会了每当听不懂的时候就当装听不到地摆面瘫样,便为“藏拙”。
“是吧~!”任臻越想越有道理——至于慕容冲原有可能是直的??他揽镜一照——长成这样,绝,无,可,能!
“皇上,我明日就要带兵去仇班堡——此战不得不赢,我定会竭尽全力。”慕容永根本在考虑另一个问题,简明扼要地打断他,“您在阿房,亲掌兵权,大事可问慕容恒,小事——便问姚嵩吧,他倒是心细如发。只一条,此人狡诈如狐,又是姚苌之子——”
“要小心他嘛!知道知道!”这些天听这话都要听出耳油来了,他忽然停顿了一下,狡黠一笑:“你怎么动不动就叫我离他远一点儿,真只是因为他是姚苌儿子?”
慕容永以不变应万变,继续面瘫“藏拙”,末了忽然说:“。。。皇上,您射的中那儿,末将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任臻手搭凉棚看去——百步之外,一个校尉执戟而立,戟尖小枝在阳光下闪出光芒——他抓狂道:“你以为我是吕奉先啊!还来辕门射戟!”说着架起慕容永特地为他寻来的轻质木弓,搭箭要射,咬牙切齿道:“射戟不行,射你却是简单!”
慕容永听不懂他一语双关,却还是掌不住哈哈一笑,转身要逃。
暗处人影见二人在习武场上笑闹,不由一摇头,对身后那人微一躬身:“公子,皇上当真是性情大变,当如何——”
姚嵩缓步而出,勾起唇角:“派人送信与父王,即刻修书苻坚,愿为其拖住长安左近的韩延段随两军,乞秦军出长安,于仇班堡一举袭杀慕容永!”
另一人心中一惊,忙道:“姚秦与苻秦已经反目,势成水火,苻坚怎会愿意合作?”
“他还有的选吗?”姚嵩冷笑道,“龟缩长安发天子诏,结果能来救援的勤王之师寥寥无几,已经处于劣势了,再困守城中更是越拖越糟,他比谁都渴望出城一战——若能除了慕容永,便是剪除慕容冲双翼。何况比起我父王,慕容冲那小白脸儿的反叛才更让他切齿痛恨。”
“若是。。。若是慕容永不敌苻坚,则中军精锐便会尽殁,于燕国——”
“高将军。”姚嵩并不看他,只是一挑眉道,“你是父王早先就在鲜卑军中埋下的暗桩,你莫不是真当燕国是你的故土,慕容冲是你的主子了?”
高盖连忙躬身低首:“末将万万不敢有悖大单于,公子明鉴!只是苻坚若一战功成,缓过这口气来,于大单于也是弊大于利——”他忽然住嘴,因为姚嵩怔怔地盯着他上下打量,姚嵩人虽生的极美,但一双凤眼总是阴测测的,连笑都带着点不怀好意,此刻如毒蛇一般地盯着他,高盖的大白圆脸便刷地流下冷汗:“公,公子。。。?”
“我记得你是邺人吧,家中可还有什么人口?”
“公子,当初秦灭燕,高家就在战乱中死绝了的,是大单于还为秦将之时在邺城的死人堆中把末将捡回去的。”
姚嵩微微蹙眉,自言自语道:“那就怪了,为何慕容冲一见高盖就哼什么怪腔怪调的‘你快回来’?鲜卑民歌?不像呀,没有那么傻的调子~”
次日,慕容永领着一万精骑并五千步卒开拔出征,带走了巢车云梯等攻城器具,浩浩荡荡地出于阿房,大有踏平堡坞之意。任臻在城墙上看了,知道这次精兵对民兵,没有输的理儿,因而也颇放心,见军容壮阔,不由略一点头:“怪道人说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
姚嵩在旁一笑:“皇上说的好似自己不是鲜卑人似的。”任臻回过神来,知道自己说漏嘴了,掩饰地一笑:“你今天帮我寻的这身衣服倒是不错,不束手束脚的,穿的也简单。”
姚嵩一抿嘴:“这叫褶胯,皇上平时无事常穿,怎不记得了?”任臻决定闭嘴,说多错多,还是走为上计。
这些天慕容永人虽走了,但半天习武半天学文的规矩是定死了的,任臻倒也用心,因而骑着赭白,在习武场练了半日箭下来,周身已是被汗湿透,他跳下马来,将缰绳递给亲兵,吩咐道:“备热水,我——朕要沐浴。”一脚跨进房内,见案上还是一片狼藉;知是没他吩咐,没人敢入内整理。他随手一翻,书册内页皆写满了姚嵩所写的汉文批注,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姚苌虽是胡酋羌人,但儿子各个都学名在外,从世子姚兴到这姚嵩,都算的上才子,这一点,慕容家上下都该自叹不如。姚嵩每晚饭后都要过来为他讲书,任臻见天光未暗,便走进内室,除裳更衣——他刚一脚跨进木桶,忽然将外袍浸在水中又猛地抽出,拧成一条鞭子向门外狠狠劈去。外面人影一闪,一道红云利利落落地飘了进来,对任臻嫣然一笑:“好功夫。”任臻见了是他,方才弃了武器,奇道:“时辰还未到啊姚公子。”
姚嵩笑眯眯地:“我来伺候皇上沐浴啊。”
“不用不用!”任臻赶紧摆手。姚嵩却贴过去道:“那,就当我想与皇上同浴,可好?”
“。。。”任臻觉得像是在拍一部三流言情剧——他才不要当西门小恨恨!于是忽然俯身,拦腰抱起姚嵩,顺手丢进木桶里,水花四溅中他龇着牙道:“姚公子想洗,我让你先。”姚嵩狼狈不堪地从水里扑腾过来,趴住桶沿,仰视任臻的双眼中第一次有了丝意料外的惊异,而后,他黑眸一闪,忽然伸手拽住任臻仅存的衣襟猛力一扯——任臻站在他的面前,便□了。他毫无愧色地低头打量了下:恩,身材比起从前整天上健身房的自己,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姚嵩已从半人高的木桶中站起身来,水蛇般地伸手缠住他的脖子:“皇上忘了我们过去的事了吗?”
任臻是个快弯成圆形的男人,坐怀不乱简直就没存在过他的生命中,此刻软玉温香在怀,他缓缓地道:“姚公子慎言,我和你之前可是清白的很。”姚嵩见他不上钩,也不气馁,反更贴近了:“那现在呢~?”
任臻若有所思道:“你。。。是故意调慕容永去打仇班堡的罢~”
姚嵩微瞪双眼,奇道:“分明是皇上分化段随韩延在先,二人才拉慕容永下水,我可是什么也没做。”任臻语塞,没想到自己的想法三两下就被姚嵩看穿,恼恨地低头,与他前额相抵:“我不敢和你说话了,慕容永说了,你是见缝就钻的小狐狸。”
姚嵩没想到他如此坦诚,扑哧一声笑了:“那不说,做点别的?”任臻一笑,搂紧他的腰,偏头吻了过去。
在这方面,他一向笃定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不吃白不吃么,至于小狐狸的那些花花肠子,以后再去计较!
注 1
:磁石门为秦阿房宫门阙之一,传此门可防止行刺者——以磁石的吸铁作用;使隐甲怀刃者在入门时不能通过;从而保卫秦始皇的安全,后毁于战火,后世再重修便虚有其表了。磁石门的准确位置;历来说法不一,《三辅旧事》指为阿房宫的北阙门;《雍录》指为阿房宫的西门,即正对长安城的正门,本文从后者。
作者有话要说:CP乱炖 攻受兼备 恩~
7第 6 章
第六章
二人在一室淋漓中,正吻地难舍难分,忽听门外一路急报:“皇上,前线战报!”任臻一惊之下,松开手,姚嵩腿软腰乏,眼看又要落水,任臻忙一把捞住他,将人囫囵抱起,轻轻端上床,才随手扯过一袭干净的袍子披上,赶着出门。
姚嵩还在面红气喘——他没想到从来不假辞色的慕容冲有这般手段——此时忽然醒过神来,拦住任臻,小声急道:“你要这么出去?”
任臻皮比城墙厚,完全不觉得衣衫不整有什么问题,但见姚嵩神情奇异,不免又低头往下看了一眼,才终于面上一红,掩袍道:“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姚嵩瞟了他一眼,不说话,单是替他穿好内衫,套好褶跨,才道:“去吧——等等,别叫人进来!”任臻本想打趣一句“你也会不好意思”,但看姚嵩面如桃花,□未退,心里一动,便什么也不忍心说了,胡乱一点头,他迈步出门。
外面候着的亲兵早已等地焦躁不已,见慕容冲终于出来,忙双膝一跪,嚎啕大哭:“皇上!慕容将军在仇班堡苦战之时遇秦兵突袭,两下夹击,已是败了!”
任臻如遭电击,恍了一下神才急道:“那慕容永呢?!他如今在何处?!”
“将军遣我等报信,自己收拾残兵往东退去——他请皇上坐镇阿房,不要轻出,免中敌人分兵之计!”
“败军之将还想教皇上怎么行军布局么!”姚嵩也已更衣出来,早已面色如常,听到此话更冷冷一笑,“一万精兵不知还能剩回几人!”一句话提醒了任臻,他忙走到沙盘前,微一端详——仇班堡建于干涸废弃的仇班渠上,地处长安近郊,慕容永若退,肯定不会往西边的长安走,秦军又是早有准备,必是穷追不舍,如今定是顺着仇班渠残道退至——“白渠!”他一指沙盘上的一点,“我们必须出兵接应慕容永,能救多少救多少!”他扬手喝道:“点兵!今夜动身,前往白渠!”传令兵领命去了,他才跌坐于胡床之上,脑中还有些浑浑噩噩难以清醒,待姚嵩走到他面前,他才道:“你不要阻止我,我知道若论稳妥,最好避战不出,就算那一万人全军尽墨了,也不至于伤了根本。可我——可我做不到袖手旁观。”
姚嵩蹲□,仰视他,轻声道:“我没有阻止你的意思,只是想说,若上了战场,至少带上我。”
当夜未时不到,慕容冲便留慕容恒守阿房,自己点一万骑兵,奔赴白渠,援救慕容永。
黑夜漫漫,无星无月,车马粼粼声没入永夜,在任臻听来,几与惊涛骇浪相等——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就敢率兵出征?可让他就此袖手旁观,安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