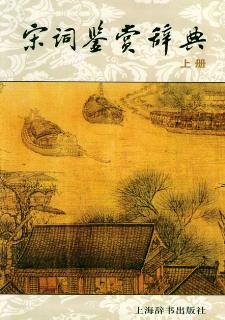席慕容诗词-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童稚时对人类的信心已是神话
殷勤种的盼望将永不开花
还有我那单纯的爱恋 还有
(还有我孩子的幼年呢?
以及将来他们的孩子无辜的容颜。)
——一九八五·十·卅
植树节之后
如果要用行动
来挽留这濒临幻灭的一切
我同意你 朋友
写一首诗其实真的不如
去种 一棵树
如果全世界的诗人都肯去种树
就不必再造纸
月亮出来的时候
每一座安静的丛林 就都会充满了
一首又一首
耐读的诗
——一九八八·五·八
给黄金少年
(一群刚上中学的少年排队走过,领队说停,每个人就惶惶然站在我对面的十字街。
头发已经是一样的模式了,相似得不能再相似。身上穿的衣服也完全相同,甚至学 号绣的宽窄也有讲究。他们都很沉默,因为按规定在队伍中是不可以开口的。)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流下泪来
这里面会有我的孩子吗
如果真有 请你告诉我
那个昨天还有着狡黠的笑容
说话像个寓言与诗篇的孩子
那个像小树一样 像流泉一样
在我眼前奔跑着长大了的孩子啊
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九八七·十一·十八
试验
——之一
他们说 在水中放进
一块小小的明矾
就能沉淀出 所有的
渣滓
那么 如果
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
一首诗
是不是 也可以
沉淀出所有的 昨日
——一九八二·七·十二
诗的价值
若你忽然问我
为什么要写诗
为什么 不去做些
别的有用的事
那么 我也不知道
该怎样回答
我如金匠 日夜捶击敲打
只为把痛苦延展成
薄如蝉翼的金饰
不知道这样努力地
把忧伤的来源转化成
光泽细柔的词句
是不是 也有一种
美丽的价值
——一九八○·一·廿九
画展
我知道
凡是美丽的
总不肯 也
不会
为谁停留
所以 我把
我的爱情和忧伤
挂在墙上
展览 并且
出售
——一九八○·十·十一
交易
他们告诉我 唐朝的时候
一匹北方的马匹换四十匹绢
我今天空有四十年的时光
要向谁去
要向谁去换回那一片
北方的 草原
——一九八七·十二·廿一
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一九七八
出塞曲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塞子歌的调子都太悲凉
如果你不爱听
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
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
想着黄河岸啊 阴山旁
英雄骑马啊 骑马归故乡
——一九七九
长城谣
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
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的悲欢啊
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蹲踞在荒莽的山巅
冷眼看人间恩怨
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
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
有你的云 你的树 你的风
敕勒川 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一九七九
盐漂浮草
总是在寻找归属的位置
虽然
漂浮一直是我的名字
我依然渴望
一点点的牵连
一点点的默许
一块可以彼此靠近的土地
让我生
让我死 同时
在这之间
在迎风的岩礁上
让我用爱来繁殖
——一九八六·十一·一
狂风沙
风沙的来处有一个名字
父亲说儿啊那就是你的故乡
长城外草原千里万里
母亲说儿啊名字只有一个记忆
风沙起时 乡心就起
风水落时 乡心却无处停息
寻觅的云啊流浪的鹰
我的挥手不只是为了呼唤
请让我与你们为侣 划遍长空
飞向那历历的关山
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
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亲啊母亲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一九七九
祖训
——成吉思汗:〃不要因为路远而踌躇,只要去,就必到达。〃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
不许流泪 不许回头
在英雄的传记里 我们
从来不说他的软弱和忧愁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
在风沙的路上
要护住心中那点燃着的盼望
若是遇到族人聚居的地方
就当作是家乡
要这样去告诉孩子们的孩子
从斡难河美丽母亲的源头
一直走过来的我们啊
走得再远 也从来不会
真正离开那青碧青碧的草原
——一九八七·十二·廿八
天使之歌
——昨日已成废墟
只留下还在旷野里坚持的记忆
(一直希望我能是天使
在俯仰之间 轻轻扇动着那
原该是我与生俱来的翅膀
巨大而又华丽 我洁白的羽翼……)
我闭目试想 总还能剩下一些什么吧
即使领土与旗帜都已剥夺
盔甲散落 我 总还能剩下一些
他们无从占领的吧
诸如自尊 决心以及
那终于被判定是荒谬与绝望的理想
这尘世是黑暗丛林
为什么 我依旧期待黎明
应该还是可以重新再站起来的吧
我悄然自问 当遍体鳞伤的此刻
当连你也终于
弃绝了我 在此最最泥泞荒寒的角落
独幕剧
(然而这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我们从来没要求
过流亡与战争)
有些记忆成为真理是因为那坚持的品质有些经
验成为美是因为它们的易碎可是请你告诉我为
什么我们的剧本里总是让有些憎恨成为习惯有
些土地成为梦境这荒谬而又悲凉的情节啊千年
之后有谁还会相信?
千年之后有谁还会相信今夜的我们曾经彼此寻
找怀着怎样温柔的心情山谷与草原的气息原来
可以如此贴近而又熟悉莲房中新生的莲子原来
全无那苦涩的恨意这一分一秒逐渐远去的原是
我们可以倾心爱恋的时光可是成长中的一切课
程却都只教会了我们要如何去互相提防每一页
翻过的章节都充满了不同的解释每一次的演出
总是些互相矛盾的台词年轻的演员因此而怯场
初来的观众在错愕间既不敢鼓噪也不敢鼓掌不
知道要用怎样的诱饵才能让编剧者揭开全部的
真相。
(然而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演出实在经不起任何的
试验与错误)
在幕启之初身为演员我的嗓音曾经诚挚而又快
乐开始向黑暗的台下述说生命里那无数次错不
在我的沧桑与阻隔我知道你正在我身后静静聆
听即使在众人之中我相信也能够辨识出那孤独
的身影多希望能够转身窥视你藏在心底的镜子
在其中应该也会有你为我留下的位置纵使到今
夜为止我们从未真正相识。
风从每一扇紧闭着的窗外吹过有水声从后台传
来灯光转蓝暗示此刻已经来到了灰茫清冷的忘
川台下是谁在轻声叹息难道他是智者已经预知
结局?
灯光闪烁间所有的脚步突然都变得踉跄与杂乱
高潮应该就是在前面横亘着的那一条忘川远处
波涛仿佛已经逐渐平息你看那白发的水手在悠
长的等待之后不是正一一重返故里让我们也互
相靠近互相碰触穿过层层莲荷的花叶终于紧紧
相拥立誓永远不要再陷落在过往的泥沼之中。
(如果能够就此约定这整整的一生都不许再有恨)
为什么希望绽放之后即刻凋谢比莲荷的花期还
短为什么依旧有许多阴影在深深的河底回绕交
缠渴盼中的爱与被爱啊在多年的隔离之后竟然
万般艰难今夜的我站在岸边只听到有人顿足有
人悲泣河面无限宽广那忘川的水流对我们竟然
毫无助益多少次在梦中宛转低唤的名字如今前
来相会却悚然察觉我们都已不再是彼此的天神
而是魔鬼灯火全灭布幕在惊呼声中急急落下从
此流浪者的余生啊将要辗转在怎样不堪的天涯?
千年之后有谁还会相信幕落之前我们曾经怎样
努力想要修改这剧中的命运身为演员当然知道
总会有个结局知道到了最后不外就是死别与生
离可是总不能就这样让整个故事都在错置的时
空中匆匆过去?
(这也是我们最深的悲哀整整一生我们辛勤种植
幸福却也无法攀采)
幕落后所有的泪水是不是都必须吞回下一场的
演出再也不会有我们发言的机会历史偏离我们
的记忆越来越远却从来不见有哪一个编剧者肯
向这世界致歉若是你还能听见我高亢的歌声传
过水面传遍旷野请你一定要记得幕落之前我们
彼此狂热的寻求曾经怎样穿越过那些黑暗的夜
即或是已经明白了没有任何现实可以接近我们
卑微的梦想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让我们静静憩息
当作是心灵的故乡。
(这也是我们最深的困惑整整一生都要在自己的
家园里扮演着永远的异乡人)
——一九八八·五·八
双城记
前言:
去年秋天,人在北京。有次坐在计程车中,忽然瞥见一处街名,是儿时常听长辈说起的,先母旧居应该就在这附近。
于是央司机绕道去看一看,并且在说出地址之后,还向他形容了一下我曾经从旧相簿里见过的院落和门庭。
司机沉吟半晌,回答我说是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不过却绝不像我所形容的模样;也许,还是不去的好。
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们默然向前驶去,黄昏的街巷终于复归成陌生城市。我只记得那位先生双鬓微白,在驾驶的途中始终没有回过头来。
那天晚上梦见了母亲。
梦里 母亲与我在街头相遇
她的微笑未经霜雪 四周城郭依旧
仿佛仍是她十九岁那年的黄金时节
仿佛还是那个穿着红缎里子斗篷的女孩
憧憬像庭前的海棠 像芍药初初绽放
却又知道我们应是母女 知道
我渴望与她分享那些珍藏着的记忆
于是 指着城街 母亲一一为我说出名字
而我心忧急 怎样努力却都不能清楚辨识
为什么暮色这般深浓 灯火又始终不肯点起
妈妈 我不得不承认 我于这城终是外人
无论是哪一条街巷我都无法通行
无论是昨日的还是今夜的 北京
——一九九一·二·十九
留言
——写给尼采的戴奥尼苏斯
1
在惊诧与追怀中走过的我们
却没察觉出那微微的叹息已成留言
这就是最后最温柔的片段了吗 当想及
人类正在同时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
二月过后又有六月的芬芳
在纸上我慢慢追溯设法挽留时光
季节不断运转 宇宙对地球保持静观
一切都还未发生一切为什么都已过去
山樱的枝桠间总好像会唤起些什么记忆
我反复揣摩 用极慢的动作
寻找那些可以掩藏又可以发掘的角落
将远方战争与饥荒的暗影减到最低
将迟疑的期许在静夜里化作诗句
2
这就是最后最温柔的片段了吗 当想及
人类正在同时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
初雪已降下 可是对于美 对于彼此
对于激情真正的诱因还是一无所知
在每一盏灯下细细写成的诗篇
到底是不是每一颗心里真正想要寻找的
想要让这世界知道并且相信的语言
要深深地相信啊 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