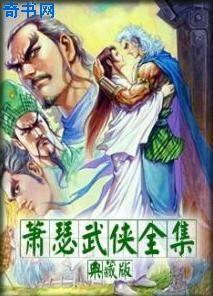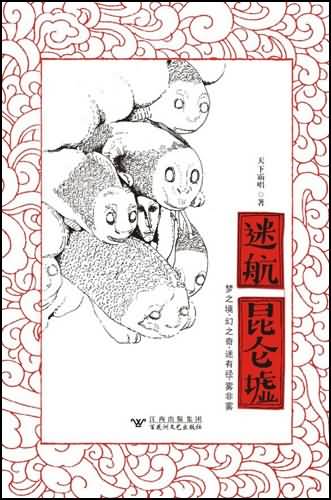我与拿破仑-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锉囊话搿E由炔恳驯患呙穑椿故O氯亍E谖簧柙谝坏兰脑扒胶竺妫丫由狭艘徊闵炒鸵坏揽硗恋蹋姑挥邪沧罢だ浮M槎倨镌诼砩希撵阂《裆匀簦谑ピ己采揭豢糜苁飨铝⒘艘徽欤贾彰挥懈谋渌淖耸疲渚⒂隆E诘甑闼频穆湎吕础8惫俑甑歉账涝谒砼浴9笞逑6缸乓豢耪诒ǖ呐诘蛩担骸按笕耍蛞荒獠徊猓惺裁粗甘靖颐悄兀俊薄跋笪夷茄プ觥!蓖槎倩卮稹6宰趴肆侄蚨痰厮担骸笆卦诖说兀钡阶詈笠桓鋈恕!蹦翘煨问泼飨员浠怠M槎俣运だ啊⑽嗬恰⑷ㄖ畛堑哪切├吓笥押暗溃骸癇oys(孩子们)!难道有人想开小差不成?替古老的英格兰想想吧!”
将近四点时英军的最后防线动摇了。在高地的防线里只见炮队和散兵,其余的一下子全都不见了。那些联队受到法军*和炮弹的压逼,都折回到圣约翰山庄便道那一带去了,英军前锋向后倒,威灵顿退了。“退却开始!”拿破仑大声说。皇帝骑在马上,他这几天有点不舒服,但这不影响他愉快的心情。从早晨起,他那深沉莫测的神色中便含有笑意。凌晨一点钟起,他就骑着马,在狂风疾雨中和贝特朗一道巡视着罗松附近一带的山地,望见英军阵地的火光从弗里谢蒙一直延展到布兰拉勒,照映在地平线上,他心中感到满意,好象觉得他所指定的胜利果然应时到了;他勒住了马,望着闪电,听着雷声,呆呆地停留了一会,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了这样一句神秘的话:“我们是同心协力的。”拿破仑几乎一分钟也不曾睡,那一整夜,每时每刻对他来说都是欢乐。他走遍了前哨阵地,随时随地停下来和那些士兵谈话。两点半钟,他在乌古蒙树林附近听见一个纵队行进的声音,他心里一动,以为是威灵顿退阵,他向贝特朗说:“这是英国后防军准备退却的行动。我要把刚到奥斯坦德的那六千英国兵俘虏过来。”他语气豪放,回想起三月一日在茹安海湾登陆时看见的一个惊喜若狂的农民,他把那农民指给大元帅看,喊道:“看,贝特朗,生力军已经来了!”现在他又有了那种豪迈气概。六月十七到十八的那一晚上,他不时取笑威灵顿,“这英国小兔崽子得受点教训。”拿破仑说话时,雨下得更大了,雷声不断。到早晨三点半钟,他那幻想已经消失,派去侦察敌情的军官们回来报告他,说敌军毫无行动。一切安定,营火全没有熄。英国军队正睡着,地上毫无动静,声音全在天上。四点钟,有几个巡逻兵带来了一个农民,那农民当过向导,曾替一旅预备到极左方奥安村去驻防的英国骑兵引路,那也许是维维安旅。五点钟,两个比利时叛兵向他报告,说他们刚离开队伍,并且说英军在等待战斗。
“好极了!”拿破仑喊着说,“我不但要打退他们,而且要打翻他们。”
到了早晨,他在普朗尚努瓦路转角的高堤上下了马,立在烂泥中,叫人从罗松庄屋搬来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和一张农民用的椅子,他坐下来,用一捆麦秸做地毯,把那战场的地图摊在桌上,向苏尔特说:“多好看的棋盘!”由于夜里下了雨,粮秣运输队都阻滞在路上的泥坑里,不能一早到达;兵士们不曾睡,身上湿了,并且没有东西吃;但是拿破仑仍兴高采烈地向内伊叫着说:“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八点,皇上的早餐来了。他邀了几个将军同餐。
一面吃着,有人谈到前天晚上威灵顿在布鲁塞尔里士满公爵夫人家里参加舞会的事,苏尔特是个面如大主教的鲁莽战士,他说:“舞会,今天才有舞会。”内伊也说:“威灵顿不至于简单到等候陛下的圣驾吧。”皇上也取笑了一番。他性情就是这样的,乐于嘲讪,本性好诙谐,善戏谑,能开多种多样的玩笑,不过突梯的时候多,巧妙的时候少。早餐后,他静默了一刻钟,随后两个将军坐在那捆麦秸上,手里一支笔,膝上一张纸,记录皇上口授的攻击令。
九点钟,法国军队排起队伍,分作五行出动,展开阵式,各师分列两行,炮队在旅部中间,音乐居首,吹奏进军曲,鼓声滚动,号角齐鸣,雄壮,广阔,欢乐,海一般的头盔,马刀和枪刺,浩浩荡荡,直抵天边,这时皇上大为感动,连喊了两声:“壮丽!壮丽!”从九点到十点半,全部军队,真是难于置信,都已进入阵地,列成六行,照皇上的说法,便是排成了“六个V形”。阵式列好后几分钟,在混战以前,正如在风雨将至的那种肃静中,皇上看见他从戴尔隆、雷耶和罗博各军中抽调出来的那三队十二利弗炮在列队前进,那是准备在开始攻击时用来攻打尼维尔和热纳普路交叉处的圣约翰山的。皇上拍着亚克索的肩膀向他说:“将军,快看那二十四个美女。”
第一军的先锋连奉了他的命令,在攻下圣约翰山时去防守村子,先锋连在他面前走过时,他满怀信心,向他们微笑,鼓舞他们。在那肃静的气氛中,他只说了一句自负而又悲悯的话,他看见在他左边,那些衣服华丽、骑着高头骏马的苏格兰灰衣队伍正走向那里集合,他说了声“可惜”。随后他跨上马,从罗松向前跑,选了从热纳普到布鲁塞尔那条路右边的一个长着青草的土埂做观战台,这是他在那次战争中第二次停留的地点。他第三次,在傍晚七点钟停留的地点,是在佳盟和圣拉埃之间,那是个危险地带;御林军全集合在土丘后平地上的一个斜坡下面。土丘的四周,炮弹纷纷射在石块路面上,直向拿破仑身旁飞来。炮弹和枪弹在头上嘶嘶飞过。我的腿就在这时受伤,但还能站起来。我感到今天恐怕难逃一死,直往他的马后躲。他看了哈哈大笑着说:“笨蛋,怕是鬼,你不怕炮弹打到你的屁股。”
拿破仑和威灵顿交锋的那片起伏如波浪、倾斜程度不一致的平原,它缓缓地向尼维尔路方向倾斜下来,这一带还不怎么难走,可是在向热纳普路那一面,却几乎是一种峭壁。一
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雨水在陡坡上冲出无数沟坑,一片泥泞,上坡更加困难,不但难于攀登,简直是在泥中匍匐。高地上,沿着山脊,有一条深沟。可是站在远处看不见。布兰拉勒和奥安都是比利时的村子。两个村子都隐在低洼的地方,两村之间有一条长约一法里半的路,路通过高低不平的旷地,常常陷入丘底,象一条壕堑,沟有时深达十二尺,并且两壁太陡,四处崩塌,尤其是在大雨滂沱的季节。我走过这条路。
拿破仑在滑铁卢的那个早晨心情很好。他有理由高兴,他擘画出来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就要实现了,真令人叹服。交锋以后,战场发生着非常复杂惊险的变化,乌古蒙的受阻,圣拉埃的顽抗,博丹的阵亡,富瓦战斗能力的丧失,使索亚旅受到重创的那道意外的墙,无弹无药的吉埃米诺破釜沉舟的顽强,炮队陷入泥淖,被阿克斯布里吉击毁在一条凹路里的十五尊炮,炸弹落入英军防线效果不大,土被雨水浸透,炸弹陷入,只能喷出一些泥土,以致*全变成了烂泥泡,比雷在布兰拉勒出击无功,十五营骑兵全部覆没,英军右翼应战的镇静,左翼防守的周密,内伊不把第一军的四师人散开,反把他们聚拢的那种奇怪的战术,每排二百人,前后连接二十七排,齐头并进去和*对抗,炮弹对那些密集队伍的骇人的射击,失去连络的先头部队,从侧面进攻的炮队突然受到拦腰的袭击,布尔热瓦、东泽洛和迪吕特被围困,吉奥被击退,来自综合工科学校的大力士维安中尉,冒着英军防守热纳普到布鲁塞尔那条路转角处的炮火,在抡起板斧去砍圣拉埃大门时受了伤,马科涅师被困在步兵和骑兵的夹击中,在麦田里受到了贝司特和派克的劈面射击和庞森比的砍斫,他炮队的七尊炮的火眼全被钉塞,戴尔隆伯爵夺不下萨克森-魏玛亲王防守的弗里谢蒙和斯莫安,第一○五联队的军旗被夺,第四十五联队的军旗被夺,格鲁希的迟迟不来,一下便倒在圣拉埃周围的那一千八百人,比在乌古蒙果园中不到一个钟头便被杀尽的那一千五百人死得更快,凡此种种迅雷疾风似的意外,有如阵阵战云,在拿破仑的眼前掠过,几乎不曾扰乱他的视线,他那副极度自信的龙颜,绝不因这些变幻而稍露忧色。他习惯于正视战争,他从不斤斤计较那些残酷的数目字,他要算的是总账:最后的胜利。开始危殆,他毫不在意,他知道自己是最后的主人和占有者,他知道等待,认为自己不会有问题,他认为命运和他势匀力敌。他仿佛在向命运说:“你不见得敢吧。”
威灵顿后退,拿破仑见了大吃一惊。他望见圣约翰山高地突然空虚,英军的前锋不见了。英军前锋正在整理队伍,似乎在准备逃走。皇上半立在他的踏镫上,眼睛里闪起了胜利的电光。把威灵顿压缩到索瓦宁森林,再加以歼灭,英格兰便永远被法兰西压倒了。皇上一面思量那骇人的变局,一面拿起望远镜,向战场的每一点作最后一次的眺望。围在他后面的卫队,武器立在地上,带着一种敬畏神明的态度从下面仰望着他。他正在想,正在视察山坡,打量斜地、树丛、稞麦田、小道,他仿佛正在计算每丛小树。他凝神注视着英军在那两条大路上两大排树干后面所设的两处防御工事,一处在圣拉埃方面,热纳普大路上,附有两尊炮,那便是英军瞄着战场尽头的唯一炮队;另一处在尼维尔大路上,闪着荷兰军队夏塞旅部的枪刺。
他还注意了在那一带防御工事附近,去布兰拉勒那条岔路拐角处的那座粉白的圣尼古拉老教堂。他弯下腰去,向我低声说了一句话。我摇了摇头。他说的是:“黄种人,前面有河流吗?”如果我告诉他前面有一条比河流还要凶险的路,战争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随后我虚弱地坐在了地上。皇上挺起身子,聚精会神,想了一会。威灵顿已经退却。只须再加以压迫,他便整个溃灭了。拿破仑陡然转过身来,派了一名马弁去巴黎报捷。他是一种霹雳似的天才。他好像刚找到大显神威的机会。拿破仑命令米约的铁甲骑兵去占领圣约翰山高地。他们是三千五百人。前锋排列到四分之一法里宽。那是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巨人。他们分为二十六队,此外还有勒费弗尔-德努埃特师,一百六十名优秀宪兵,御林军的狙击队,一千一百九十七人,还有御林军的长矛队,八百八十支长矛,全都跟在后面,随时应援。他们头戴无缨铁盔,身穿铁甲,枪橐里带着短枪和长剑。早晨全军的人已经望着他们羡慕过一番了。那时是九点钟,军号响了,全军的乐队都奏出了“保卫帝国”,他们排成密密层层的行列走来,一队炮兵在他们旁边,一队炮兵在他们中间,分作两行散布在从热纳普到弗里谢蒙的那条路上,他们的阵地是兵力雄厚的第二道防线,是由拿破仑英明擘画出来的,极左一端有克勒曼的铁甲骑兵,极右一端有米约的铁甲骑兵,是第二道防线的左右两铁翼。副官贝尔纳传达了命令。内伊拔出了剑,一马当先。进攻开始了。整队骑兵,长刀高举,旌旗和喇叭声迎风飘荡,每个师成一纵队,行动一致,有如一人,从佳盟坡上直冲下去,深入尸骸枕藉的险地,消失在烟雾中,继又越过烟雾,出现在山谷的彼端,始终密集,相互靠拢,前后紧接,穿过乌云一般向他们扑来的*,冲向圣约翰山高地边沿上峻急泥泞的斜坡。他们由下上驰,严整,勇猛,沉着,在枪炮声偶尔间断的一刹那间,可以听到大军踏地的轰鸣。瓦蒂埃师居右,德洛尔师居左。远远望去,好象两条钢筋铁骨的巨蟒爬向那高地的山脊。无数的铁盔、吼声、白刃,还有马*在炮声和鼓乐声中的奔腾,声势猛烈而秩序井然,显露在上层的便是龙鳞般的胸甲。高地的顶点背后,英国步兵在埋伏着的炮队的掩护下,分成十三个方阵,每两个营组成一个方阵,分列两排,前七后六,枪托抵在肩上,瞄着迎面冲来的敌人,沉着,不言不动,一心静候,他们看不见铁甲骑兵,铁甲骑兵也看不见他们。他们只听见这边的人浪潮似的涌来了。他们听见那三千匹马的声音越来越大,听见马蹄奔走时发出的交替而整齐的踏地声、铁甲的磨擦声、刀剑的撞击声和一片粗野强烈的喘息声。一阵骇人的寂静过后,忽然一长列举起钢刀的胳膊在那顶点上出现了,只见铁盔、喇叭和旗帜,三千颗有灰色髭须的人头齐声喊道:“皇帝万岁!”冲上了高地。突然,在英军的左端,法军的右端,铁骑纵队前锋的战马,在震撼山岳的呐喊声中全都直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