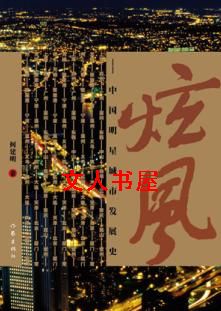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й����侫��İ���ʧ��:����ޱ�-��2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Ψ�ĵ�˵����Ҳ�����Ǿ��ӡ���������������K�ط��ľ�ͷ��������ĩ���˱�������Ӣ�۱��ų���ٱ�ɳ��裬������䣬���������л������֦���㣬���˵ı������������ı��磬һ��������Ļ����
�����ձ�����ʿ����Ϊ����������ʤ��ʷ���������ս��ߡ������������������������սᣬ�������չ�ϵʷ�ϱ����˹��˳��������������ڰ��ڡ�������ǿ�������֮���й��ֿ�ʼ�˰��ڡ������ڵ���ʮ�����ᡣ
�����ɡ�Ԯ������ʼ�ġ���ս�������ڽ�ս��������ڡ�Ҷ�������ֺ�����½����˧��Ҳ��������������������֮�����Լ��������ϣ�����ʱ���������˺�֮�ƣ���Ȼһ���ٰܣ�һ�����ӣ�Ѯ��֮�䣬�ɶ��뵺��������֡��Թ�����ʮ�꣨1894�����¶�ʮ���գ�9��22�գ���ּ�����Ĵ��ᶽ����Ϊ����������족����������ʼ����������ʮһ�꣨1895������ʮ���գ�3��9�գ����������ص���ׯ̨ʧ�ݣ��ԡ�������Ϊ�м���й�½���ڱ�����ս�У������ܼ�������˵����ʧ������������ǡ�����������ʧ�ء�����ʧ�ء�����ʧ�ء�����ʧ�ء����ʧ�ء����ʧ�ء�����ʧ�ء���˳ʧ�ء���ľ��ʧ�ء�����ʧ�ء���ɽʧ�ء�ţׯʧ�ء���ƽʧ�ء�����ʧ�ء�Ӫ��ʧ�ء�������վ��������й����ӵ��˲���һ���ij̶ȡ�
����˵һ�����ӣ������Ժ����й�½��ս����������ʮ�꣨1894��ʮһ��ʮ���գ�12��13�գ��������DZ��վ�ռ�죬���ں��ǵ�ս�Ե�λ������������פ�ɸ���������ս�����й����ǣ�����һʤ����������������ͳ�������ͬ��ʿ�ɡ�����Ԫ�������ư�����˳�����������Χ�������վ���פ�����վ�����ǧ�ˣ����������������ˣ����ӵ������ˣ������ӵ�������ǧ�ˣ�������������ˣ�����ս���Բ��ˡ���ʮ��֮�ڣ��幥������һ�ǣ��Ա�ƽ��֮ս�վ��Զ���֮�����ݶ�ǣ�����½������ǿ����������һĿ��Ȼ��
����������
�����ƺ��������������
��һ�ڣ����ǽ���һ�������ְ�ض��������Դ��Ľ����������ǰն������͢�ƺ�Ҳ�Dz����Ѷ�Ϊ֮�����������������Զϴ�����ġ�������֮�ܡ�
�����ڱ����У�Ҳ��һ����Ϊ���ܶ���ն�ľ��٣����з���ǫ���DZ���ˮʦ����Զ����Ѳ�ġ��ܴ�������������
�������������ԡ������������壬һ�ɹ��Ϊ���Ӷݵġ�������ô������������������ν�ġ�
������������������ʷ�����壬�����ε����壬���������µ�����ȴ���ྶͥ��˾��Ǩ��ν��������̩ɽ�������ں�ë������Դ�ڴ�Ҳ��
����ɱ����������ӡ���������ɱ����ǫ���������ӡ�ˮʦ�������������й���������������ˮʦ������ӡ֤�ˡ�ɱһ�Ӱ١���һ�ж���ͨ�帯�ܵ����ƺ���ЧӦ��
����ͬ������������������Ӱ�첻һ��
���������ʮ�ּ��ȣ����������ἰ������ͬ���ֵ�����ɣ������ܱ������ɶ�����ս��Ч�����֣�����Ϊ�ϡ���ּ���Σ���ѶDZ�ӣ���֪���գ���ν�����ѵܡ�
��������ǫ���о��ߡ������ߡ����ԣ�����б�Ҫ��˵���䷽��ǫ�¼���ԭί��
��������ǫ��1852��1894������չ�ã�һ˵���ã���������ˡ����ݴ���ѧ�ñ�ҵ��1877����Ϊ���ҵ����Ӣ��������ĻʼҺ���ѧԺ��ѧ������ѧ�ɻع������Ρ���Զ������ϰ���ܴ����з�ս���𣬷�������������˳�����Զ�����Զ��̨������۵������Ļ������1889�꣬�������о���Ӫ������ί������Զ����Ѳ��1892�꣬ʵ�ں����������Ӷ�Ʒ��������ս�ճ��𣬷���ǫ�����ʡ���Զ��������������ê��Ϊ���ڴ���ڡ�ʻ������ɽ�ı��ֻ������Ͻ������Ѿ���¶������ǫ�ġ���������ʵ���㺽��ģ��Һ��ҵģ�������������������������ǣ������ʡ��š����ɾ�����δ�������ս���ƽ���ִ���ɽ�⺣������ǫ�ġ���Զ�����롰���ҡ��ţ���������������������������ʿ������ƥ�;���Ʒ��ת�ص�½�����������¶�ʮ���գ�7��24�գ����������磬�ֱ�ʻ���й���
����������������5ʱ30�֣�����Զ�������ʴ�ʻ����ɽ�������վ������ѹ�ռ�������������ٳֹ�������Ϣ������ͣ���ʴ���Ӣ�����������ս��������쿪������Ϣ����Ѷ������ǫ���������IJ���ҹ11ʱ�������ٶ������ġ���Զ�������У����ڴ�ͬ���ڵȴ������¶�ʮ���գ�7��25�գ�����4ʱ������Զ���������ҡ�����ʻ����ɽ�ڣ��ϡ���Զ�����Ա��ӻع����������ҽ���δ�������ر���Ҫ���������ġ��������֣�����ǫ���Dz��ֻ࣬�����ں���������ʱ˳���֪��ǰ����ս�����ٷ��ء�
�������¶�ʮ���գ�7��25�գ���7ʱ������Զ���������ҡ��������ձ����ӡ�
����7ʱ15�֣�����ǫ���ȫ��ٱ������λ����ս����
����7ʱ20�֣��ս��´�ս�����
����7ʱ43��30�룬�ս�����Ұ����һ���ڣ���ʾ���档
����7ʱ45�֣�����Ұ�������й��������ڡ�
����7ʱ52�֣�����Զ���ſ��ڻ�����
����7ʱ55�֣��ս�������ޡ��ſ��ڡ�
����7ʱ56�֣��ս������١��ſ��ڡ�
����������ս���ձ��������˷ᵺ��ս��
�����й����������ھ������ơ�
���������������£�����ʮ������Ϊ�ϡ������ߡ�δ������һ�ֺ���ѡ���ң�������˵�ǡ��ӡ���
���������ǣ����ӡ�Ҳ�Ӳ���������̫������ô�죿
����ʣ�µ�ѡ���ֻ����������ƴ��һս����ս������
��������ǫ����ѡ���ˡ��ߡ����ڵ�ǿ�����������ڻ������������ص�����£�����ǫָ�ӡ���Զ������ս����������ʻ���ս������ᡣ
����8ʱ53�֣�����Զ��������һ����졣����ͣս�����źš�
������һ�ᣬ����Զ�����ϰ���֮����������һ���ձ������졣
�����ս���״��ֹͣ���ڻ�������Զ����Ҳֹͣ�˷��䡣������ʱ���˱�������������ʻ��ս�����ս�ע�������Է�ɢ������Զ�����ֳ˻���������������
������ʱ�������ɡ����١��ű�Ϊ����Ұ���š�
����12ʱ38�֣�����Ұ����Զ���������ڣ����ڡ���Զ��������ը��
����12ʱ40�����ң�����Զ����ˮ�������ɡ���ʿï����ͬ��Э���£�������������Ұ�����������ڣ������������С���Ұ��Ҫ��������Ұ����������ʼ���٣�����12ʱ43��ת�泷�ˡ�����Զ���û���ʻ������ս������������������ҡ��Ÿ��˸�dz�����������ų�û�����ٽ����ű������ᵺ��ս���з��ľ���ʧ������
�����϶μ�������ʵ���й���������ʷ�о��ߵĹ�����ʵ������¼������˹�����ǫ��ս��������Ļ㱨�У�������������У���ι�������α�Χ��������Ұ������յУ������ٽ���ê��������䲻����ен�Ҫ����������Ϊʤ��ʼ�����뻢���ӹ����ڡ�����ϧ���������������磬�������ʷ���Ի������������ر�֮��������������ȫ����û������ͬ����һ�Ҷ��飬����֮ν�Σ�������֪�ӡ������Ұ��������������к���Ŀ�������ң������ز��ݵ������գ��������������ƶ������ϻظۺ�ȷ�����Ա��书��
���������ں�ս��֪��������ԹҰ����ж����Ͷ������������ν������Ϊʤ����ȴ��ʤ���ú����ݡ���������һ�εġ��ӡ������ǹ����ټ�Ǵ��
����������ʮ�����Ļƺ���սʱ������ǫ�ġ��ӡ����������µķ�չ���������븴����κ�ս�ļ�����׳�ң���������ǫ�ı��֡�
����ս�۰���ʮ���գ�9��17�գ����������Ļ��
����12ʱ50�֣�����Զ������������305���ھ������������ս�������һ�ڡ������������̷��ڡ��ս�ð���ڻ��Ƚ���
����12ʱ52�֣��ս����ɵ��������й��������ڡ�
�����й�������V�α��Ш���ձ�����֮�䣬���վ���һ�λ����뱾��һ��Ϊ����˫��չ����ս����ս����Ϊ���ҡ�
����13ʱ30�֣��з������¡��ų�û��
����14ʱ40�֣��з����������Ÿ�dz��
����15ʱ30�֣��з�����Զ���ų�û��
����������Զ���ų�û������Զ�����ϵķ���ǫ����æ���Լ��ľ����´���ת�������Զ������ս��������˳����ʻ������ס��Źܴ��⾴�ټ�״��Ч��Ҳ����ս��������ʱ���й��������Ƹ�Ϊ���ԣ����콢����Զ������������һ��������Զ���ţ����ڶ����ս���ӵΧ��֮�С�����Զ���롰��ס���ս���ݣ��ڱ���������ս���ڲ��ˣ�����˧�ڲ��ˣ���Ŀ���ͣ�Υ�������ƺ��Ѳ���Ҫ����Ц���ǣ�����Զ���������У�������·�������Ѿ���dz�ġ���������ײ������ν���ϼӴ���
��������Զ�������Ӻ���������
����17ʱ30�֣��з�����Զ���ų�û��
����17ʱ45�֣��ս���������Զ��������Զ�����ˣ������˳�ս���������������˳�ۡ������ճ�û�Ľ��⣬�ڶ��������ܸ�dz�ġ���ס����౻�ս��������ƺ���ս������ˮʦ�Գ�û�形���ա��ձ����Ͻ�����һ��δ����
����ʱ�£��Իƺ���սȫ���Եķ����Ѿ��ܶ࣬���ڲ��ٸ������й�ѧ�߶����ս�۵İ���̽��Ҳ��ȫ�����̣��������ժ����һ����֮��ȥ�������ǣ�
�����л����岻��Ӣ�ۣ������ս�������������������������ȣ�����ȻҲ����ų�������ս���е�Ҷ־�����������ǫ�ȣ��������ھٲ�β��ܺ�˱��ˡ�����Ҫ�ȵ�Ӣ������ų���ӲŸ���һ˿�������˺�����Ȼ����ݬ���֡������ߵ���а�أ�
�������������������Ѿ�Ӣ�������ˡ������ǣ���Ϊ��ʷ�ĸ�������Ӣ��֮��˭Ը�⽫��õ�Ӣ������ΪӢ��ʵ����
�����������ǫ�������������ˣ��������µij��辯�룬�ֵ������ڶ��̶�����ֹ������ѧ������ͷ�о��أ�
����������˼���������Ǹ��桰���š���1991��9�£�����ʦ����ѧ��ʷϵ�븣��ʡ���Ժ��ʷ�о����ȵ�λ�ڸ������ٿ������纣ս�еķ���ǫ�����־��ᡱ�������桶���ռ���ս���з���ǫ�������ּ�����Ϊ����ǫ������˵������ǫ���й����������ܳ����˲ţ��ں��������������ļ��纣ս�У���Ӣ����ս��ָ��Ա������������������Ĺ۵��ѻ���ȡ��һ�£���Ҳ��ѧ���о��ϵ�һ�����š���
���������ǣ����Ϻ��ˣ�һֱ��Ŭ��Ϊ�����˷��������У�����ǫ�þ�������ֶ��Ů��ٳ���ֳ����������������ֻἰ���ļ��ij��棬������ʵ�ġ����Ĺػ������ں�������ʷ�ı�����ۡ�
�����º�������֪�Ľ���ʷѧ��������������֤�ݷ�����������Ȼ��ֹ���˸��������Ϸ�������ǫ�ʾӡ������������ҡ�������ʽ�ľ��С�
������ʷ�Dz���ԩ���ġ�
��������������������������ʷ�ġ����徫��Ľ������������ʷ��¼���ھ����������������������빫����
���������㹻��֤�ݣ�����ǫ��ȻҲ���Է�����
���������ڵ����⣬˭Ҳδ�ܴӷ���ǫ��ս���ӵĸ��˵�����Ѱ��Ӣ���˸��Ӣ��ҵ������
�����������ӣ�����ǫ����л���£�Ҳ�DZ����ļ��㣬�ʺ�����Ҳ�����ʬ������֤�ݲ��������£���æ���������������ڼ���������������Ȯ�ľ�̬�����Ǻ����˵�������dz����
��������������壬̫ϲ��������Ӣ����Ǵ����ͽ����֯��ʷ�ġ����顱�롰��ѵ���ˣ�����̫ϰ�߽���żȻ����֤���㷢����һ��ĺ����ˣ�����̫������м������ϸ�ڶ����Ի����ػ������ʱ���������������ˡ�����������顱��֮��Ч������ѵ��ѵ�����룬ץ��ס�µġ�żȻ�������������ھɵġ�ϸ�ڡ���������ʧ�ܡ������ѹ����л����Dz��ܽ����������һ����в��Ԥ�����ƺ�Ӧ����ϵ����ս�Űܺ����۴�ý�����������������������ǵص�Ӣ����������������������ﰸ��
�����ص���������֮ս����ʷ�ܽᣬ������Ϊ�ձ��˵ġ�ʤ�������й��˵ġ��ܡ���ӡ֤��ͬһ������ʷ������������������Ϊ˫����ʤ�������ܡ��ѳ�Ϊ��ʷ��ʵ���Dz�����˵�ġ�
������ν����ʷ����������ָ������ʷ���ɡ�˳Ӧ��ʷ���ơ����ֱ���Ťת����ʵ֤���˵���ʷ��Ǩ�����֡���ʷ�������ų���ѧ���ᣬ����Ҳ�ų��������ҵ�������ͬ��
�������������Ҳ���е����ѻ��������£���ġ���ʷ�������ۣ��������ǡ���ʷ������������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