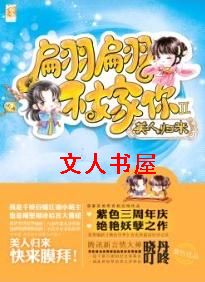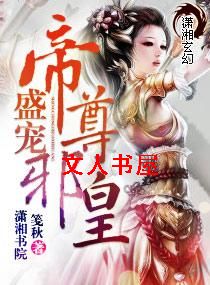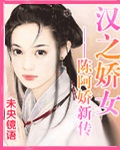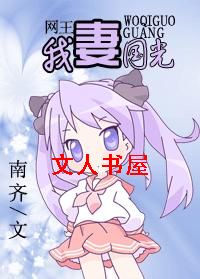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放下小说而拿起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恶痛绝得迫不及待的鲁迅,是一个耽于战斗而荒不择路的鲁迅,是一个不惜耗尽自己的文学生命而与旧文化纠缠和斗争到底的鲁迅。
如何批判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鲁迅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学理的,或曰理性的;二是形象的,或曰文学的。
读鲁迅的杂文,我们常常觉得痛快淋漓,仿佛观看一场武林高手的撕杀。鲁迅手持利剑,面对强敌,见招拆招,须臾之间将强敌致于死命,而后利剑入鞘,转身扬长而去,身后一片残骸。
这种痛快淋漓,正是来自鲁迅学理的批判与文学的批判交错辉映的结果: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感性的温度。
所谓学理的手段,就是以西方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作为参照系,运用辩证的方法和逻辑推理的论证过程,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观照,作出深刻的批判。
学理的批判,首先要有理性的工具。鲁迅所用的工具就是西方的理性主义。自由、*、科学、*等西方现代思想资源,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观照的基本工具。著名学者汪晖在鲁迅论名著《反抗绝望》中认为,鲁迅的批判理论有着双重的历史基础,一是“面对中国封建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沦落而作出的历史选择”,“鲁迅选择的是人的解放”;二是“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自身的怀疑”。汪晖认为,“鲁迅的‘人国’是对中国专制制度及其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政治及其公认价值的双重否定”。可以说,汪晖的观点,确实指出了鲁迅思想充满矛盾的特征,而且也在细部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但如果从宏观上作整体看,鲁迅仍是以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为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所谓的对“现代自身的怀疑”,本身也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而在鲁迅的思想中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只能表明鲁迅的批判,从来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批判,而是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气质,他是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攻击的思想家,带有强烈的生命个性。
以杂文名篇《我之节烈观》为例,整个批判的过程,鲁迅都是以西方现代理性旗帜下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平等”、“妇女的生命与男人一样重要,同样应得到尊重”为潜台词,对不合理的旧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学理的批判必须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展开。在对“女子节烈”的批判中,他先从不节烈的女子并不害于国家的角度对节烈提出疑问,接着又从“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论证节烈之荒唐;再从“表彰之后,有何效果”的角度否定节烈的意义。通过常识加以否定之后,作者又更深入一步提出问题并对节烈进行的否定:“一问节烈是否道德”,“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从而将节烈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肢解得“如此支离”。理论上的批判结束后,作者又进一步考察了现实生活中节烈存在的缘故,深刻揭示出“节烈”对中国妇女的深重戕害。正如钱理群在《“保存我们”是“第一义”》中所评,“鲁迅把五四时期的怀疑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就像医生解剖尸体一样,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的陈尸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正面反面,从学理到人情,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又是那样无情地、不厌其烦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疑了又疑,问了又问,从现实到历史,从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根源到群众基础,刨根问底,穷追不舍,思考极其周密,驳诘十分雄辩,真是锐不可当。他的所论也就具有了铁的逻辑的说服力。”
鲁迅的杂文、杂感一方面具有这种浓烈的理性风格,能让人在清析的思路中看穿旧文化的腐朽,使人建立起理性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有着浓厚的文学的气息,具有十分生动的艺术形象感。这就是鲁迅对旧文化批判的另一种形式:文学的、形象的。
形象的,或曰文学的批判,是指鲁迅通过塑造形象,运用文学的手段将批判的诉求传达给读者、在情感上引起读者共鸣以达到感染读者的一种批判形式。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依赖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进行,而且让读者在文学作品中回到国人生活的现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压迫,以唤起“疗救的注意”。形象手法的批判形式,一方面作为杂文中的重要因素,配合理性的手法,相得益彰,让人在理性的犀利目光下,感受形象的温度。但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鲁迅的小说中。它通过塑造生活于旧中国的孔乙已、祥林嫂、阿Q、六斤、单四嫂子、狂人、疯子、华老栓等人物以及再现末庄、茶馆、吉光村、咸亨酒店、酒楼、陈士成的老宅等生活场景,重现了旧文化控制下的社会生活原貌,让读者从作品主人公的命运中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反动的本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不仅表现为对旧文化的简单而直接的否定。鲁迅并不将中国传统文化作整一观,针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鲁迅在否定之外还进行了揭露、驳斥与价值重估。他的小说,大多以揭露旧文化的腐朽为主题,向读者敞开被长期遮蔽的旧文化腐朽一面和狰狞面孔,使人们在认识与感染之中对旧文化加以否定。对旧文化中的错误观念,鲁迅则毫不留情加以驳斥。在他的杂文中,鲁迅针锋相对地驳斥从旧文化中产生的错误和反动的观念,使现代理性的观点更加明晰。对旧文化中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的文化,鲁迅运用的是价值重估的批判方式,进一步澄清文化价值理念。
不管是学理式的分析还是文学化的感染,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始终如一的。在批判中,鲁迅作为批判主体与中国旧文化传统之间是对立的,即就是说,鲁迅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否定的。这就像面对旧文化象征的雷峰塔,鲁迅是从塔外一砖一瓦地将之拆除,虽然这样拆除的,有时是塔的梁柱,危及整个旧文化体系的庞大建筑,有时不过门头之类的装饰小品,无关大体。
有人说,鲁迅不但解剖别人,更是敢于解剖自己。因为鲁迅本身也将自己作为旧文化的一个残余对待的,他明确说过自己是“从旧营垒来”的,身上带着旧文化的鬼气,对自身毫不饶恕的批判,更能说明他没有放过自己眼下旧文化的每一个腐朽之处,使得他的批判更具反省式的意义。
从外部批判旧文化,对旧文化的破坏只能是点点滴滴的。只有到了鲁迅晚期创作的《故事新编》,我们才看到,鲁迅才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与核心之中、深入中华文明的古塔内部,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为致命的手术:解构。
第三节 批判与解构
第三节 批判与解构
文化的通约性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史,就是一部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史。西学东渐,堪称是两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最为壮观的文化现象。从国家的组织形态的宏观体制,到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形式,从哲学、政治、宗教、文艺等意识形态到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无不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今天,它又借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手段,使这种现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在消极的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的江河日下、日渐式微;在积极的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大气磅礴。若从世界文明交流的更高层次上说,这过程不正说明了人类具有超出不同文明范式进行交流的可能吗?我相信,在这个无比壮观的过程的表面之下,不同的文明体系之内本身就自然地存在着相通的、最基本的文化因子、文化结构、文化价值或文化自觉,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些不同体系文明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这一信念在我对《故事新编》的理解中又一次得以印证。在这部由近百年前的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一个对中国旧文化极端得无以复加的批判者,对中国旧文化的批评采取的一种态度:解构。解构,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加以拆解、怀疑、否定和重估。这种将拆解、怀疑、否定与重估融于一体的解构,在西方哲学文化史上,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在从法国知识界走上人类知识系谱的舞台的,两者相距了三四十年。
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不同的文明体系中,产生基本相似的文化现象,这并非完全偶然,而是缘于文化本身具有的通约性。文化的这种通约性,能使得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各自封闭的体系内沿着各自的方向成长与变迁的过程中,呈现出相似与相通的东西。
西方哲学中的解构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解构主义,是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后结构主义中发展创立的一个哲学派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里达沿着后结构主义的路径,在对结构主义、胡塞尔现象学以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的方法。
大体来说,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而上学本质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构阅读呈现出文本不能只是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
由于德里达本人并没有对解构主义进行直接的总结与定义,解构主义似乎一直显得难以表述。他的解构哲学是“寄生”型的,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法,表现在德里达对西方大量哲学经典的阅读与理解之中。
“解构”一词是德里达从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发展而来的。针对结构主义认为“人有一种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构造能力”,以及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传统认识论,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在作品之中解开、析出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多重意义”,“使一种解释或意义不致于压倒其它各种”,从而揭露真理的虚构性,“强调意义的绝对自由,认为对于任何一部作品,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特有的批评,而对于这个人的批评,其他人又会有不同的批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的疑问永无止境,永远不会有结束,形成开放的场。”(朱立元P935)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
这样,德里达的解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方法,更是一种新型的知识,新知识/思想的生成形式,或者可以不无夸大地说,最具有未来面向的知识生产形式。”(陈晓明P3)在对结构主义的解构阅读中,德里达引入时间性,否定结构主义的中心主义性质。在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的解构中,引入了“延异”以否定现象学的“本原论”,即,“本原总是处于延异之中,它总是延迟着到场,在它内部总已蕴含着区别、差异。”(朱刚P35)晚年,德里达又展开了对正义、伦理、法律、政治的解构,使得他的解构哲学更加丰富而繁杂。
然而,解构主义并不是否定、怀疑一切。即使在前期批评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时,德里达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寻求肯定性;后期的德里达则更是一直在寻求意义与价值的肯定。所以说,真正的解构,“并不是简单的颠覆、拒绝和否定”,(陈晓明语)它是有底线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今天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解构理论的观照下,本质主义、同一性、二元对立等都将成为重新质疑的对象,它几乎颠覆着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在哲学史上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开创性的思想源泉。
解构的本质
德里达的研究领域涉及面非常之广,又对解构主义理论没有系统的论述,他本身也反对以系统化的方法对其理论加以总结和理解。他的理论都在他对不同作品的阅读与诠释之中。面对内容庞杂头绪纷繁的解构主义理论,既使专门的学者也难以完全理清,更惶论一般的读者。
弱水三千,独取一瓢。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既要深入理解掌握解构主义这一对后现代具有开启意义的重要批判方法,把它作为分析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基本工具,使自己的思想从一元化的、已经板结的知识结构中解放出来,勇于对知识发出自己的声音;又要尽量避免陷入德里达深邃、晦涩的哲学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