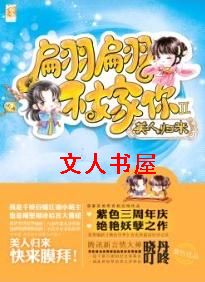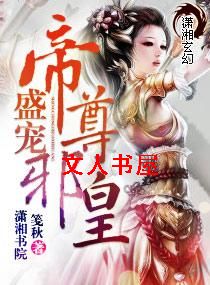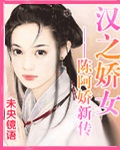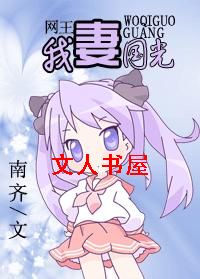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统治者长期以来的瞒与骗,又使得中国成了一个愚昧与麻木的社会。革命变成了闹剧,鲜血成了治痨病的良药;单四嫂子儿子病危之际,伸来的不是援助之手,而是乘人之危,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冷漠。面对革命者的杀戮,是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无聊看客,是“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因而,鲁迅作出了惊世骇俗却直达本真的结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人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厨房。”
可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厨房里,都生活在这样的暗夜。非人、扭曲、没有希望,这就是暗夜,白昼也需要点灯的暗夜。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像无边无际的暗夜一样的中国的社会现实。
在暗夜中突围
面对暗夜,青年鲁迅是踌躇满志的。他没有坐视,他从来都是个行动主义者,他要代表中国思想文化进行突围。他“在年青的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他有强烈的改变这暗夜的欲望与责任感。
当鲁迅明白了自己的暗夜处境时,他首先做的,就是弃医从文。他决定投身到文艺活动之中去,立志用文艺改变这国民、改变这暗夜。因为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接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熏陶的鲁迅,就这样投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是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对中国民众从零的起点上进行的启蒙,进行的是一种“横的移植”式的启蒙。
一方面,他竭力将西方文化中最为基本的科学、技术、历史、文化与文艺介绍到中国来。1907年,他完成了其早期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人之历史》、《摩罗诗力学》、《科学史教篇》及《文化偏至论》,1908年又完成了《破恶声论》。这些作品,常常成为鲁迅研究者对其思想分析的基本资料。事实上,这些作品包含了鲁迅的世界观及对东西文化中许多关键问题的理解,并且成为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几乎涵盖了鲁迅思想的所有重要问题。但如果从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来看,写作这些作品的行为,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富有世界眼光的、对改变黑暗中国充满信心的思想者的形象。林贤治先生在对比鲁迅与卡夫卡时曾说过十分精辟的一句话: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这对于鲁迅一生的精神特征的概括是十分准确的。但在早期的鲁迅眼里,世界仍是完整的,道路与天堂并没有分离。鲁迅企图用西方的科学、文化、历史观、文艺来改造中国,而他亲手做的,就是将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用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精神来来重新塑造现代中国文化,用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来点亮暗夜般的中国。
另一方面,他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他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寄希望于办报刊来推进文艺运动以影响和改变这个暗夜般的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在暗夜中新生。可是,就在他的《新生》快要出版之际,曾经一起谋划的“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新生》腹死胎中。它的失败,是鲁迅积极改变社会、推动思想启蒙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交战的第一个回合。《新生》的夭折,给热血沸腾的鲁迅兜头泼下了一盆冷水。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有如“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鲁迅终于感到,道路与天堂原来并不总是在一块的。
纵观近现代史上,办报刊半途而废者并不鲜见,但大多数人却始终表现为一种“屡败屡战”的韧性与勇气,为何鲁迅却偏偏如此深地感到寂寞与痛苦,难道是他的承受能力太差之故?当我们联系到鲁迅早年由小康之家而中落的生活经历时,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的这种寂寞与痛苦,实际是他特有的敏感、忧烦与阴郁气质的表现。而这,早已在他少年时期就已形成,而且终其一生。这种特有的气质,也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始终有一种透彻感、保持一种力透本质的、犀利的、冷冽的目光,使他总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于常人很正常不过的一次办刊失败,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说,却内化为一件十分严重的心灵事件,并在他以后的书写中常有提及。在《呐喊。自序》中,他说到;这件事让自己看见了“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办刊失败的经验,让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局限,看到了个人在暗夜面前的无能为力,同时,也让他从踌躇满志中清醒过来;更加明白了自己所面对的暗夜的无比复杂性。
联系到他后半生进行的尖锐的思想文化批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鲁迅早期启蒙作品和办刊的愿望,理解为他对推动中国思想启蒙所进行的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鲁迅企图以启蒙思想的传播为已任,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在中国文化的革新发展中作出自己个人的努力。,从而改写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命运。实现启蒙思想的传播,一方面当然需要将西方现代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另一方面,这样的介绍也需要良好的载体进行传播。鲁迅早期几部介绍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作品,正是他对西方思想文化努力推介的结果,他要将西方关于思想、历史、文化及文艺的观念输入到中国的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去。
至此为止,鲁迅所进行的启蒙是建设性的,他是在正面的角度推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
可惜的是,他推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正面努力过早地夭折了。办刊的失败与他特殊经历造成的、从小就埋藏在心里的阴郁气质遥相呼应,使他走向了建设的反面——批评,并且终其一生。
办刊失败只是个引信,引爆了鲁迅本已内在地储存的反抗精神的烈弹。漆黑的屋子里,没有光明,鲁迅本想点起一盏灯;现在,既然灯也点不了,不如干脆掀掉这漆黑的铁屋子——这或许是暗夜中突围的最好的办法?
在沉顿中奋起
“破”与“立”,是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基本方式,也是任何一种文化改造、革新过程中必须做的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事。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干预也是从这两方面进行的。所谓“立”,就是建设,就是为中国思想文化添加新的内容。鲁迅在1907年所写的这一系列作品,以及他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都是他在建设的方面所作的努力。他的努力主要是从西方“拿来”“火种”,为我所用,将进化论、科学思想引进中国的文化体系;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过从中国文化的自性中去寻找积极的因素,并小心呵护它的成长。
所谓“破”,则是拆除,就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除去那些腐朽的内容,扫出一片可以安放新文化的空地。鲁迅一生的奋斗,所做的主要还是“破”的工作。他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旧思想文化的领地里逡巡,不断揭露日已颓废的旧文化的专制和陈腐的本质,“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早期小说,某种意义上所描述的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统治下人们苦痛的生活状态,并通过再现人物的苦难生活有力地揭露和鞭笞着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的戕害。他的大量的杂文,像匕首与标枪一样犀利地深入到了传统思想文化深处,并将其中陈旧与腐朽的东西逐个加以扫除。
孟子曾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从建设到批评,鲁迅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
当他在失败的无奈中感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时候,他深深地懂得,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那是多么的困难。必须为新的建设清扫出一片场地!
可是,暗夜还在弥漫,自己却无法为改变社会现实尽一份力。
鲁迅陷入了深深的虚无之中。在S会馆的那些日子,他度过了一段人生最为消沉与颓丧的生活。他让自己沉醉在钞古碑的无聊中以抚慰虚无的侵袭。那些时候,“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他任凭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
鲁迅说:“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
好在,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选择,否则,我们今天无法看到一个叫做鲁迅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被沉默压垮的人。他没有被暗夜所吞没,他终于走出了暗夜的屋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历史,从来就不全是必然性的总汇,有时,一些偶然性的参与,常常让历史显得更加精彩、曲折与迷离。我当然不排除鲁迅在沉寂十年之后走出书斋的必然性,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无量功德归于鲁迅的同乡好友钱玄同名下。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之间那席早已传为美谈的对话,终于在鲁迅对暗夜的绝望之中,闪进了一丝希望的微光。“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将信将疑,觉得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有。”
一个迂回之后,当鲁迅再一次直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他不再着意于“建设“,而着意于批评,不再着重于“立”,而是侧重于“破”。他要清理出一片可以让西方科学与理性精神自由生长的思想文化空间。
最早进行鲁迅批判的作家是李长之先生。他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将鲁迅的精神进展分为六个阶段,并将1918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之前的一段时期称为鲁迅精神进展的第一阶段:成长和准备期。李长之的批评虽然很早,但构制初定,对之后的鲁迅批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鲁迅批评》一书也成为了至今为止鲁迅批评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在这里,李长之清醒地看到了早期鲁迅的文言论文在思想上与之后的鲁迅作品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看,从“立”与“破”的角度看,这第一阶段,则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积极建设的时期。而此后的整个大半辈子,则是鲁迅运用批评的手段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塔进行“拆除“的时期,直接的“建设”是很少的。
有人曾经不解甚至责难,鲁迅一生著述中缺少长篇巨制,没有较系统的学术建树,与一个思想家的身份不够相称,在五四一代学人中算不上成绩斐然。弄清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从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处于“破”的角度进行考虑方能全面理解。我们看到,1908年之后,除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之外,鲁迅就再也没有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篇作品,也少有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篇章。相反,除了短篇小说外,他大量写作的是短小精悍的杂文,间或少许散文。这一方面当然是“战斗的需要”,同时也是“破”的思想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大凡建设者,才会大兴土木,平地起高楼;而拆除者,却是一砖一石、一瓦一梁地逐个敲掉。不论是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入,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加以保存,都是系统性的工作,都十分需要学术上的专门深入,并以专门的学术专著加以巩固。偏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却是难以大制作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往往“建设”者多,而“破坏”者少。作为一个比较彻底的“破坏”者,鲁迅没有大制作虽是一大遗憾,却也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从整体看,鲁迅一砖一石的“破坏”互相响应,彼此嵌合,不也同样构成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个体系最为有力的打击吗?
当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这一点上,鲁迅的批评与建设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的建设,是将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引入中国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构建起更加科学的文化体系,剔除陈旧腐朽的思想;所谓的批评,则是对中国传统陈旧腐朽思想文化的破坏与扫荡,为西方思想文化的来到铺平道路。批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