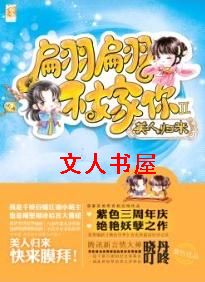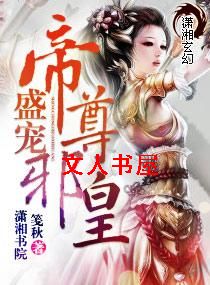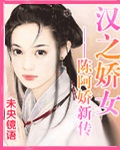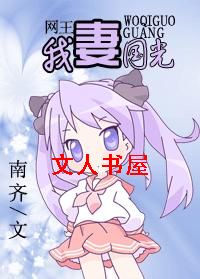�֮��--³Ѹ�����±� ��ѧ̽��-��1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ʵ�ǵ�ʱһ��ʷ��֮�������ǵ�ʱʷ�¶��������һ������Ϊ֮�����ߣ����Ѷ�ר�飬�����Ծ��������������ں�����������֤������֮�����Ĵ�ܶ��Ǻ��������ߣ��ڹ˾�����֤���������˾���ʷ���Ķ����ģ��˾���������֮�ۡ���ʹ�˿��Գ����ߣ�������Ǯ��ͬ���⡣������Ǯ��ͬ���ɹ���ͬΪһ�ˣ�ʵ�Ǵ��ޣ�������νǮԽ�˹�������֮���ᣬ�������ɽ�лƵ���һ��֮��Ц�ӡ�����������������������������ز����������Ԫ�꣬��ͬ�����Ԫ��ĵģ����Կ���νǮ��ͬһ��֮˼��ʵ����й��Ĺ�������ͨ�������ߣ��д�˼��֮�˱ز��ڴ�ʱ����һ���ٷֳ����ʿ��֮�����ɣ�������ͬΪ������֮�֣��̿�˵Ҳ����ͬΪ�˵�˼��֮�˸Ķ���������������ͨ������Ǯ֮һ�ֽ�̵�����Ǯ�ߣ����������IJ���Ȼֽ֮�ҡ�Ƥ�Ҵ��ž�ӡ������ǧ��ǰ����һ�ֲ��㵱�Ŀ���Ʒ����ʱ������Ϊ��Ȼ��������ȱ���Ѷ���������ͭ���һ�����ʣ���Ȼ�Լ�������������ͬ����β����ն����֮��������һ������֮����Ϊ�պ���ϸ˼*��ʵһ�������������ǹ��ӣ�����Ϊ��ͬ���������飬��֮ԻǮ���Ա���ʵ�����������������ʵ����Ǯ�ߣ��Դ��෴֮��Ϊ����ʵϵһСС������νǰ��Ի�����������ǣ������������ޡ����Լ����أ�Ǯ�������������ɹţ��ɹŶ�����Ǯͬ�Ժ���ΪŦ�������串����˼�����ֱ���һ�м���Ǯ�������������ڳ��������˱�������֪�ں���֮�������ϴ�����˱���֮����֮Ŭ�����������־����ʷ�ⰴ�˱ؾ�֮��ʷ��Ҳ��������ζ���֮������˲�һ�ᣬ��ϵ���������ˣ�һΪһ����һ�йʴ�����֮�ߣ�һΪһ��̸��ʱ֮��νע����ĸ�ߣ�һ����Ϊһ��һ�ּ������ξ�ʷ�����ߣ���ν�ɹ���ͬ��Ҳ����������radicali*��������ͬ����Ȼ��ǿʹ�����ͬ��ʹ��ɲ�ǰ��һ������������ǿ��ɴ�ǰ������һ��֮״̬���Ӵ���Ϊ�����������϶�ĩһ��ͬ���ɹţ�ʵ���վ������֮�ۼӴ����¶���֮�����������൱ʱ����������ν֮������������������������һ���ߣ�����������Ϊ������һ��֤�ݾ�����飬��ϧ�����˵ز���٣���ϧ����ϧ���ҵ�ע��ν��ţ����Կ���ͬ����һ��������֮���ԣ�ʼҲ����һ��ɨ��̸֮������֮�����ڱ羭�ɹ�֮��������Ǯ��ͬ���ˣ�����һ�����й��������ߣ���������֮���ģ��֣��пɼ�������Ū��Щ�й����£�����Ը���ȥ֮������Ⱦ��羭�ɹ�֮һ����Ȼ����Ŷ�����Ϊһ��ɨ��̸֮����Ϊ˳������������һ��ɨ���ӣ��ְ���ת��������С��ղղ֮�ɹ����գ����ֵߵ�֮���𣬰�֮��ʱͨ��ΪȻ��������֮���˻����˼����������ۣ���Ȼ��������֮�˾�֮�۲�����֮��֯ѧ�����ޣ�Ʃ���н���������£�ʤ���������Ա��Ȧ����Ҳ�������������֮��֮�ɹŶ����������֮��֮�ţ���֪�����֮���Ե������纺��֮�˶�����˹������������νʷ����Ȼ�������ܹ���ν�����������˺������ߵ�˵����ʶ����ЩȦ���Ӷ�����ЩȦ�������Ժ���֮����������������ߵ�˵������֪û������������û�����������Ĺ��£�ƫ�Ա�һ���飬˵���������Ĵ����������ӿ��İ취����֪û�����ܣ���û����������ʷ����£���������ι��£�������һ���飬ʹ����ѧ����֮����ͬ����������֮ƾ���飬ȴ��˵��ʷ��������֮���ˡ���ʱ���յĽ����İ취����֮������ʱ���Ĺ����������IJ���������ϧ��
��������ת����֮���ǵ���ͬ���������СС���ɹ����ѱ��ް������߲�Ī�����أ�������������ԱС�������Ͼ����ʹ���˰�֮Ҳ���������ԡ��й��Ļ�����12�ڣ��ɶ���ʤ������
������˹��ġ�Ϸ�ۡ��ǶԹ��ա�ϵͳ���ɹš��Ľ�����ٽ������ʮ�����͵�һ���С������С����ˣ����ա�ϵͳ���ɹš�����ʷ��������������ġ�Ǯ��ͬ�����п�֤�����ó��Ľ����ǣ�û��Ǯ��ͬ���ˡ�����û��Ǯ��ͬ������������Ҳ���ݳ��ˡ�����յ��˼仯����������Ҳ���ˡ���������һ�����š�����˹�����Ǽٽ衰�����С��������������ڵ������ó������Ľ��ۣ��Է��������ϵͳ���ɹš������롶�����±ࡷ�еġ���������������ͬ��֮�������õ�txt������
�ڶ��ڡ����������±ࡷ����ɵġ��ع�һ�м�ֵ��
�ڶ��ڡ����������±ࡷ����ɵġ��ع�һ�м�ֵ��
�������˼����³Ѹ������Ʒ
������ãã�˺��У�һ���˵�˼���ܵ���һ���˵�Ӱ�죬����˵����������˶�������һ����˼��Ӱ�죬���˻�����ʱ��ʹȻ֮�⣬�����ţ������ٻ�������˼���Ը��б����������Ƶ����ӣ������ں��߽Ӵ�������������Ҫ��Ӱ���˼��ʱ�����ܲ����dz�ǿ�ҵĹ������ܿ�ʹ�Լ����ڵ�˼����ѿ�����������Ŵ�³Ѹ˼���ܵ���ɵ�Ӱ�죬����Ҳ����Ϊ��³Ѹ��˼���Ը�������������Ƶijɷ֣�����˵���������Ƶ���������ỷ����
��������³Ѹ˼�������֮��ľ���ԨԴ�������н϶��ۼ�������ʱ�ڣ�³Ѹ�ĺ�������ũ����˵��³Ѹ�ǡ�����ѧ˵��κ�����¡����Ə���ڡ�³Ѹ�����ġ���˵��³Ѹ���������ķ�������ɵij��ˣ�����Ž����ۣ��������ڽ��ĸ����۵ġ�����Ԫ���ڡ�³Ѹ����ɡ���������³Ѹ����ɵ�˼�룬��Ϊ�����ڵ�³Ѹ��һ��������*�����ߣ���������ʱ���Ϸ�չ������ε���ʶ��̬������������ɲ��ܴ������ϵĽΣ��෴�ģ�������Ƿ����Ĺ���εĴ����ˡ��������ڡ�����������һ���У���³Ѹ����ì�ܵ�˼�����������ķ������ڶ�³Ѹ����˼���еĸ���������з���ʱ����һ��������³Ѹ����ɸ�������֮��Ĺ�ϵ����ѧǫ�ڡ�³Ѹ����ɡ�һ���У���³Ѹ����ɷ�����ѧ�����½������⣬��Ϊ³Ѹ����ɾ�Ϊ�����Ļ������������Ļ����������翴���������仯�Ĵ��ڣ�³Ѹ�Ƴ�ġ����˵��Դ�����ɵġ�Ȩ����־���������ڵ�һ�£����Ƕ��Ƿ���ͳ�ģ�����������һ��ǿ�ҵŶ������������С�
������³Ѹ�����˼���ϵ���о������������Ĺ������³Ѹ˼�뿴��һ�ɲ��������Դ������ߣ�ֻ�Dz�����³Ѹ����˼�룬����³Ѹ���ڡ��ر���д���������±ࡷʱ�����˼��Ľ��������������١�
�����ں������ġ�ԨԴѧ�о���һ��������³Ѹ����ɵĹ�ϵ��һ���У���³Ѹ�����˼��Ľ��ܽ����˽��Ե����֣��ȽϿ�ȷ�ط�ӳ����ʵ�����߽�³Ѹ����ɵĽ��ֳܷ������Σ���һ��������֮ǰ�����ڣ�³Ѹ����ɵ���Ҫ̬���ǿ϶��ġ������ģ�������Ϊͬ������Ҫ�����ڡ��Ļ�ƫ���ۡ���Ħ��ʫ��ѧ�����ƶ����ۡ���ƪ�����С��ڶ���������ǰ��1927�����ҵ����ڣ���Ҫ̬���ǿ϶��ģ������еijɷ������ˡ����϶�����ǡ�ż���ƻ��Ĵ�������ǡ��ɹ������ɨ���ߣ���Ϊ��ɵ�������ǰ���˵ģ�ͬʱ��Ҳ��Ϊ��ɵij��ˡ�̫��ã������Ϊ��ɵ�һЩ��������һЩ����ì��֮��������������1927��֮������ڣ����ڵ�³Ѹ����ɼ�����һ�ʣ����䳬����ѧ������˼���������������ڡ��й�����ѧ��ϵС˵����&��#8226�����ԡ��У�³Ѹ��������ɵij�����ѧ˼�룬ָ��������ɽ��������ų��˵ij��֣��Ȳ����֣��������ǿ��顣�����ȴ�������³�֮���ģ�������������Ͳ��ⰲ�ڿ��飬���߷�������飬��ʹ�ڹ¶��к���ĩ�˵�ϣ����ů֮�ģ�Ҳ��������һ��Ȩ����������Ϊ���������ߡ���
�������պ������ķ����۵㣬³Ѹ�����ƺ���ȫ��������ɵ�˼�롣����Ȼ������ʵ�����ġ�������³Ѹ�������ѧ��̬�ȷ���ʱ���н��п��죬ȴ��ӳ��³Ѹ�����˼�벢������ȫ������һ��ʵ�����ң��ڲ�ͬ��ʱ�ڣ�³Ѹ�����ܵ����˼��������Dz�ͬ�ġ����˿������ǿ��Դ��Եؿ�����³Ѹ���������ڽ�����ɵ��������ۣ����ڲ����ڸ������壬���Ÿ��˵Ķ��������ڣ����ص���������ɵķ�ż���ۣ������ˡ��ع�һ�м�ֵ����
������Ϊ������Ʒ�ġ������±ࡷ�����ǿ�������ؿ���³Ѹ�����˼���̬�ȡ�������Ʒ��³Ѹ���ǽ�����һ�ֶԳ����й���ͳ˼���Ļ��ġ����ı��������εĻ����ϵģ�ʼ����һ�֡��±ࡱ����̬�������������¡��������֡��±ࡱ�Ĺ��̣�ּ�ڶԡ����¡��ļ�ֵʵ��ȫ��ĵ߸���������ǿ��������³Ѹ�Լ���˵�������������±ࡷ�ij��Ծ��ǡ���һ����Щ���ֵ���ء���
����³Ѹ�ġ��ع�һ�м�ֵ��������������������ġ�û�е��ߵġ���ż��һ��ȫ���Ƶ���³Ѹ�ġ��ع�һ�м�ֵ��������ȫ�����ǽ��й���ͳ�Ļ���������ۣ����й���ͳ�Ļ��е��Dz��ָ�������ݣ�ȴͬ�����ڿ϶��������������������ݡ��ڡ������±ࡷ�У�����������ҵ���α֮�⣬ȴ�����϶���Ů洵Ĵ��쾫����������������ī�ӵ�ʵ�ɾ������˵ĸ������Ƿ����ڷ��Ҿ����أ��������й���ͳ�Ļ������˻����ļ�ֵ�����������ݡ�
����³Ѹ����ϵͳ�ؽ������˼��ġ����������κ�����������ѧ�������һ���������Ǵ��Լ����еĹ۵���������Լ����������������ȥ����ѡ�ֱ桢���ջ���������
������������ڶ����û�����ƵĽ��ܣ������³Ѹ�ƺ��Եø��ӳ��죬�������ԣ����ӡ��ع�һ�м�ֵ������������ˡ������±ࡷ��ʹ³Ѹ�����˽�й���ͳ�Ļ�֮·��
������ɶԽ�����Ӱ��
�����ӹ�����˹��������ɵij������ִ�˼��ʷת����ִ��ı�־�����ڡ��ִ��Ե���ѧ�����ָ������������ɽ����ִ��ԵĻ���������۾��淢���˷��츲�صı仯������ת���Գ������������ĵ��ߡ�����ɸ���ִ��������崫ͳ��������ͼ���������������ڲ�ȥѰ�����Ҹ��µ����ݣ�����ת��ȥѰ�����Ե����ߣ��Ӷ���ʹ�ִ�ת����ִ����õ��˲����ִ�������˼��ҵ���ͬ������������ϣ�������ƺ����Լ̳�����ɵ��²���������ڡ�ǩ���IJ��͡���1981���У�����������˺��¸������ɵ����⣬���Ժ��¸������ɵ�˼�뿴��һ�����壬��Ϊ��ɵ�˼���Dz���ͳһ�ģ�Ҳû�������ԡ�����������һ˼·�������һֱ����ȥ���Ӷ�������ɵ����ֲ���ͳһ�ġ��������Ե�˼����չ�������������Ƿ����ζ���ѧԭ��ij嶯���ǻص�������һ������������������������Ҫ����ɵľ���������żȻ�Ժ����⣬���ֶ��������Ϸ�����ɵĴ���Ŀ��ֿ϶����Ƕ�ij����������������Դͷ����ij�ֻ��������ṩ�����ĵķ�������Ŀ϶���������P20�������������͵����ˡ����������塢�۳���ȡ�ȥ��Ŀ���ۺ��ռ��ԡ�ǿ������Ͷ�Ԫ�ۡ����ݣ��Ա����Ρ�ǿ�����ߵ���������ڽ��ԡ���������ȵȡ����⣬�����˽���塣����������������ģ���������ڰ���ɴӺ��¸�����ζ���ѧ�����ȳ�����ͬʱ����Ҳ�������Լ��뿪���¸���������Զ�����Ǹ����������Ҳ��һ��ʼ���ǵ�����Լ�����ʱ��ɵĵ����Ǿ��Ǻ��ִ��Ŀ����ˡ������������������ĵ��ߡ���
����һ�仰�����Ǵӵ��������ϣ���������ɵġ��ع�һ�м�ֵ�������ͱ�Ȼ�ص����˽��³Ѹ���š��ع�һ�м�ֵ�����й��Ļ�����ĵ�·���ߵ��ˡ������±ࡷ��չ���˶��й���ͳ�Ļ��Ľ�����������������������ѧʷ�Ͻ�����һ������ʽ�ĵ߸����ߵ��˽������ѧ�������˺��ִ��������ܡ�
������ɵ����ֽ����³Ѹ�͵����
�������ڶ������ݵ���ɵġ��ع�һ�м�ֵ�����⣬���Dz�����³Ѹ�͵���������ɵ����������һ������ѧ����һ������ѧ����һ���ڶ�����һ����������
����������һ�����ϵ��������ӣ���ʹ���ո����Ǵ������滷���ٴ�IJ�ͬ��������������������֮�����ò�£�ȴ������ͬ���ںˣ����
���������������ζ���ѧ�Ľ�dzɹ��ģ�������ѧ�Ͼ�������һ���µ���ѧ��Ԫ��������Ӱ���������ǡ���ȶ��ԣ�³Ѹ���й���ͳ�Ļ��Ľֻ�ǿ��˸�ͷ����ֻ��ץסһЩ�ؼ�����Ҫ�����ݽ����������Ĵ�������ң���ֻ����ѧʽ�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