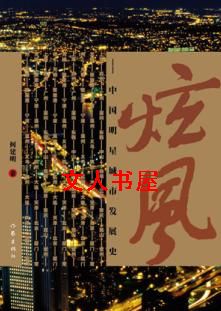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诗学(增订版)-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叶燮
叶燮说“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这种美感经验过程是直觉的,非演绎的;他又说:“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显示他正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信徒,不相信诗有“逻辑的结构”(这是他——和其他中国批评家一样——所不同于美国新批评家所构成的“形态主义”的地方);但毕竟他说话了,他用疑问句的方式分析这句诗在我们直觉里所发射出来的多义性的层次,而使我们(读者)的直觉得来的浑然的灵感经验有了眉目更清的印证;但我们并未由具体的经验逃出而落入抽象思维囚牢中,我们还是握着“当时之境会”。疑问句的分析方法,与凶巴巴而来的权威性的肯定句的分析是不同的;疑问句有待读者的点头,叶燮把心感活动非常技巧地还给读者;在后者的情况下,一切要听批评家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叶燮给了我们非常有效的说明性的批评而无碍于美感经验呈示之完整,这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诗的“机心”,“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辨,恐至此亦穷矣。”而缺乏了这种基本的顾虑的批评家,必将诗分割到无可辨认而后已。
我的第三个例子是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中论到陶潜饮酒诗第五首的文字,这篇文字里可以说具有叶燮之长,而尤有进者,分析及于单字的多义性,且贯及全诗前后的呼应,实在是“形态批评”最上乘之作,由于本篇太长,且录一段见其经纬: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3)
……庐之结此,原因南山之佳,太远则喧,若竟在南山深处,又与人境绝。结庐之妙,正在不远不近,可望而见之间,所谓“在人境”也。若不从南山说起,何异阛阓?然直从南山说起,又少含蕴,故不曰“望”,而曰“见”。“望”有意,“见”无意。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来……乃自得之谓也。
批评(在此尤指鉴赏方面的批评)往往是一种回顾的行为,是在诗的美感活动在我们意识里发生了作用以后,对当时的直觉经验的分析。吴淇的批评正是对这种美感经验的分析,在上录的片断中,他仔细地推敲构成其阅读时直觉到的“自然”、“自得”、“天趣”的手段;他的考虑仍是美学上的考虑——同时我们注意到,其间还是含有判值性的因素,下意识里,他是被传统认“自然”为诗的最高理想这一说法(皎然、司空图、苏东坡、严羽)所支配着。
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的理论(或批评)的一些特色加以扼要的复述:
一、 中国的传统理论,除了泛言文学的道德性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外在论外,以美学上的考虑为中心。
二、 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
三、 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说的批评来看,它们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直接与创作的经营及其达成的趣味有关,不是浪费笔墨在“东家一笔大胆假设、西家一笔小心求证”的累积详举,那是种虽由作品出发而结果离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辩证批评;它不依循(至少不硬性依循)“始、叙、证、辩、结”那种辩证修辞的程序——我们都知道,西洋批评中这些程序,完全是一种人为的需要,大部分可以割去而未损其最终的所悟;中国的利用了分析、解说的批评,多半是属于切去了外加的修辞的枝丫的批评(或应说:未强加修辞的枝丫的批评)。他们用分析、解说仍尽可能点到为止,而不喧宾夺主——不如近代西洋批评那样欲取代作品而称霸的咄咄逼人的作风。
在我们回顾传统批评的特色时,我们虽然觉得中国批评的方式(当指其成功者)比西洋的辩证的批评着实好得多,但我们不能忽略其缺点,即是我上面所提到的:“点、悟”式的批评有赖于“机遇”,一如禅宗里的公案的禅机: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答:春来草自青。
这是诗的传达,确乎比演绎、辩证的传达丰富得多。但批评家要有禅师这种非凡的机锋始可如此做,就是有了禅师的机锋,我们仍要依赖小和尚(读者)的悟性;“春来草自青”之对“如何是佛法大意”,在禅宗的看法,是“直指”,是“单刀直入”,但不见得所有的小和尚都完全了悟其间的机遇,这是“点、悟”批评所暗藏的危机;但最大的问题是,有“独具只眼”的“禅机”的批评家到底不多,于是我们就有了很多“半桶水”的“点、悟”式批评家:
问:如何是诗法大意?
答:妙不可言。
于是我们所得的不是“唤起诗的活动”,“意境重造”的批评,而是任意的,不负责任的印象批评。
由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胡先生在“德”先生的旗帜下可以这么凶,不把这些“顺口开河”的批评一扫而清誓不为胡适之。于是前推后拥,泰西批评中的“始、叙、证、辩、结”全线登陆,这因为是“矫枉”,所以大得人心,而把是否“过正”的问题完全抛诸九霄云外,这,在当时确是很需要的;惟有实证实悟才能发挥批评的功能。
新文化新文###动从最开始的时候便强调批评的精神,虽然当时的作者,因处于新旧的交替,还没有提供出完善的方法和客观的态度。五四运动原是一种文化觉醒的运动,百多年来外侮之辱,至此无以复加,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灭亡的恐惧。所谓文化觉醒,便是要雪耻辱,重建民族的信心,要除恐惧,推动新的科技文化以充实国势。要救国,必须要传播新的思想,所以必须要推动口语,作为传播的媒介,使新文化的意识与意义得以普及大众。要他们觉醒到国家的危机,必须对旧文化的弊病作全面的攻击,在当时,新思想者不假思索地揭传统文化的疮疤,呈露着一种战斗意识的批评精神,当时的凶猛程度,我们现在看来,是相当情绪化的,对于传统文化中一些对新文化新社会仍具启发意识的美学内容及形式甚至生活、伦理的观念,对于它们的正面作用完全一笔抹煞者,大有人在。在当时的激流中,要停下来不分新旧只辨好坏完全客观而深思熟虑地去处理文学者实在不多,而且亦非当时的主流。五四时期强烈的战斗的批评精神亦反映于当时的创作里,譬如批判的写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反传统社会的戏剧与小说,为当时最具代表性而贡献也最突出的文学创作,即就诗歌来说,当时所继承的便是西方浪漫主义中革命性的一面,由语言的形态(弃传统不涉理路的语态而袭用说理演绎的语法,强调“我”的重要性,由“我”向“你们”申说当前要义)到题旨,无不具有批评的精神,甚至有时会沉入过度伤感主义的新月诗人,都可以说是在一种对过去制度批判的精神下进行,如徐志摩认为爱情至高至大可以克服万难改变世界等等,固然可以视作缺乏理智平衡的一种宣泄,但这种推崇爱情的态度,后面仍是对传统儒家克制爱欲的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4)
五四的精神之一,便是实证实悟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但开始阶段的作品,常呈现过度情绪化的发挥,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这种矛盾的现象,是任何剧变中常见的历史现象。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形态的回顾,以李长之的《迎中国文艺复兴》(1942年)所提出的几点最值得我们参考,兹列举数则于后:
一、 五四运动并非“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的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可是中国的五四呢?试问复兴了什么?不但对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
二、 五四乃是一种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乃是在一切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上要求明白清楚的一种精神运动,凡是不对的概念和看法,都要用对的概念和看法取而代之。在这种意义下,势必第一步是消极的,对一切的权威、感官的欺骗,来证实的设想,都拟一抛而廓清之……所以这种启蒙的体系太重理智的意义与目的的实效,于是实用价值是有了,而学术的价值却失了……和理智不解缘的,是唯物思想及功利主义。
三、 五四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扬西抑东……移植的文化,像插在瓶里的花一样,是折来的,而不是根深蒂固地自本土的丰富的营养的。
四、 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那时并没有民族的自信,只觉得西方文明入侵了,于是把自己的东西怀疑吧,毁掉吧。
五、 五四运动主张明白清楚,是一种好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明白清楚就是缺少深度,水至清则无鱼,生命的幽深处,自然有烟有雾……五四是一种反“深奥”及“玄学”的态度。
六、 五四在表现方法论上,也是清浅的,很少人谈到体系和原则,触及根本概念的范畴……国人对浪漫主义的误解,以为披发行吟为浪漫,以酗酒妇人为浪漫,以不贞为浪漫……
七、 五四缺乏自觉自信,样样通的人太多,窄而深的人太少。
五四给我们的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怀疑精神,反对人云亦云的批评态度,对传统的批评方法有极大的修正作用,怀疑精神所引发的必然是寻根的认识,在五四时期,由于对于西洋思想方式及内容过度一厢情愿地重视,而不能对传统文化作寻根的认识,到其正面价值的再肯定。譬如当时过度重视功利主义——影响至今——便是一例。为什么五四以后并没有引发到对传统及西洋的寻根的认识呢,我想一方面是传统惰性的阻力仍大,最重要的还是开放性思想的受挫。五四反对了传统的定型思想以后,作家们受着当时政治潮流的影响,再落入新的定型思想的枷锁中,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派作家,每每被困在源出西方的马列主义的模子中;当时的胡风,因为紧握着五四给他的一点开放精神的种子,欲挣脱思想的枷锁,而终于被围剿整肃到无法生存。
但我们并不是说从五四到四十年代间没有冷静、客观、深思熟虑,对中西文化作寻根的认识的批评家,有,但不多。朱自清的《新诗杂谈》及其对传统文学(如《诗经》)的探讨,朱光潜中西美学的比较,李广田的《诗的艺术》,钱钟书的《谈艺录》及其他美学论文,刘西渭(###吾)的论诗与小说的文字……在过度情绪化的批评激流中它们是难得的论著。但当时大多数的批评,如果不落入某种定型思想的枷锁,便是用了辩证方法而徒具辩证的程序的文字,它们甚少触及文学作品中艺术结构的核心。
一个完美的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要对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对诗人由感悟到表达之间所牵涉的许多美学上的问题有明澈的识见和掌握,不管你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辩证的程序。所谓明澈的识见当不指死学而来的“抛书包”,而是活学而得的对美感视境的诸貌、风格的蜕变之历史识见。死学而来的“抛书包”虽号称读遍四书五经,甚至凡诗皆可顺口背出,而结果是大堆头的未经思考的猛录前人所言,尽“屡积详举、言繁意简(而瘦而假)”之能事,对一首诗的机心,对一篇小说的结构与风格毫无认识;活学而得识见的批评家,可能也曾读遍四书五经以后的重要文献,但不同的是,学养不露形迹,绝不繁复乱录,化学问为识见是也。批评家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有“洞彻之悟”的,对作品中的艺术性(一首诗的机心)有了明澈的识见,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点、悟”的方式(有禅机的批评家用了这种方法而不见碍),还是用逻辑化的辩证的程序(他自然会避免不必要的修辞的枝丫),而都可以做到“言简而意繁”的有效的批评。
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1)
这里,我打算用近人周策纵先生的一首旧诗作起点,来提出文言文用字、用词和语法所构成的传意特色,然后进而观察一般中国古典诗里(作者)传意和(读者)应有的解读、诠释的活动(以下简称为“传释活动”)。
这篇文章,一面是我的“语法与表现”一文原题“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1973)见《饮之太和》(台北,1980)第25—84页;另题“语法与表现”见《比较诗学》(台北,1983)第27—86页。的延伸,一面是打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