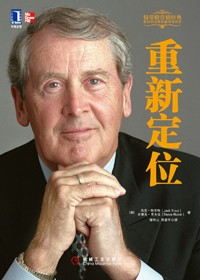迈克尔.杰克逊自传太空步-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备,你知道,就这么走上去——唱歌,跳舞,再开点小玩笑。
我们在不止一个有脱衣舞表演的夜总会里演唱过。在芝加哥一家这样的夜总会里演出时,我总是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一名叫玛丽·罗斯的女演员表演。那时我可能有九岁或十岁了吧。这个姑娘会脱掉她的衣服和紧身短衬裤,然后把它们抛向观众。男人们捡起那些衣服,一边使劲儿嗅着上面的味儿,一边狂呼乱叫。我和哥哥们便眼看着这一切,默默接受下来,爸爸并不在乎。这种把戏我们见得太多了。在一个地方,那些人在演员更衣室的墙上挖了个小洞,甚至在女厕所墙上也挖了一个。透过这些洞你可以偷看里面的动静,而我则看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那个地方的家伙们都疯了,一天到晚干一些在女更衣室墙上钻孔这类的勾当。当然,我也承认,那会儿我和哥哥们也曾为抢着往里看争执不下。“躲开,该我了!”我们一边喊,一边使劲推开别人,好给自己腾出一席之地。
以后,我们在纽约的阿波罗剧院演出时,我看见的情景差点把我吓死,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我见过不少脱衣女郎,可那天晚上,一个描着艳丽的睫毛,梳着长发的女郎出场了。她的表演令人叫绝;但大出人们所料,在快结束的时候,她扯下了她的假发,从她的乳罩里掏出两个大桔子,重现出那巧妙化妆之下一副棱角分明的男人面孔。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只是一个孩子,没法相信眼前这一切竟是事实;但我向外看了看观众,发现他们都喜欢这些东西,发了疯似的鼓掌、狂叫。而我,一个小小孩儿,就站在台角,看着这狂热的场面。
我被吓坏了。
就这样,在孩提时代,我颇受过一些这类教育,受的真够多的了。也许这使我在长大成人之后,能把精力放在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
我们在芝加哥的夜总会里成功的表演之后不久,一天父亲带回家一盘磁带,里面的歌我从来没听到过。我们习惯于演唱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因此当父亲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起磁带里的那些歌时,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里面无非是一个唱得不怎么样的家伙和伴奏的几声吉他和和弦而已。父亲告诉我们,录音里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歌手,而是一位歌曲作者,他在加里拥有一座录音棚。这位名叫基思的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来练习他的那些歌,看看能不能从中挑选一些给我们灌一张唱片。自然,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的确想灌一张唱片,随便什么唱片。
我们把重点放在声音上,而不像以往那样,从舞蹈这一角度开始排练一首歌。唱一首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新歌并不怎么有趣,但我们已经很老练了,能藏起我们失望的情绪,并尽力唱好它。等我们作好准备,觉得自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了,爸爸把他们录了下来,当然,开头总要出几次错,爸爸也免不了说几句给我们打气的话。我们都想猜测出基思先生是否喜欢我们为他录的东西,这样过了一两天,爸爸突然又带来了更多的歌曲让我们学,并说我们将在第一次录音时演唱这些歌。
基思先生和父亲一样,也是个酷爱音乐的钢铁工人,只是他更多的从事唱片商业活动。他的唱片公司和录音室都叫做“钢城”。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基思先生当时的兴奋并不亚于我们。他的录音棚在市中心,因此,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就出发了,那时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竞赛者”还没开始。基思先生在门口迎接我们并打开了录音棚,他带我们参观了一个摆满各种设备的小玻璃间,并把每种设备的用途都讲给我们听。看来我们用不着太多的录音设备至少在这儿用不着。我把一个大金属耳机戴在脑袋上——在演唱中他总是掉到我的脖子上——好让大家知道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
就在我们兄弟几个琢磨插头该插在什么地方,人该站在哪儿的时候,一些伴唱的演员和一个管乐小组进来了。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我们之后录音的,当我们得知他们是来配合我们的时候,都又惊又喜。我们朝爸爸看去,他却根本不动声色。显然他已经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什么事也别想让父亲吃惊。他告诉我们,在录音间里的时候,一切都要听从基思先生的指挥,只要我们照他说的做,录音效果自然就会使人满意。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录完了基思先生的第一首歌曲。一部分伴唱歌手和管乐手也是头一回录音,都觉得挺吃力;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受过第一流的指导,所以不像我们那样习惯于一遍又一遍地演唱或演奏。这时我们才会体会到,父亲为把我们培养成优秀的职业歌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以后接连几个星期六,我们都在这里度过,把一周中练好的歌曲灌成唱片,每次回家时再带走一盘基思先生的新磁带。有一个星期六,父亲甚至带着他的吉他来和我们一起演唱,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录音。在唱片开始发行之后,基思先生给了我们一些,让我们在每首歌曲之间或演出之后把他们卖给观众。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名家的大作,但是人人都需要有一个开端,而在那个时候,能出版一张写着你们小组名字的唱片是一件大事。我们实在幸运极了。
这张名叫《小大人》(Big Boy)的唱片是我们在“钢城”公司录制的第一张单曲,歌中充满了相当低沉的调子。《小大人》是一首动人的歌曲。当然,要是你想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你就得想象一个瘦小的九岁孩子在唱着这只歌。歌词中说,“我不想再听童话故事了”,但事实上我离能够理解绝大部分歌词的年龄还差得远。我只是在唱他们让我唱的东西。
这首带着迷人的低沉调子的歌在加里的电台播放之后,我们在邻居中间立刻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谁也不相信我们有了自己的唱片,就连我们自己也费了好大劲儿才相信了这一点。
在“钢城”公司录完了第一张唱片后,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芝加哥各种大型能手比赛上。通常别的演员在见到我时都要仔细打量我一番,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之后出场的,大概因为我的个头儿太小了吧。一次,杰基突然失去控制大笑起来,就好像谁把世界上最逗的笑话讲给他听了似的。比赛马上开始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敢说,爸爸当时一定担心极了,唯恐他在台上演砸了,便走过去想提醒他两句。谁知杰基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他就和杰基一起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爸爸自豪的说,杰基偶尔听到一群歌星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说道:“今儿晚上可不能让‘杰克逊五兄弟’里的那个侏儒抢了我们的好戏。”
刚开始我觉得挺不好受,因为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我觉得他们这么说真是卑鄙。我不能不接受我是最矮的这个事实,可不一会儿,我的其他几位哥哥也都笑得不行了。爸爸解释说他们不是在笑我,并说我应该以此为荣才是。那帮人不过是在胡说八道,因为他们竟认为我是个装成小孩模样的大人,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小芒奇一样。爸爸还说,要是我能使那些油头滑脑的家伙和加里那些给我们捣乱的邻家小孩用同一种腔调议论我们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让芝加哥跟着我们跑了。
我们还得跑自己的事情。在芝加哥几家挺不错的夜总会演出之后,爸爸在市里皇家剧院登了记,让我们参加那里举办的晚间业余歌手大赛。B。B。金在皇家剧院现场录制他出名的专辑时,爸爸曾特地跑去看过。当早年他送给蒂托那把发亮的吉他时,我们还曾经跟蒂托开玩笑,想一些女孩的名字来命名他那把吉他,就像B。B。金管他的吉他叫“露西尔”那样。
连续三个星期,我们都在这个比赛中获胜。那些每场必到的观众总是在猜测,这周我们又拿出什么新歌。另外一些歌手抱怨说,我们一次次来参赛实在是太贪心了,可他们追求的东西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比赛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如果你在晚间业余歌手大赛中连续三次获胜,你就将被邀请举办一场收费演出。这样面对的将是几千观众,而不只是酒吧里那几十个人。而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格拉迪丝·奈特的节目揭开了那场演出的帏幕,“杰出人物”乐队还搬出了尚未公开演出的新歌《我从葡萄藤中听说了这回事》(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助兴。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
芝加哥之行结束,我们清楚的感觉到,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业余歌手大赛需要我们去赢得桂冠,就是纽约阿波罗剧院举办的那场。许多芝加哥人都觉得,在阿波罗取胜除了是一种凭运气得来的快感之外,没什么了不起。可爸爸比他们看得远。他知道,纽约和芝加哥一样,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选手,而且纽约的录音人员和职业音乐家比芝加哥更多。如果我们能在纽约成功,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这就是我们必须在阿波罗获胜的意义所在。
芝加哥给纽约寄去了关于我们情况的报告。我们的名声是如此之大,甚至都没有参加任何一场预赛,阿波罗剧院就直接让我们进入了最后决赛。这个时候,格拉迪斯·奈特已经跟我们谈到了去摩城公司的事宜,爸爸的朋友、“温哥华”演唱小组的成员博比·泰勒也和爸爸谈起过。爸爸对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让摩城公司试听我们的演唱,但这是将来的事儿。我们到达坐落在第一百二十五大街上的阿波罗剧院时,时间还早,足够参观一下这座建筑的。在经理陪同下,我们穿过剧院的大厅,观看曾在那儿演唱过的所有明星的照片,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当最后经理把我们带到化妆室门前时,我已经找到了所有我喜欢的歌星的照片了。
我哥哥们花钱去看为别的歌手举办的所谓的“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仔细的观察所有那些明星,尽力去学习看到的一切。我盯着他们的脚步、他们挥舞手臂的姿势,以及他们手握话筒的方法,努力搞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在台角仔细研究了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之后,我弄清楚了他的每一个步点,每一声低吼和每一次旋转。不能不说,他的演出就是为了把你拖个筋疲力尽,让你把所有的情感都发泄出来。他的风度,他从每个毛孔中迸发出的热情都是无与伦比的。你简直就能感觉到他脸上的每一滴汗珠,也能感觉到他正在经受什么。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这样表演。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观察我喜爱的歌星,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詹姆斯·布朗、杰基·威尔逊、萨姆和戴夫、欧杰伊兄弟——他们都善于调动观众。我从杰基·威尔逊那儿学到的大概比从别人、别的地方学到的都要多。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受到的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常站在台边的幕布后面,看着每一个演完节目下台的人,他们个个全身湿透。我带着敬畏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从面前走过去。他们都穿着漂亮的漆皮鞋,那会儿我的全部梦想就是得到一双那样的漆皮鞋。记得当我听说他们不做小孩尺寸的那种鞋时,甭提有多伤心了;我从一家商店跑到另一家商店寻找漆皮鞋,得到的答复却常常是:“我们不做那么小的。”我很难过,因为我希望我的鞋也像那些演出用鞋一样,擦的闪光,灯光一照就反射出红色和橙色的光来。哦,我是多么想要一双杰基·威尔逊的那种漆皮鞋啊。
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呆在后台。哥哥们都在楼上吃东西或聊天儿,而我则低低的蹲在楼下舞台边上,用手揪着蒙满尘土、有一股怪味儿的幕布,注视着台上的演出。我是说,我的确注意了每一个脚步,每一次移位,每一下扭动,每一回转身,每一个摇摆,每一种情绪,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那就是我受的教育和我的消遣。我一有空就总在那儿,爸爸、哥哥和其他的演员都知道哪儿能找到我。他们总是以此开我的玩笑,而我已经被看到的或追忆起来的表演场面深深吸引住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还记得所有这些剧院的名字:皇家剧院、住宅区剧院、阿波罗剧院——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从那些地方产生的才华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看大师们工作;你不可能把我站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交给任何一个人。有一些音乐家,如斯普林斯廷和U2,也许可以觉得自己是从大街上得到了启迪,而我则是一个注重气质和心灵的演员。我得到的启示来自舞台。
阿波罗剧院的墙上挂着杰基·威尔逊的照片。摄影师捕捉了他一条腿抬起,身子扭转,刚好抓住麦克风前后摇晃那一瞬。他大概在唱那首悲哀

![恐惧状态 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