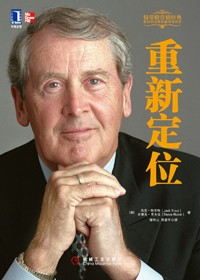迈克尔.杰克逊自传太空步-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虽然已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我们杰克逊家的孩子却从来没有失去过这种感觉。凯瑟琳和蔼、热情、认真;我无法设想,要是没有这样的母爱,我将如何长大成人。
我知道孩子们都有个特点,要是他们从父母那儿得不到他们需要的爱,他们就会从别人那儿寻找,并且依恋那个人,比如爷爷奶奶啦,或者任何一个人。有母亲在身边,我们从来就不必寻找什么别人。她教给我的东西是无价的。善心、爱和替他人着想是她恪守的信念,她教育我们不伤害别人、从不祈求怜悯和决不贪小便宜。这些恶习在我们家里被视为邪恶。她总是希望我们奉献,从不愿意我们去索取或乞讨。这就是她的为人。
我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我母亲的性格。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住在加里市——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浑身流血不止的人挨家挨户的敲门。附近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血迹。邻居们谁也不敢让他进去。最后,他到了我家门口,在门上连拍带敲。我妈妈马上就让他进来了。你看,一般人谁也不敢这么做,可我妈妈就敢。我记得我醒来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大滩血。但愿我们能像妈妈那样做人。
我关于爸爸的最早记忆,就是他从钢铁厂回家时,总要带一大口袋浇了糖汁的炸面包圈给我们吃。我们兄弟能一下把他们吃个精光,然后,爸爸打个响指,那个口袋一下子就不见了。他经常带我们去公园坐旋转木马,但那时我年纪太小,早记不清坐木马时的感觉了。父亲对我来说总像个谜,这点他自己也知道。我几乎从没有真正和他亲近过,这是不多的几件使我觉得后悔的事情之一。那些年中,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外壳,每逢他和我们谈完家里的正经事儿时,就很难和我们再呆在一起。有时家里人都聚在一起,他却离开了房间。哪怕到了今天,他仍然不愿意正面接触父与子之间的问题,因为他太局促了;每当我看到他这样,自己也跟着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的确,父亲总是保护着我们,这是他为我们做的一件大事。他总是用最好的方式照顾我们的利益,保证我们不受骗上当。也许,他会不时犯些小错误,但他一直认为,他是为了这个家,才做这一切努力的。在父亲帮助我们完成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是出色的,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在我们和各种公司以及商业界人士打交道的时候。我要说,只有一小部分艺术家是很走运的,而我们兄弟几个属于这个范围;很少有人在少年时期步入这一行便拥有我们这样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基金、不动产,还有各种别的投资。是父亲为我们准备了所有这些。他兼顾着我们的和他自己的利益。到现在我还很感激他,因为他没有像许多童星的家长们那样,试图把我们的收入据为己有。想想看,一个人怎么能偷自己孩子的钱呢?我爸爸从来不做这种事。可是我还是不了解他,这不能不让一个渴望理解亲生父亲的孩子感到难过。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人,也许永远会这样。
虽然《圣经》上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我却是从父亲那儿知道这个道理的,绝非受圣人的指点。有几次我和父亲同行时,他说: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天赋,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又没有计划,也终究会一事无成。他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好几遍,然而意思却一样清楚。
乔·杰克逊和我母亲一样,一向喜爱音乐和唱歌,但他也知道,在我们家那条街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于“猎鹰”乐队的情况,我因为当时还小,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记得,每逢周末,他们就到我家来排练。是音乐把他们从钢铁厂的劳动——我爸爸在那儿开吊车——带到别的世界中。“猎鹰”在城镇各处演奏,足迹遍及北印第安纳和芝加哥的俱乐部和学院。在我家排练时,爸爸就从柜子里拿出他那把吉他,并把它接在地下室的音频放大器上。大家都就座,音乐于是便响了起来。它喜欢弹奏布鲁斯摇滚乐,那把吉他便是他的骄傲和快乐之源。放吉他的柜子几乎被看成是一个圣地。不用说,我们小孩子是绝对不许接近那里的。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去圣殿,但他和妈妈都知道,音乐能使我们全家抱成一团,也使我哥哥他们那么大的孩子不被附近的犯罪团伙拉下水。“猎鹰”小组来的时候,家里三个最大的孩子都被爸爸以各种理由留在旁边;爸爸尽力让他们明白,允许他们听排练是对他们的特殊照顾,其实是他自己非常愿意让他们留在身边。
蒂托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正在进行的一切。它一直是带着萨克斯管上学的,但现在他却说他的手已经足够大,能按到吉他上所有的和弦,并能在把上滑动,像爸爸那样奏出不断重复的即兴曲了。这说明他总有一天要赶上爸爸的;他和爸爸长得那么相象,我们都希望有一天他能把爸爸的本事都学到手。在他渐渐长大的过程中,这种相象变得有些令人不安起来。也许爸爸看出了蒂托热切的心情,于是他对我们兄弟几个下了一道禁令:在他出去的时候,谁也不能碰那把吉他一手指头。没什么好说的。
因此,杰基、蒂托和杰梅恩在瞧仔细妈妈去了厨房后,才敢从柜子中把那把吉他“借”出来。他们在搬琴时小心翼翼,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到了我们自己的房里,他们便打开收音机或手提式便唱机,跟着一起弹奏。蒂托会把吉他举起来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往床上一仰,然后把它竖直。他和杰基、杰梅恩轮流弹着,三个人都想显示一下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本事,还试着怎样才能弹奏出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绿洋葱》(Green Onions)中的那一段。
那会儿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偷偷溜进去看他们弹,如果我答应不告密的话。一天,妈妈终于抓住了他们,我们几个心里都忐忑不安。她训斥了我们一顿,但又说,假如我们一直小心谨慎的话她就不告诉爸爸。她知道,没有吉他,我们就可能去学坏,也可能挨打,所以她从不会拿走能让孩子们呆在她身边的任何一样东西。
当然,出事只是个迟早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一根弦断了。哥哥们都吓得要死。在爸爸回来之前已经来不及把琴修好了,况且,我们谁也不知道该怎样修。哥哥们想不出好主意,便把吉他放回柜子里,希望爸爸会以为弦是自己断的。不用说,爸爸没买他们的账,他大发雷霆。姐姐示意我别吱声,也别露面。但我听到蒂托大哭起来,自然就跑去看个究竟。蒂托在他的床上哭个不停,爸爸走过去示意他起来。蒂托给吓坏了,可父亲就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他那把宝贝吉他。他严厉的看了蒂托一眼,好像要把他的五脏六腑看穿似的,然后说道:“让我看看你会弹些什么。”
哥哥恢复了镇静,开始弹他自学的几段快速音乐。当父亲看到蒂托弹得是那么出色之后,他明白了,他的儿子显然练习了好一阵子了,而且,蒂托和其他的孩子并没把他的宝贝吉他当玩具玩儿,已经发生的只不过是个小事故。就在这时,妈妈走了进来,对我们的音乐才能表示了热烈的赞赏。她告诉爸爸,我们是有天赋的,他应该听听我们的演奏。她一个劲儿的劝他,由于有这一天,他开始听我们的弹奏了,并且还挺喜欢。这样,蒂托、杰基和杰梅恩三个人就热切地练习起来。几年过去,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妈妈告诉爸爸,说我歌儿唱得还不错,又会打鼓,于是,我就成了小组的一名成员。
大概就在那时,爸爸决定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家里发生的这件事了。渐渐的,他和“猎鹰”小组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而更多的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块儿练习弹奏的时候他指点我们,教给我们弹吉他的技巧。我和马龙年纪尚小,还不能弹,但我们观察爸爸如何训练哥哥们,边看边学。爸爸不在时不许动吉他的禁令依然有效,但一有机会,哥哥们就抱着那琴弹,爱不释手。杰克逊大街上我们那座房子里终日洋溢着音乐声。瑞比和杰基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花钱让他们去上音乐课,因此他俩的基础很好;剩下的孩子们就在加里的学校里上音乐课,并参加学校的乐队,但再多的练习也消耗不完我们那旺盛的精力。
“猎鹰”小组仍在演出挣钱,尽管他们的演出越来越少了,但那笔额外的收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笔钱能使这个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不至于断顿儿,但要想买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还是不够。妈妈在希尔斯百货公司干些零活儿,爸爸仍在钢铁厂工作,虽然没人挨饿,但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总觉得那种日子真是没有指望。
一天爸爸很晚才回家妈妈开始着慌了。他刚一到家她就准备朝他唠叨几句。这种事我们时不时能看到一回这次我们想看看他是否能像责怪别人那样听别人的责怪。可当他把脑袋伸进门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脸上挂着一种调皮的神情还往背后藏着什么东西。等他从背后拿出一把闪闪发光的红吉他时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把吉他只比柜子里那把稍微小一点儿;我们都希望,爸爸这样做是为了把那把旧吉他给我们,可他说这把新的是给蒂托的。我们羡慕极了,一起围过去,这时爸爸对蒂托说,如果其他人想练习的话,你就得把吉他给他练。我们不准备把它拿到学校去炫耀。这是件分量很重的礼物,而那一天对我们杰克逊一家来说,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妈妈为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她也了解她的丈夫;她比我们更了解他的远大抱负和他为我们安排的计划。夜晚,我们都进入了梦乡后,他向她诉说他的梦想,这梦想并不仅仅停留在一把吉他上。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和器材,而不仅仅是礼物打交道了。杰梅恩得到了一只低音贝司和一个音频放大器;给杰基的是一副沙锤。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开始变得像一家音乐商店。有时候我听到爸爸和妈妈就增加的花销争论不休,因为买这些乐器和附件,我们已经没钱买每个星期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了。可不管怎么说,爸爸总是有说服力的,看来他抓住了谈话的窍门。
我们甚至在房间里装上了麦克风,在那个时候,他们可真算得上奢侈品了;尤其对一个总是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在家里装上那些话筒,目的绝不在于赶上琼斯一家或是任何一位在晚间业余歌手比赛中露面的歌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作好准备。我曾在“能手大赛”上看到过一些人,他们在家多半儿唱得挺不赖,可一站在麦克风前就连嘴都张不开了。还有一些人,一开始唱就大喊大叫,好像想要证明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话筒那玩意儿。他们不如我们有优势——那种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获得的优势。我想这大概让许多人嫉妒,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对使用麦克风的擅长让我们占了便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只消看看我们为此作出的牺牲——业余时间里的排练,学业的荒疏和朋友之间交往的减少,他们还有什么权利嫉妒呢?我们唱得越来越出色,但我们工作的强度决不亚于一个年纪比我们大一倍的人。
一次,我正看哥哥们——包括敲邦戈鼓的马龙在内——练习,爸爸带着两个小家伙,一个叫约翰尼·杰克逊,另一个叫兰迪·兰西弗,他们负责打击乐器和管风琴的演奏。摩城公司后来称他们是我们的表兄弟,其实这不过是那些负责公共关系的人的宣传手法,他们想让人们觉得我们是一大家子。这下我们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乐队!我观察每个人的演奏,试着把能学会的都学会,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哥哥们排练时,或是在慈善募捐集会和商业中心演唱时,我就将一切统统吸收进去。我观看杰梅恩的时候最为入迷,因为那时他是歌手;再说他又比我大得多——而马龙的年龄和我则太接近了。是杰梅恩送我去幼儿园,他穿不了的衣服也总是给我接着穿,他做了什么后,我便试着去模仿他。要是我学得挺像,爸爸和哥哥们就会笑起来,但我一张口唱歌,他们就开始静静的倾听,那时我用童声模仿着别人的声音唱;我是那么小,好多歌词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唱得越多,知道的也便越多。在跳舞方面,我则总是无师自通懂得该怎样跳,因为杰梅恩要举着他那支大低音贝司,所以我注意的是马龙的脚步,再说因为马龙只比我大一岁,我也只能跟得上他的步子。不久我就在家里包揽了大部分唱歌的活儿,并准备随哥哥们在公开场合演出了,通过练习,我们逐渐对每个小组成员的特长和短处都了如指掌,分工也便自然而然的形成

![恐惧状态 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