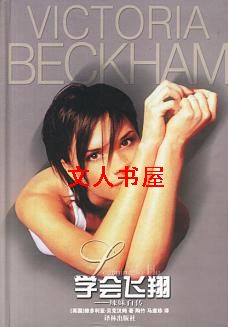浩然口述自传-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能!我不被任何热闹场景所动,我的心被引人入胜的书抓住了。
一会儿,一个表弟来喊我:金广,大过年的干啥在屋里猫着!
我头也不抬地回答他,别捣乱,我看书哪。
过一会儿,一个表兄来找我说,走,咱们踢球玩儿。
我掰开他那只抓着我的手,挺不高兴地说,不去!不去!
村里的小伙伴,对我都特别好。在这个小山村里,唯有我出生在有电灯、有火车道的矿区,见过世面,知道许多他们所不知道的新鲜事儿。我念过三年半书,识文断字,会自己写对联。我从小热情,没骂过街,没打过人,跟小朋友翻脸瞪眼的事儿都没几次。因为这些,年纪相仿的人都愿意跟我好,喜欢跟我一块儿玩儿。少年儿童们玩耍的场面,没有我加入,会明显地减色。他们屡次派代表找我,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执意不去,谁都不好硬强着,可又不死心,一会儿这个返回来,一会儿那个返回来,闹得我一天没去玩儿,也没能安下心来好好地看看书。等到初二,我在无意之中改变了态度,收到特别满意的效果。“改变”是这样开始的,一群小伙伴搭着帮,又来纠缠我,央告,说好听的,求我去跟他们玩儿。我就是硬着心肠不答应,非得留在家里看书不可。
他们中间一个挺纳闷地问,啥书把你给迷成这样呀?
我告诉他,是讲梁山好汉故事的……给你们念一段,你就信啦。都别吵吵,老实听着啊!
于是,我盘腿坐在炕上,手捧着书,从我刚才看到的字行处起头,磕磕绊绊地往下念。
挨着炕沿站立的一排小伙伴,开始都挺好奇地听,听了一阵之后,心气就不一样了。有的悄悄地坐在椅子上,有的不知不觉地趴在炕沿上,直着眼睛往下听;有的东张西望,打哈欠,总想说话儿。那些听得入神的伙伴就冲说话的伙伴嚷,别打岔,听着!爱听的留下没动,不爱听的无精打采地走了。等一会儿他们又转回来拉我,那些听入迷的人就推他们,把他们推到屋门外边。
从这天起,到初五,我几乎总是从早给他们念到晚。我得到了满足,他们也觉得有趣,觉得比到街上踢球好玩儿得多。
晚上看书困难,灯油太贵,有多半瓶子油,起码得用半年,要是点灯看书,两夜就会耗干。我姐姐不让,我也舍不得。这可怎么办呢?讲故事和听故事,可以摸黑,看书没亮绝不行。早早地躺在炕上睡不着,怪难受的。姐姐不睡,去串门。我也出去,我跟小伙伴到西场看斗牌的。
我管这家的主人叫三舅。他的屋子很大,一盏有罩子的煤油灯挂在从房柁垂下来的绳子上,给炕上围坐一圈的赌钱人照着亮,也给旁边“瞧眼儿”的人照着亮。
我心里忽然一动,这儿有光可借,我到这儿看书多美!
这样想着,我悄悄地转回家,摸黑进了屋,摸黑找到书,再到西场三舅家,挤进“瞧眼儿”的人缝里,趴伏在炕沿上,接着看我心爱的书。开始,那些斗牌人吵声叫声笑声特别刺耳朵,加上灯光摇晃,使我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到书页的字行上。等到看着看着入了神,随着豹子头林冲去发配,走在荒凉可怖的漫漫小路上,我仿佛也跟随他艰难地举起脚步,周围的一切人和声响都被忘掉和消失。直到有人轻轻地拍打我的肩头,我才被惊醒似地蒙怔起来。三舅笑眯眯地说,这么看书,还不把眼睛看坏!快回家睡觉去吧。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6)
我抬头一看,发觉满屋子人都走净了,只有三妗子跪在炕里铺褥子。当我走出那烟气腾腾的屋子,到了冷嗖嗖街上的时候,雄鸡已经扯开嗓子打鸣儿了。
这个年过得很高兴,凡是使人高兴的时间都逝去的特别快速。我只把一部《水浒传》看完少一半儿,就到了“雁叫河开”的九九以后。庄户人家,得准备春耕种地了。
我和姐姐倒换着抡了两个下午铁锨,把一个猪圈的粪肥起出来。而后,我俩又一筐一筐地把粪抬到大门外,加在原来积下的粪堆上。姐姐用镐头和小锄捣粪,我给老灰毛驴备上鞍子,搭上抽板的驮篓,往地里运送。
我家有两块地,村西有我妈妈坟堆的那块地近,村北那块是一小条一小条的梯田,要爬一道小山梁,远得多。先远后近,姐姐让我先往村北的山坡子地里送。
从村里到地里,有很长很沉闷的路程。赶驮子的人,都哼着小曲、打口哨,或是扯开嗓门唱驴皮影或河北梆子、大口落子,用这些来消除单调和孤寂。我特别爱听这种声音。每逢我跟在别人后边听,或是迎面传来这种音调,都让我如醉如迷,都把我带到一个神奇的境界,都使我感到庄稼汉是那么纯洁、那么洒脱、那么自由自在、那么可敬可爱——他们的人和声音,都跟美妙的大自然融化成一体,难解难分,让人看得听得心醉神往……
山梁那边的三郎寨,只有很少的土地,没人跟我结伴同行,也难遇上来往的人畜。我跟一个哑巴牲口孤零零地走,从不会打口哨,也不好意思哼唱,就一边踏着石子小路,一边海阔天空地幻想,让自己那幼稚的灵魂,在幻觉的境界里任意地驰骋。这是我少年时期最好的享受。只是这一回我放下了幻想,我得利用这长长的小路,看那没有看完的书。
灰毛驴驮着粪篓,在前边甩动着四只挂了铁掌的蹄子,出了村东口,往北拐。我跟在它的后边,等上了一个名叫“北牛子”的小坡,觉得路顺了,便打开书本,边走边看。路是直的,又是熟的,即使到董家沟以后要偏西北了,越过一道沙石河往鹰爪子山爬山梁的时候,我的两只看字的眼睛,只要稍带着瞄瞄脚下的石子路,就蛮可以顺利前进。
我跟随着灰毛驴,走哇,看哪。“人”在爬北山,“神儿”却登上了梁山,走进了聚义厅。遇到精彩的情节,我一会儿提心吊胆,一会儿唉声叹息,一会儿又忍不住嘿嘿地笑出声来。
喂,你这是上哪儿呀?一声喊叫,从头顶上传来,把我从水泊梁山拉了回来。定睛一看,左边是陡立的山崖,右边是阴森的沟谷。天哪,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了?
山崖上打柴的人,是我们庄上的,我得称呼他表兄。他告诉我这地方已经过了大郎寨,超过我送粪的地界三四里路之远了!
我慌忙往前跑,想把驴截住,好往回头路上转。可惜,我跑出老远,都没瞄着灰毛驴的影子。我给吓傻了眼,折到山崖下边。
对小门小户的庄稼人来说,一头驴就是半个家当。如果丢失了毛驴,我靠什么种地干活呢?这就等于败了家呀!
我慌慌张张沿着走来的路往回返,汗水顺着两腮往下流。我下了一道大坡,越过两条小沟,又登上一座高岗,绝望地朝下坎一看,那颗悬挂起来的心,才落下来。灰毛驴比我规矩,它根本没有往前走,到了三郎寨我家的地边上,它就自动地拐了进去,等候卸下驮着的粪。是我走过了站,让灰毛驴在地里等了这么久。
它发现我赶到跟前,悲哀而又奇怪地看看我。四条蹄腿因为过久地站立,已经没了力气,颤抖地抖动着,挣扎地摇晃着,几乎快要给压得趴下。
我扑过去,急忙放开划子、放开抽板,在粪块卸落的“哗啦”声中,我害臊地求饶地抱住了灰毛驴那毛扎扎的脖子。
4
跟书打上交道以后,曾经发生过许多上边说的那种不入时、不顺眼、不合常规的事儿,使我在村子里,甚至左右村子都出了名,那就是:一个没人管教、不务正业、早晚得丢人现眼的书迷!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7)
念过“四书”、“五经”的吴老师,是我们王吉素这个小村至高无尚的圣贤先生。他正派、古板、严厉、尖刻。我在他家南院西厢房里的八仙桌子旁边,念过半年《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念一半就停止了。我怎么也难想起他都教过我什么。但是,有一次,老先生赌钱输了回来,发现我没有“念经”而偷偷地雕刻皮影人,就用细细的藤子棍儿抽打我脊梁和脑袋。那种像刀子割一样的疼劲儿,我倒记得特别清楚,至今不忘!
有一次,几位头发花白和有胡子茬的庄稼汉,在村东口谦卑地围他而立,洗耳恭听他高谈阔论。有一句评价我的话,正巧让打草归来的我从短墙的那一边经过时听到了。
吴老师声音洪亮地说,我早就看出来,金广那小子,是全庄孩子里边最没出息的一个,不会长成个好庄稼人,等着丢脸吧!
这句话,仿佛在我头顶上爆炸一枚炮弹!我木雕泥塑般地在原地站立好久,才迈得动脚步。
要知道,吴老师是一位最有威望的人,他的话就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他那魁梧结实的二儿子,只因有点痔疮毛病,他就对二儿子说“不宜成亲”,那位孝子就得按照“真理”行事,咬着牙熬光棍儿,熬到老死!
他的话,比打比骂还要严重地伤害我的自尊心,好长时间我都有些抬不起头来,认为自己确实干下了“蠢事”。但我觉得我能够让自己变得有出息。我反复思量以后,就托人给在开滦赵各庄下煤窑的二舅带个口信儿,求他设法把我送进唐山瓷器厂去给画匠当学徒。——幼年的我,对绘画特别感兴趣,认为当画匠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我如若能干上这一行,就表明我最有出息!当这个美梦必然地破灭之后,我头一次产生了灰心丧气的情绪。
我常躺在炕上,或是坐在树下苦思冥想,勾画自己“没出息”的下场和情景。没有人管教我,我也没办法管教我自己,我肯定要变成个“最没出息的”,肯定不会长成一个“好庄稼人”。那么,“没出息的”、“不好的庄稼人”是啥样的呢?是“败家子儿”?是“落道帮子”?是让狗追着咬的乞丐?是让人嘲笑和远避的“大烟鬼”?是让人咒骂和厌恶的“花柳病患者”?是被人抓住了吊在树上毒打的“贼”?不不,我宁肯去找个人缘好的财主家当“小半活”,或是到大城市里去,先在街头卖烟卷儿,等长大就拉洋车,凭卖力气活着,起码不算丢人现眼吧?
五花八门的凄惨前程,都在等待着我这个无所依靠又“不安分”的孤儿。命里注定,我绝不会有个好前程!
……
谁能料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迅速推进、改变了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我这个农家孤儿的生活道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爱上了写作,并暗暗地把成为革命作家作为终生奋斗目标。这理想的小苗,是革命的时势促成的结果,然而,恰恰是民间口头文学、地方戏曲和那些借来的和买来的曾使我大为着迷过的各种杂乱书籍,才把我熏陶、培育成一颗文学的种子!
我在理想的道路上,朝着目标往前迈步。我当了报刊的记者、编辑。在吴老师给我下结论的第十个年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第十二个年头以后,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我把一本新书寄给了正在故乡念书的表妹。
农家的一个看书迷,成了写书迷,终于写出了书、出版了书,这不能算一件小事,家乡的人常常议论我。
多年以后,有一回,我陪一位朋友到王吉素村去,正巧在村东口遇见吴老师跟人聊天。
他显得老了,眉毛胡子都变黄,脸色却很红润。据村里人说,这位老人家是很会保养身体的。
我向朋友介绍他,这位是我小时候的老师。
吴老师听我这么一介绍,两只老花的眼睛立刻放出光芒。他挺得意地用手指头捋着下巴颏上的黄胡子,慢条斯理地说道,我这一生,就教了金广这么一个最有出息的学生。
。 想看书来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8)
老人家重新评价了我。我自己也重新认识了童年做过的那类“蠢事”。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
1
在王吉素,庄稼人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让年少的我很不甘心。父母都不在了,我和姐姐商量,到唐山的陶瓷厂当画匠去。就这样,一个看似灿烂的前程摆到了面前。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朝正东方向走去。
走了一天遇上一背着粪箕子拾粪的老头儿,我跟他打听,老爷爷,这儿离林南仓还有多远哪?老人家朝我瞥一眼,说,不远啦,差不多三十里吧……
我吓了一跳。一位邻居曾经嘱咐我,当天晚上要到林南仓投店住下。可走了这么久,还有三十里,能赶到吗?
听了这个回答,我开始感到浑身十分累乏,脚掌子非常疼痛,两条腿如同坠绑上两个石头“嘟噜子”,越走越沉重,每抬动一下都困难。于是不由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