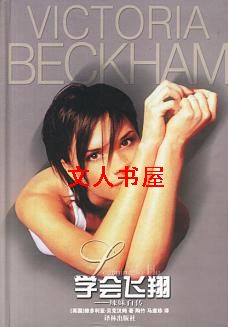浩然口述自传-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欺欺人地说成是“文艺春天的来临”,替“四人帮”粉饰了悲惨的现实,麻痹了广大群众。这是我的又一严重错误。特别是北京市的业余文学青年,他们信赖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正确的帮助,我在主观上也想热心地给他们一些帮助,可是中了“四人帮”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当作糖灌输给他们。他们的健康成长受到妨碍,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7)
我在“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旋风里迷失了方向,承认了十七年文艺界是“黑”的,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就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十七年是“黑线专政”,那么我这个十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又如何解释呢?我觉得自己不是“黑线人物”,我当时是不受重视的、是被“黑线”压制的。我把自己初学写作时,一些作品没有被发表,牵强地说成是被“黑线”压制;把没让我参加文代会说成是不受“黑线”重视;甚至把一些同志出于爱护而对我的批评和指教,也曲解为“黑线压制”,这是极其荒唐的。我向这些被我伤害了的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因为接受了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的谬论,我就不能不承认自己这个从十七年走过来的人也中了所谓的“黑线流毒”,在一些场所,把自己过去接受的一些艺术上的问题,也作为“流毒”来清理。同时,用“四人帮”的艺术标准,特别是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模式“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以及写矛盾冲突的一套谬论来衡量自己的旧作,就觉得有些东西不够标准了。编选“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的时候,我把曾被一些同志肯定的作品,如《晌午》、《蜜月》等,视为是有“毒”的作品加以删除。搞新的创作,我使劲地学习样板戏的经验,明明感到是框框,强硬着往里钻,我对长篇作品必不可少的成长人物、被争取团结的人物,抱着极小心的态度对待,尽可能少写,怕犯“中间人物论”的错误。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没办法加进“阶级斗争”的线索,宁肯放弃,也不写,怕蹈“无冲突论”的旧辙。我机械地强调创作为政治服务,不多谈创作技巧,怕触犯“为艺术而艺术”的禁条。我尤其把“四人帮”那个“根本任务论”当作自己认识上的一个“提高”。总之,我把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所否定的,都当成“错的”、“旧的”,而把“四人帮”鼓吹的一套“样板戏”经验,都当成是“对的”、“新的”。所以我就声称跟“黑线”决裂,走“新”的,也就是以样板戏为榜样的创作道路。我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否定了自己过去十七年曾经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所走的道路,而把自己禁锢在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框里”,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必然铸成了写出《西沙儿女》这样的错误作品。
我出生在北方农村,成长在北方农村,一直用笔反映北方农村生活,对西沙生活没有任何积累,对处理战争题材没有任何经验,只凭着一个“大人物”派给的任务,就靠着临时采访的方法写起小说,这本身就是违反创作规律的。我这样做了,还扬扬得意地认为,自己积极地写了不熟悉而应当熟悉的生活,是及时地为“政治”服务了,是我所走“新”的创作道路的一个标志。实践证明,我这个创作活动为“四人帮”阴谋家服务了。所谓“新”路,正是旧路,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深入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以及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一个违背,是我对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正确道路的一个否定。“黑线专政论”、“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毒害,导致我的某些创作从为工农兵服务而变成为党内野心家服务,为阴谋文艺服务了,这个教训是多么沉痛!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制造争端、挑动派性,分裂了文艺队伍,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不堪回首的。就我个人的错误来检查,因那时运动的反复,我与本单位的几位作家伤了感情,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尽管我没有利用后来我自己的所谓得势的地位加害过任何一个作家,甚至没有对任何一级领导汇报过他们的情况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情况,但是在内心里我对他们有排斥情绪,不愿再到一起工作。我对他们遭受“四人帮”压制的痛苦没有切身体会,对他们不下乡、不写作品是受“四人帮”压制的结果没有认识,尤其对一些同志不下乡、不写作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抵制这一点,更不理解。所以在1974年以前,我在跟业余作者谈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带着感情说过,有些作家拿着高工资,不下乡、不写作品这些错误的话。我伤害了这些同志,我在这里道歉。1973年冬天文化局创评组搞所谓反“回潮”。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开始以后只参加半天会,进会场之前,文化局一位领导才在门口把会议的内容告诉我。我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凭过去的主观印象发言表态,支持这个会。我把这些同志遭到不合理的批判,看成是这些同志本身不好好地深入生活写东西而胡闹应受的处罚。我还从“重新组织队伍”这个错误观点出发,说市委能让这些同志回到创新岗位上来不简单,我让这些同志感市委的恩,不应当再给市委“惹祸”。我还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要离开创评组,搬到农村去。我以一个最“革命”、最“合格”的作家的神气“教训”别人,给那些受冤挨整的同志增加了精神压力。我要向这些同志承认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8)
1975年春天开始,随着我对叛徒江青这个人反感、憎恨萌起,对当时受“四人帮”摧残的农村生产,也有些不满意和担心。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华主席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我是从心里拥护的。10月里,根据我前一段的生活感受,写了中篇小说《三把火》。我想形象地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配合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以“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作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斗争核心。主人公杨国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土改以后当过干部的老同志,把他们团结起来,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稿子打印后要在《北京文艺》上连载,已到1976年春天。那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接着批判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我的《三把火》被揭发为是写“三项指示为纲”的,是宣扬“举逸民”,搞“复辟”的。当时我想不通,觉得用作品体现主席的精神没有错,可当时是有理没处讲的,不免又很紧张,怕被文化部抓了典型而遭到迫害。所以,第一次修改,也就是在《北京文艺》上连载的稿子,主要更动是消除“三项指示为纲”的痕迹,例如把女主人公访问、起用老干部的情节,改为访问“老贫农”等。在连载过程中,社会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的口号喊叫起来了,从市委有关部门到文化局各方面向我提出按这个口号修改作品的要求。特别是剧团要把它改成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调演,领导向我提出,全市只有这一个戏,参加汇演必须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只能搞成。搞成搞不成,关键在你协助。在当时那种压头盖顶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我从勉强到自愿、从别扭到顺手地按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调门,一遍一遍地加码,改写了这部作品。因为要遵照领导关于避开“三项指示为纲”、“三上桃峰”这个“三”字的指示,还把书名《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不管这个作品的修改过程如何曲折,但它是通过我的头脑思考、通过我的手完成的,要由我负全部责任。
所谓“写与走资派斗争”是“四人帮”一个重要阴谋。他们借着这套诡计,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这股风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医院。我又一次错把“四人帮”的诡计当成了党中央的号令,唯恐因住医院对文艺问题比较闭塞而落后于“形势”,我就从报刊上几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论的文章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二十三条”、“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以及毛主席当时的新指示开始学起。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不是系统的而是割裂的来学习,所以辨别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伪,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属于坏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谬论。我兼收并蓄地“学”了一通,又被从医院里叫出来参加一次文化局创评组召开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座谈会,听了一些发言,立刻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其结果,使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我把《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三把火》的素材是生活中来的:起用老干部问题来自通县的富各庄、果上山粮下川来自怀柔县蚕坊营;杨国珍这个人物来自密云县新农村的杜常珍等几位同志。到了改《百花川》,就完全按照上边,实际上是按“四人帮”的“要求”和“指示”图解了,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人物的原则。这也是林彪、“四人帮”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流毒和表现。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5月里路过南京师范学院时,在一个座谈会上大谈“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体会”,替“四人帮”扩散了毒素。我这方面的创作和言论不自觉地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他们效了劳。十年间,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事业的紧要关头,说错一句对革命不利的话,办错一件对革命不利的事,都是罪过,何况我说错了那么多、做错了那么多!我认账、还账、决不赖账。我的心情是随着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加深的过程而加重的。我十二岁成为孤儿,十四岁参加革命活动,十六岁加入党组织,十七岁开始一边识字一边学习写作。是党把我培养成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犯了错误,我怎能不认错、不改错呢?我是一个自认对党有感情、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为什么会犯下这样有害于党和革命的错误呢?为什么从懂事起就立志在私生活和在社会上都当个正派人的我,却在人生的途程上留下这样歪斜的脚印呢?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关键在于我自己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造成的。第一,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学习得不够,更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下过工夫,缺乏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主要凭着对党感恩的思想、凭着热情工作,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盲目性。“文化大革命”前,因多年当基层干部和从事新闻工作,养成一种偏重于当时的政策学习和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比较注意政治理论学习了,却赶上林彪、“四人帮”干扰,他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主义横行、形而上学泛滥,把我的思想搞乱了。这两点的直接后果是,当上边领导出现了坏人,又跟他们发生了工作关系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地被利用,当了他们的工具。第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大的挫折,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学习写作以后,一下子酷爱文学创作,不顾一切地为“创作”而奋斗。这里边既有新生活的鼓舞,有革命事业心,又有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顺利了,有成绩了,就扬扬得意,骄傲自满;有了困难,就急躁悲观;遇到风险,就总想保住写作权利;越有点名气,这个包袱越重,于是就有了怕字,不敢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低和一切围绕着“写作”,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字转,是我犯了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内因。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9)
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把步子迈正,把创作搞好。我现在虽然身体不行了,但还年轻,还能为党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党和人民给我的笔,写出较好的作品,以功补过,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