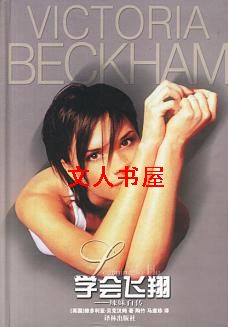浩然口述自传-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
1
算卦的瞎子给我批过八字儿,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如果父母比我还要命硬,那我就活不长;反过来,父母没我命硬,他们就得一个个地让我活活妨死!这是一项多么残酷无情、恐怖可怕的判决呀!
父亲性情豪放而豁达,对这种玄奥的占卜和奇特的预言,既没说过相信,也没说过不相信,似乎并不怎么往心里放。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对此,母亲特别固执己见。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我拜认了好几个光棍汉和“绝户头”的干佬儿。在她看来,因我“命硬”将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就好似是一件沉重的东西,让别人分担分担,自己身上的负载就小了些,轻了些。分担的人多了之后,或许就可以免除。
她甚至让我给街头的野狗作揖,给临往屠宰场送的肥猪下跪。说那狗到处挨打,为我减轻苦难折磨;说那猪吃一刀子,就代替我,或者替我的父母经受了死亡。
2
母亲的娘家很穷,除了耕种坟茔周围的一点点梯田薄地外,外祖父依然得到附近的山村做月工或打短工,外祖母给旱店子或洪水庄的地主当老妈子。他们早出晚归,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小弟弟看家,也看坟,守护住薄地上长着的豆荚、倭瓜和别的作物果实不被人偷走。
母亲终生念念不忘的是一位在北京念“大书”的“洋学生”。那学生家里是个大财主,家里人不让他干活儿,不让他管事儿,吃饱饭呆着不出门惹事就行了。为了拴住他,给他娶了个也是财主家的特别俊的媳妇,媳妇还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可他总是不高兴,不肯在家里睡暖床热被、吃鸡鸭鱼肉、守着娇妻爱子,连绫罗绸缎的衣裳都不爱穿。他经常到山沟里的乡村串门儿,身上是布衣布裤,脚上是布鞋布袜,只有手上总提着一条亮晶晶的“文明棍儿”。他常到坟地找我的外祖父来聊天,对我的外祖父特客气,笑模笑样地说话,称“您”,还把我外祖父说的那些“颠三倒四”不成句不成文的话,用铅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很喜欢我母亲,管我母亲叫“小妹妹”。我外祖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聊天。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跟小孩子,跟一个穷看坟的小孩子也有说不完的话。他求我母亲教他用高粱秫秸皮儿编蝈蝈笼子,用兰草编蛤蟆、编花篮儿。他答应我母亲等到冬闲的时节,带我母亲到村里去,跟一群穷人家的闺女学认字儿、写字儿。
过往行人,特别是那位好心肠的“洋学生”,在坟地茅屋前的瓜棚豆架下所留下的言谈话语,对于我的母亲——在当时只是一个长在偏僻的山沟里、穷看坟的闺女来说,不仅抵消了不少生活的孤寂,填补了头脑中的许多空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的母亲受到非同一般的思想熏染和风习影响。她再不肯用长长的布条子裹脚了。外祖母给她缠上,她就偷偷地抖落开。为着这种不遵守传统规矩的行为,她的脑袋经常被笤帚疙瘩打得小包刚下去,大包又跟着起来;身上也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总不见彻底消退。结果呢,她人长大了,脚也跟着长大了。那个时代,大脚女人是很难找到好婆家的,何况又是个最贫穷、最低下的看坟人的女儿。外祖父为这件事发愁,急得没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只好委曲求全地给她找了一个傻子做丈夫。她决不屈从,决不肯不舒心地活一辈子。就在要成亲的头天,一个月黑天的三更里,她逃出坟地的茅草屋,逃出山沟。
母亲只身一人,逃到将近百里以外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本指望能找到那位姓秦的“洋学生”帮助,不想从看门人那里得知他被诬为俄国人的同党,杀了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2)
看门的老头儿见我母亲可怜,诚心诚意地劝她跟他回家。
这老头儿姓梁,自称是个“命大”之人。就在我母亲到了看门老头儿家不久,刚刚上炕端起饭碗,偏巧来了一位好几年没有登过门的侄子。
等到串门儿的侄子一走,老两口就咬起耳朵根子,然后老头儿对我母亲说,刚才来串门儿的我那侄子,你看咋样?我估摸着准可你的心。
母亲也觉得“巧”。因为她第一眼见着那个串门儿的人,就觉得顺眼,面貌作派极像那位善良心肠、好性子、有学问的秦先生,听他一阵子热烈的谈论,越发觉得相似。她认为,这非同一般的事里,俩人肯定有缘分,应该成为夫妻。
三天之后,母亲被看门人和他的老伴儿简单地打扮一番,借一辆牛车,送她跟我的父亲拜了天地。
母亲常常无限哀怨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过了两年的舒心日子,前边和以后,没有舒心过一天!她所说的两年,是指跟父亲新婚后的两年。
那会儿,父亲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显然跟母亲是一致的。否则,凭他那一个大院两间房屋和二十亩土地的庄稼主儿,又是个模样不丑、身体不孬、性格爽直活泼的汉子,找个门当户对、符合规矩的闺女续为“填房”,绝不会有多大难处。他并不识几个字,却几乎自发地跟京里卫里的一些新派思想遥相呼应,特别好追“时兴”。他对受难的人极富有同情心,尤其对受难的女人。同时,他也渴求一种感情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的脾气有时候很暴躁,暴躁一阵儿,就像干柴猛烈烧过,立刻声止烟消,剩下的只有给予人的温暖。他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要不然,他不会在那种时代和那种环境里做出一件震动全村的事儿:每当母亲做饭,只要赶上回家,他就要帮着烧火。当母亲生了我的姐姐以后,不仅劳累,而且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父亲总是主动早起,替母亲抱柴、舀水,把早饭做熟。母亲吃饭,他就帮助带孩子。这件奇闻在村子里传开,“让人笑掉了大牙”。我的爷爷听到之后不相信,掐着做饭的时辰,悄悄溜进路南西头的小院子里一看,果真瞧见我父亲正“像老娘儿们那样撅着屁股”烧火。
爷爷被气得浑身发抖,抢过火棍子要打父亲:不要脸的东西,你还像个男子汉吗?
父亲抓住烧火棍子的另一端,抢白我爷爷:男子汉咋的?男子汉不吃饭行吗?要吃饭,不烧火,能生着吃吗?
爷爷说,烧火做饭,是老娘儿们的事儿呀!
父亲说,您看看,咱家的老娘儿们啥也不干,躺在炕上呆着了吗?
爷爷扭头看一眼,瞧见我妈正跨坐在炕沿上,一边奶着我姐姐,一边忙着做针线活儿。他没话可说,只好一跺脚,松开手,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式地骂了几句,故意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父亲接茬儿做饭,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3
可恨的水灾和兵灾,破坏了乡村的宁静日子,扰乱了人们自得其乐的心绪,改变了、甚至扭曲了不少正经庄稼人的人生道路。
这一切,都极为明显地影响着父亲。他渐渐变了,不安于守着妻子和孩子苦熬岁月。在一场大水过后竟然丢下妻儿老小,偷偷地离家外出了! 对父亲的行动,母亲很恼火,也很伤心。尽管父亲到赵各庄煤矿落下脚之后,就立刻往家里写来信,没过几个月又托顺路的同乡人捎来钱,母亲仍然不肯原谅他。
大水过后,压在土地上的积水渐渐消退,较高的地方露出了地皮。
面对一切灾祸都逆来顺受的庄稼人,见此光景,立刻活跃起来,纷纷踏进或锳进又脏又臭的泥水中间,奔到属于自己家的地界里,打捞泡倒、沤烂的秫秸秆和粮食穗子。于是,村子里立刻浮动起一种类似丰收年收割打轧的忙碌气氛。
母亲受到这种气氛的牵动,想到自己家的土地、地里的庄稼,她不声不响地磨快了镰刀,找齐了绳子和扁担,掩上门,拉着姐姐到村子当中、路北大槐树下的我大伯家。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3)
见母亲手里拿着家伙,大妈大惊失色地喊道,你到咱单家庄挨门地串串、瞧瞧,哪有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下地去的?
母亲说,不下地,庄稼能回到家吗?
大妈喊叫起来,你知道不知道,在这泥里水里干活计的男人,全都光着屁股……
母亲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光他们的,碍着我什么了?
就这样,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路上和左右两边邻家地里都有赤身裸体的男子汉的泥水中,折腾了三四天,终于把没有腐烂的庄稼穗子都剪下来,用背筐一筐一筐地运到家,晒晾起来。她把秫秸打成捆,拽到水浅的地方攒在一起,准备等道儿不大泥泞的时候,再往家里鼓捣。
她总算是用她推崇的、经常挂在嘴上的志气和正气闯过一道难关。她动手准备过冬的糠菜,以便带着孩子,熬过一个漫长的寒夜,迎接新的春天和新的希望的来临。
谁能料到,刚一入冬,又发生了一场新的不安宁——兵灾接踵而至。 大妈气喘吁吁地跑进我家,进门便嚷,大兵见男的就杀,见女的就糟蹋!你还愣着干啥,快带着孩子跑吧!
母亲听罢,转身回到屋里,立刻为难了:自己独自一人,怀着孕的身子行动不方便,又背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哪还有力气携带沉重的东西呢?最后,她只好慌慌张张地把磨好的一小布袋高粱面,还有吃剩下的几个夹馅饼子,一齐装进篮子里,用一只胳膊挎起来,另一只胳膊揽住背上的孩子,重又迈出门槛儿。
……
枪炮声停息了一天一夜,证明大兵已经过去后,母亲带着姐姐回到家中。家里的情景非常凄惨!锅被砸了,碗被摔了,鸡被抓走了,粮食、被子全都没了踪影。
母亲不仅没有像邻家人那样大哭大嚎或大骂大吵,甚至没吭一声,便关上门板儿,一边用糠秕煮些粥吃,一边照管我那在奔波中得了病的姐姐。她一连几天不出门,怕听那些可怜的人们乞求可怜的话。
终于在1931年年尾,1932年就要来临的时刻,母亲怀着我,背着我两岁的姐姐,冒着刺骨的西北风,绕过可能驻有大兵的村落,以太阳计时间,不停地赶路。一路上,遇上车就搭车,没有车就步行,天一黑,就寻找安全可靠的小店投宿。经过三天半的辛苦奔波,她跨越了玉田、丰润的县界,终于到达开滦赵各庄煤矿。
她从包裹里掏出父亲寄到家的那封信的信封,举着让过路人给查看,打听父亲的地址。
经人指认,母亲找到了父亲的小屋。一进门,便撞上一个人影。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真叫可怕呀!蓬乱的头发是长长的,瘦瘦的脸庞是苍白的,细细的脖颈是漆黑的,眼眶子显得特别深,嘴巴显得特别大。他上身穿着一件连乡村叫花子都不会要的破棉袄,又大又臃肿。那上面补丁摞着补丁,好些地方绽开了线,大窟窿小眼的,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黑棉花套子,垂吊着一条条一缕缕的布片子。而下身是一条夏天穿着才凉快的“灯笼裤”,裸着膝盖,也遮不住脚腕子。
分离的几个月里,母亲憋了一肚子怨气。奔波的一路之上,她准备了一大篇发泄的、能把人心刺痛的话语。然而,这一切一切,都被父亲的这身穿着,尤其是这一副衰落潦倒的凄惨相给赶跑了,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腹的怜悯和疼爱。
镇子外边的东南角上,有几个大粪场子,其中一个不知何故停工了。干活的撤走了,东西也搬走了,只是掏粪和晒粪人住的窝棚还没有拆掉,那里可以对付着住些日子。
于是,1932年3月25日,那个黑咕隆咚的半夜间,我在那个大粪场子的低矮而又破旧的窝棚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这以后,在摊晒着大粪汤、堆积着大粪干儿垛的包围中,在带着酸、辣的臭烘烘的空气里,我长到会说话,会走路,开始了我那充满着各种滋味儿的童年。
我记事儿晚,记性差,四五岁以前的事情,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印象,在脑海里几乎成了一片空白。即使保存下某些没有忘掉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些碎片片。而每一碎片,都如同经过人工筛选和雕琢,舍弃了多余的部分,保留下最美好、最令我珍惜的极少极少的那些东西。
。。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4)
睡觉、起床是最普通的事儿,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