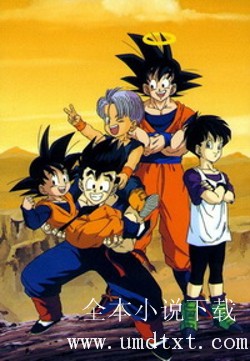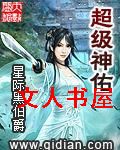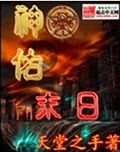詹天佑-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唐绍仪说:“詹姆斯,我们这些官学生只有你拿到了耶鲁大学有铁路专业毕业证,大清国万里河山,将来肯定要修很多铁路,你呀,大有作为呢。”
詹天佑说:“美国的报纸也报道,中国至今还没有铁路,有一些西方国家想在上海和天津修铁路,但遇到很大阻力,说中国官员不喜欢听到火车的轰鸣声,也不愿看到铁路穿山过岭,占用农田。”
梁诚说:“火车跑得快,全世界都在修铁路,日本这样的小国都修铁路,大清国那么广阔,就能坚持不修铁路,这不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吗?”
梁敦彦说:“大清国逆世界潮流而动的事多呢。你们没有听到美国人评价吗,说日本在美国有数以千计的留学生,我们大清国才这么百十来人,却那么多人反对,来了还要半途而废。大清国的人为因素太多了,当初我们能留学,也全因曾文正公全力推动,现在我们撤回,又是那么几个反对党在鼓吹,因人废事,这将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后果。”
詹天佑说:“不要小看这条铁路,横滨是通往世界的港口,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这实际上就是把东京连向了世界啊。美国人批评我们大清国把皇帝居住的地方称为紫禁城,不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皇帝住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很有讽刺意义的事情。”
横滨火车站的月台上站了许多接人的人,非常热闹,这与美国的各大车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呜——!一辆火车进站了,车站更热闹了。看在这些大清国的幼童眼里,真是好羡慕,尤其是詹天佑,对于火车和铁路,他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离开横滨火车站,梁诚问车夫,横滨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有,车夫高兴地说:“有!”于是拉着他们往另外一方向走去,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热闹的街区,只见街道两边的店辅装饰的古色古香,一些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涂着胭脂,擦着花粉,嗲声嗲气在招徕客人,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一看这情况,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詹天佑说:“梁诚小老弟,你要找好玩的地方,车夫把我们带来这里,你看这里好玩吗?”
唐绍仪说:“不要说玩了,中文教习常提醒我们,非礼勿视,要是吴嘉善大人知道我们来过这里,我们回去全都完蛋。”
梁诚知道自己惹祸了,申了申舌头,不敢出声。
梁敦彦叫车夫不要停车,赶快离开。车夫回头看了一眼这几个年轻的大清国小伙子,连连点头。鞭子一挥,赶着牛车迅速离开了。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车夫似乎在问现在还想去哪儿,梁敦彦说:“回码头!”
牛车回到了码头。詹天佑付了车费,因为时间还早,他们就在码头附近漫不经心转悠。
如梦乡途(2)
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日本装扮的男子拦住了他们,问道:“兄弟,你们是从大清国来的吗?”
几个人都被搞糊涂了,怎么这人用的是大清国的官话问话呢。梁诚说:“我们不是从大清国来的,我们是往大清国去的。”
那人问“你们不是大清国人?”
唐绍仪说:“我们是大清国人。”
詹天佑说:“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年前到了美国,现在从美国回大清国。”
那人说:“这就对了,你们归根结底还是从大清国来的嘛。”
梁敦彦说:“你不是日本人?”
那人说:“我是大清国人。”
唐绍仪说:“大清国人怎么一身日本人打扮?”
那人说:“没有办法,如果不改这身打扮会有日本浪人找麻烦的。怎么,你们来自广东吗?”
刚好这几个人都是广东人,詹天佑说:“是的。难道你也是广东人?”
那人说:“正是。”
梁敦彦说:“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那人说:“我做点小生意,到日本就改日本服饰,回大清国就改回大清国服。”
梁诚说:“可你回去没有辫子?”
那人说:“辫子好办,我有好几条呢。”
大家一听,都笑了,知道那人讲的是假辫。
那人说:“你们这么年轻,多年前就到了美国,是卖猪仔去的?不对呀,看你们温文尔雅的样子,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呀。”
詹天佑说:“我们不是卖猪仔去的,也不是富贵人家的子弟,我们是去美国读书的。”
那人说:“去美国读书,读西洋书,那有什么用,不在国内读四书五经,考个一官半职,跑到美国读洋书,回大清国做什么呀?”
唐绍仪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那人说:“不知道就不要去嘛。唉,说来我们也是有缘,我在这里很少见到象你们这样有身份的大清国人,噢,再见呀,希望下次再见到你们。”边说,边摆手走开了。
梁敦彦说:“这人也真奇怪,又要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又这样奇怪地走开了。”
唐绍仪说:“这说明,我们那些漂泊在国外的同胞,只要见到来自大清国的人,那怕说一两句话也是一种安慰,你不要以为他在这里做生赚钱,可是远离故国的孤独总是难于避免的。”
梁诚说:“是呀,人无论走到哪里,终归还是自己的祖国亲啊。”
詹天佑说:“梁诚是一个才子,说起话来总是抒情一样,你还写过不少英文诗,是吗?”
梁诚说:“写诗作词,无补于世用,还是你詹姆斯学的铁路技术好啊。”
大家随便转悠,很快到了上船时间,及时回到船上。
过了横滨,幼童们的心情开始浮躁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下一个码头就是上海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将以怎的方式迎接大家呢?出洋肄业局那座庭院还在吗?刘开成大人还能在码头迎接他们吗?
疑问与兴奋交织着填充着幼童们的脑海。
有些幼童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行李箱,再一次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把应该带回的东西都带回来了。詹天佑打开自己的皮箱,轻轻地捏了捏放在箱角的那块小铜镜,这是母亲陈娇当年在天字码头送别时亲自放到自己手上的,似乎当年的余温还在。这时,他碰到了一个用黑布缠包的小包,这一下撩起了他对潘铭钟的思念,这是在哈德福处理潘铭钟遗物时,他特地留下的,一块砚池,是从上海出洋肄业局带到美国的,这个典型的中国旧时知识分子的文房四宝之一,凝聚着潘铭钟在哈德福勤学苦读的全部生命历程,潘铭钟甚至还用这块砚池里的墨写过英文单词呢。当时,所有的人都为潘铭钟的去世而悲伤,詹天佑不仅与潘铭钟是老乡,而且平时相处得也是最好的,詹天佑在悲伤之余,比别人更多了一份沉重的心情,他在想,父母把潘铭钟养到十岁交给朝廷,他却因为过于勤奋而葬身异国他乡,没有沙场战士牺牲的壮烈,他的父母将一无所有。詹天佑对自己离家前一年三弟天瑞早夭的情景似乎还有印象,母亲那丧子之痛的伤心欲绝是令人难于忘记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大家不管以什么方式回国,毕竟都能见到自己的家人,而潘铭钟的父母却永远也见不到他们日思夜想的孩子了。于是,詹天佑决定不能让潘铭钟这样完全消失在美国,必须要帮他带点什么东西回到故土,他默默地从潘铭钟的遗物中留下了这块砚池。詹天佑轻轻地抚摸着这个小布包,眼睛有些湿润,他在想,如果能找到潘铭钟的父母,自己一定要亲手把这块砚池交到他们手中。这块砚池随潘铭钟最早一期到美国,现在它又最后一批随詹天佑回到大清国,从大清国带到花旗国,又从花旗国被带回大清国,它可是见证了一桩亘古未有的历史事件啊,凝聚了一百二十个大清国幼童九年间的全部历程啊。
终于看到岛屿了,幼童们激动起来,海浪不再咆哮,秋日的阳光照在海面,金光闪闪,海鸟在轮船的窗外飞来飞去,不远处还能看到渔民捕鱼的船儿,大家从窗口顺着前方望去,心中默念着:“上海,终于回到上海了!”
看到陆地了,看到陆地上那隐隐若现的房子越来越清楚,看到水草了,咣!突然船身震动了一下,好象碰触了什么东西似的,幼童们从想象中回过神来,“北京”号轮船停靠在了上海码头。幼童们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吴嘉善让一个中文教习通知大家先不要下船,等候岸上官府派人接应。大家一听,官府派人来,心中很是高兴,感到作为出洋官学生的荣耀还在。
所有的客人都下船了,这时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子进到船舱,按照花名册点名,根据吴嘉善提供的名单,这一批回来的幼童总共是三十九名,途中在哈德福和纽约分别有容揆和谭耀勋逃脱,实际应是三十七名,其余人员为监督、教习、厨师、裁缝、杂役和监督的家属们。中年男子说:“各位学童,我奉上海道台刘瑞芬大人的吩咐,前来接应大家,我叫陆海,请大家下船吧。”
点完名,幼童们马上感觉现场气氛不对,只好各自提着行李默默下船。走到码头一看,那里有几个兵勇拿着兵器排队站立在那儿,数十辆独轮车挨个儿排开。
怎么没有见到吴嘉善和中文教习们呢?
梁敦彦问走在身边的陆海:“陆先生,吴嘉善大人呢?”
陆海说:“吴大人已经坐轿去上海道台见刘瑞芬大人去了。他叫我代他向你们道别。”
梁敦彦说:“厨师和杂役也一起去了?”
陆海说:“是的。”
周围几个幼童听了,心中顿时失落了许多。
陆海说:“各位学童,请大家上车吧。”并用手示意大家依次坐上已在那儿等着的独轮车。
车夫们对大家笑,帮着幼童们把行李放在车上。每一辆独轮车只能坐一个人,这样,每一个幼童坐上一辆独轮车,各自的行李则放在独轮车上与人对应的另一边。幼童们多年没有坐过这种车,只好由车夫帮助他们坐稳。
陆海自己坐在最后一辆独轮车上,这样,三十八辆独轮车一齐从码头起身,兵勇们拿着兵器行走在独轮车队伍的两旁。这支奇怪的队伍行走在大街上,吸引了许多行人的目光。幼童们坐在独轮车上,自己也感到非常别扭,感到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在带着异样的神情看着自己。这哪里是光荣回国呀,这简值如犯人*。所有幼童的心一下子冷到了冰点。
詹天佑打量着街道两旁,发现上海比九年前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想寻找当年肄业局的方向,但是根本分不清。
很快到了上海道台衙门,可是,没有见到上海道台刘瑞芬,也没有见到吴嘉善,幼童们按照陆海的提示,下车后各自提着行李排成三排队伍,一个官吏模样的人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点名册,一个一个点名,唱完名,对大家说:“各位学童,刘瑞芬大人说了,今天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先吃了晚饭,再歇息歇息,今天就不接见大家了。衙门为大家准备了晚餐,请大家先就餐吧。”
上海道台衙门的冷遇,所有幼童都感受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无话可说。
吃过一顿简单的晚餐,他们被带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这座书院也是一处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院子里有几棵葱郁的金桂树和银杏树,可以闻到幽幽的桂花香味,银杏的叶子有些发黄。青石板上长满了青苔,有些树枝之间还能见到一些蛛丝网,空气中有一些潮湿的味道。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在这里生活,庭院里的幽静与幼童们在美国学校或驻洋肄业局的环境相比,真是反差太大了,即使是当初的出洋肄业局也比这里要好一些,这里的环境更加重了幼童们内心的压抑。
陆海给每一个幼童派发了了一付床板,一床棉被,还有一盏煤油灯。
晚上,门口守着几个兵勇,幼童们只能在“求知书院”里面活动,不得外出。
唐绍仪的床与詹天佑的床紧挨着,他们望着煤油灯,好一阵子都没有讲话。唐绍仪先开口了,他说:“天佑,你说吴嘉善大人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这样与我们分手了?”
詹天佑说:“我也感到奇怪。可是,他对我们幼童的反感与我们幼童对他的憎恨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或许他有难言之隐吧。”
唐绍仪说:“平时,吴大人一直强调我们要讲礼仪,可是他这样突然地不见我们,也不管我们,真是很难说符合礼仪呀。”
詹天佑和唐绍仪不知道,吴嘉善确实有他的苦衷,他一个人承受了撤回肄业局的全部责任,他只在上海匆匆与上海道台刘瑞芬见了一面,就直奔北京,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交差去了。他下船时确实想与幼童们告别,毕竟大家相处了数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