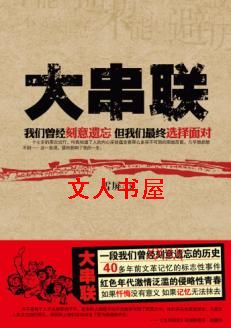山歌年代-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А⒚苈胙А⑶楸ㄑ榧约荷杓埔桓稣感碌男蜗螅和反髟裁保笄鸺茄傻某檠┣眩笪律粢谎嗲椋凵裎薇认芮芑裆俑镜那榛常漳芊采倥姆夹摹N揖钩彰哉庵旨锹迹刻焱砩弦耘ザ廖杩诰∏榉手笔椋荒茏园巍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迷航(6)
有天我同郑华上同一个班,发现他愁眉苦脸;陶醉在流言中的幸福感荡然无存。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说小凤要结婚了。大概流言传得太盛,传到了小凤父母耳朵里。她们自然不希望未来的女婿是外地人,又窝在书店里没有前程,所以加快了为她物色如意郎君的脚步。他们为她选了一个工厂主的儿子,她去见了,除开有钱,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她本来对婚姻大事毫无主见,懵懂不清,父母极力撺掇就同意了。婚期定在下个月。这几日常能看见一辆银灰色的本田雅阁接送她上下班。
人高马大的郑华俨然一只躲在深洞中的小鼹鼠,失落、茫然、自卑、迷惘五味杂陈,在角落里注视着小凤的姿影木然发呆。后来触电事件发生了。店内的防盗器出问题,平时是他负责维护修理,这次他象往常一样拿了工具箱蹲在机器前操持,眨眼功夫倒在地上。谁都没想到这位精熟电工的仁兄会触电,当时还以为是没吃早饭低血糖晕厥所致。救护车呼啦呼啦驶来,医护人员做了简单的急救措施后抬走了他。他沉重的躯体砸得担架嘎吱作响。到晚上,我收到他的短信,寥寥几个字:“一触解千愁。”我猜不透这样的字眼是悲观还是乐观。
因为前些日子的晚归,行动神秘兮兮,神情鬼鬼祟祟,妻子怀疑我有外遇。起先我还矢口否认,在她喋喋不休的追问下,我同她摊牌。那是我这个完美丈夫第一次大发脾气,第一次承认我同别的女人有染。我言辞激烈,将满肚子的泔水一瓢接一瓢的往她身上泼,把她批得又臭又硬。她也拿出女强人的姿态跟我干上,结果;我敌不过她;因为我的物质生活是她提供的;所以我被扫地出门。我暴躁的摔了几样东西,丢下父母的惊叹与孩子的哭闹离开了身后所谓的家。
短暂的茫然不知所措后,我决定动身到H县山脉路五十号找仙妮。到达H县后,百般打听,我终于找到山脉路,五十号是独立于其她四十九号的建筑,四面种植着高大挺拔的乔木。生活在五十号的人也不同于其他人,光是神态就难以琢磨。也许是间谍工作使然,他们装扮人物,有医生,有护士,有病人,看来我正巧赶上了乔装医院工作人员的训练课程。他们的演技无可挑剔。我找到一个抄着手,鼓瞪眼睛,张开嘴巴,抬头看天的男病人搭话。
“我找仙妮。”我说。
他缓缓低头,投来极富智慧且深邃的一瞥。
“找谁?”她深沉的问道。
“仙妮,你们的同志,”我将手中的金属书交给他,以证明我确实知道他们的秘密,“你们是间谍。”
“嘘——!”似阻止我道破,他捂住了我的嘴。“小声点,别让其他人听到。”
“内部也保密?”
“当然。”他说,“其实我和仙妮还有更重要的身份。我们不是一般人。”
“怎么个不一般?”
“我们来自火星。”火星两个字他说的很平缓。“仙妮是她来地球的化名,她的火星名字叫扑勒克克克斯。”
“不可思议。那么仙妮,我是说扑勒克克克斯人呢?”
“先回星球去了。不过她会回来接我。我每天仰望天空,其实是在观察她抵达的迹象。相信我,仙妮会接我回去,你有信物,她也会接走你。”
在火星同扑勒克克克斯美不胜收的生活,多令人心驰神往。看天空的火星人向我保证,无论我在哪里,某天一架飞碟会出现在我头顶,打开舱门将我带走。炽热的幻想使我神轻气爽,我在归途中好几次笑出声来。
我收到妻子的短信。她向我承认错误,并说看到了公务员教程上写的东西,要同我谈谈,重归于好。我对我们的交谈从来没有信心,最终的结局总是我服从她。
这条短信搅得我心烦意乱,一边是低头认错的结发妻子,一边是令人向往的火星生活,我突然面临着一个哈姆雷特似的艰难抉择:
同她和好还是随扑勒克克克斯去火星,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山歌年代(1)
那年我患了肺结核,医生建议到一处空气新鲜的地方疗养,我便休了半年学去了外婆家,一个看起来宁静祥和的客家小镇。
嫁给爸爸以后,妈妈再没有回过娘家,我还是从她每年填寄的邮单上得知乾镇这个地方。三天三夜的长途旅程后,我见到了纯朴的亲人。叔伯兄弟们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为我接风洗尘。饭后我被安排到家庭条件最好的大舅家居住,他们对我关怀备至,生怕我磕着碰着向妈妈交不了差。亲情固然温馨,但我始终觉得他们拿我当外人供着。彼此操客家方言,独独对我讲应付外乡人的官话,我感到身上的客家血统被冷落了。我偷学了几句客家话拿出来显摆,希望引起共鸣,却招来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
有堵无形的墙横在我和亲人之间。六月初六我尝了新米,却没有祭祀土地老爷、五谷大帝,七月半放水灯的风习干脆瞒而不报。问何以如此,他们答说怕我笑话乡下人的鄙陋。在大舅家的日子,虽然好吃好喝,我却精神沮丧,茹饮孤独。最后实在忍受不住,发了通大脾气。大舅百思不得其解哪里怠慢了我,倒是外婆大略明白我的心意,问我愿不愿去听山歌。
我求之不得,即便病得更严重,也想经历一番客家人的独特体验,方才不虚此行。
于是外婆带我去了一家挂满白底黑字木牌的茶铺。除了“老人山歌会”的牌子,另外有“老年活动中心”、“文化茶园”等名目,可见是小镇老年人重要的聚会场所。
茶铺是清末样式的老铺房,木板插进门槛排成门面,放眼望去,老式黑白电视机里见到的灰白图像映进眼帘。采光单靠一圈天井采光,还算敞亮。天井左边的柜台上摆放着点好茶叶的盖碗茶,凡有人叫茶,勤快的老板娘抓起茶壶,携一盏茶碗放在客人桌上,再将新鲜开水注进,斜斜的合了茶盖,一抹起细沫的盈盈翠绿浮现在盖子边缘,勾人眼馋。卖茶外,柜台亦兼卖各种食品杂货。另有柜台放置着纱帘围成的纱笼,内堆猪头、牛肉、鸭掌、豆腐干等腌卤制品,方便叫酒喝的客人做下酒菜。其余大部空间错落有致摆起竹椅方桌,老人或三四个一组,或六七个一群,插科打诨、敬烟啜酒、码牌博弈,其乐融融,我仿佛听一架雕镂精细的古老座钟悠然晃着钟摆。
外婆是熟客,老相识们满堆笑容招呼她:“秀珍姐来了,泡茶,算我的。”外婆称声谢,径直抬张竹椅坐下,提起嗓门与同样来喝茶的老妇人聊家长里短。
外婆把握介绍给几位花甲老人。他们都认识妈妈,口中管她叫“幺妹子”,是乾镇读出来的不多的几个大学生。得知我也是大学生,他们开玩笑似的对外婆说:“秀珍姐;你们家的弯弯树怎么种正的?”我不懂此话的意思,但知道是句赞扬的话。有老人山歌会的会长阿山叔,乾镇名望很高的厨子,教出来的五个徒弟现已自立门户,外婆说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吃他做的夹沙肉;另一位林阿伯是屠户,外号“林瘟猪”,肉摊就摆在茶铺外面,听说猪见他提刀便会发瘟自行了断。有人喊割肉时,他便跑出去分筋错骨,让你觉得在人身上动刀子也会很爽利。他不断提起妈妈伶牙俐嘴同他讨价还价的旧事。
闲谈过程中,我左顾右盼,闻不到任何有关山歌的气息。外婆似忘了此行的目的,没有半句提及。被算计的感觉又浮上心头,我决定先开口搞清楚状况。
“阿山叔,你会唱山歌吗?”我问老人山歌会的会长。
“会,”他没有谦让,“过去谁能唱得过我阿山,哪个妹子不想同我阿山对歌。现在,”他摆摆手,”不行了,老了,那口气早歇菜了。”
“唱‘郎搭妹,妹搭郎’的情歌,阿山是这个。”林阿伯竖起大姆指凑趣道,“若唱掌牛歌,我敢讲我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小时候命苦,起早贪黑去给地主家掌鸭掌牛,一个人孤零零上下山,怕得慌。就吼山歌壮胆,久而久之,吼出一副好嗓子。”
“林阿伯,”我鼓动道,”给唱个掌牛歌。”
“味道不对了。”林阿伯惭愧摇头,“我怕糟蹋了歌。要说唱歌,最厉害的还是女人,女人声音甜,有神。”他斜了一眼外婆,“你外婆也是高手。外公就是被她的歌声勾了魂,死乞白赖央着媒婆倒她家说亲。”
“没羞”,外婆说,“过去的事莫在小孩子跟前乱讲。大家心里亮堂得很,歌唱得最好的不是我,也不是你们。当初你们从没夸过哪个人的嗓子,独独夸过阿银,现在倒退步了。”
外婆提到阿银的时候,两位老前辈忽然缄默不语。他们低下头,裹起烟叶掩饰脸上的窘态。这个名字犹如寒山寺凄凉的钟声,渗进其他听闻者的思绪里,令他们微微一震。
外婆自觉口误,赶紧转移话题。名字的影响尚未淡去,一个十六七岁模样,衣着妖冶,满头棕褐色的波浪卷发的女孩破门而入。她的面孔浓妆艳抹,眼影、睫毛膏、粉底、口红能用的化妆品好象都用上了。迷你裙,*袜,一双白色帆布鞋,裹挟着廉价香水的味道涌进茶铺,感觉是迷路投错了地方。
女孩吐掉口香糖,随手把挎包扔进靠椅里,冷淡地环视茶铺一圈。仿佛发出了信号,老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动,稀稀拉拉的挪动桌椅,众星拱月般朝向女孩。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外婆咬着我的耳朵说:“听歌吧!”不愿多做解释,跟着调整了座位。
其实,老人们对女孩并无好感,刚才悠闲的面孔此时大理石般生硬冰冷,我甚至从藏不住感情的老人眉梢读到憎恶。女孩也不待见老人们,只顾照镜补妆,你会以为是两个敌对的阵营狭路相逢。冷漠的对峙叫我费解。
女孩往靠椅上以座,翘起盛气凌人的二郎腿,端起桌面上的白开水润润喉,紧接着微启朱唇,唱出一段新鲜的声音:
妹子生得好人材,
好比月光走出来;
妹是月光哥是日,
不知几时做一堆
……
这应该便是山歌,我抛开脑际萦绕的疑惑去追逐歌喉发出的精彩回响。
女孩的歌同她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歌声清新甜美,词从她的嘴里精灵般蹦跳出来,化作一缕明媚春光,一笼沉沉暮霭,然后,从此背景走岀一对彼此相悦的男女,倾诉着炽热的思念。不止白天,思念漫延到夜里。月亮出来了,满室熠熠生辉,两个人不约而同走到窗前,共向月光祷祝心事。
老人们早已洗尽初见她的不悦,全神贯注倾听,有的忍不任脚踩节拍,晃起脑壳浅吟低唱。
温柔过后,女孩突然拔高音调,两匹峭山陡然而起,滔滔流水阻遏通路。蓦地,从山岭中飘出果决的海誓山盟,高亢激越,架起一座浩浩然的音桥,老人们昏浊的双眼登时闪岀光彩,有如执迷信徒聆听高僧大德教诲后顿然开悟。
每首歌的间歇无异于凌迟耳朵。没有歌时,老人们继续厌恶女孩,恨不能摧毁那副承载天籁的糜烂躯壳,据歌喉为己有。歌声响起,全又变成六神无主的风筝,任女孩舞动着线圈控制他们的喜怒哀乐。
不仅他们,复归平静时,我的骨头业已酥软,两只手掌着魔似的拼命鼓掌。女孩投来冷冷一暼,好像我多事似的。我的掌声也惹得老人们侧目愠怒。我纳闷,先还听得如痴如醉的他们,宁将愉悦悄悄藏在心底,也不肯施舍一通掌声,一句赞许的话。他们看女孩的眼神永远带着不解挑剔,指摘,这也是我曾经遭遇过的眼神,但相较之下,他们对这位妩媚的女孩更加苛刻。
随后,老人们口袋里掏出叠得四方四正的手绢,一层接一层的展开,拿起钞票交给阿山叔凑份子。阿山叔把钱掷到女孩面前,背转身便走。女孩抓起大把零钞向老板娘兑成整钱,迎亮光照照真假后,粗暴地揉进挎包,拎起它快步离开茶铺。茶铺又恢复到听歌前的状态,仿佛经历的不过是场美丽的梦。
那个谈之色变的名字——阿银——此时教我无法释怀。我们离开茶铺后,我鼓起勇气寻求答案:“那妹子是阿银?”
“不是。”她说,“别来钻我们老人的牛角尖。”
“您骗我。”我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她就是阿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