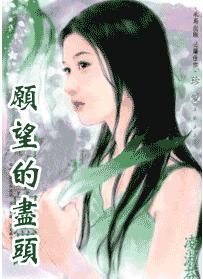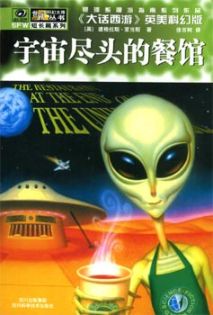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伸缩了好几次。熟悉蛇腹管的伸缩状况后,依序按了按右边的琴钮,同时按了一遍左右的和音钮。等其全部发出音来,我停下手,倾听周围动静。
老人们挖坑之声仍响个不停。四把锹尖啃冻土的声响,汇成杂乱无章的韵律,异常真切地涌入房间。风时而吹响窗扇。窗外残雪点点的斜坡触目可见。我不知道手风琴声是否传至老人们的耳畔。大概不至于。一来声小,二来逆风。
拉手风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新键盘式的。因此好半天才得以熟悉这老式结构和按钮的序列。由于小巧玲珑,按钮也小,且间距极近。对妇女或小孩倒也罢了,而男人的大手上去,弹奏自如远非一件易事。更何况还要一边注意旋律一边有效地控制好蛇腹管。尽管如此,一两个小时过后,我终于随机应变地准确弹奏出几个简单的和音。而旋律却横竖浮现不出。我反来复去按动琴钮,力图回想起类似旋律的声音,结果想起的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音阶罗列,无法把我带入音乐境界。时而也有几个音的偶然组合使我蓦地为之动念,可惜即刻为空气吞噬得无影无踪。
我觉得,自己所以搜刮不出任何旋律,恐怕也同老人们的锹声不无关系。当然不止于此。不过他们发出的声响妨碍我集中神经也是事实。锹音那样清晰地声声入耳,以致我竟开始恍惚觉得老人们大概是在自己脑装里挖坑。他们越是挖得起劲,自己脑袋里的空白越是迅速扩大。
时近中午,风势愈发凶猛,并夹杂雪粒,雪粒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劈里啪啦干巴巴的声响。而后变得冰一般坚硬的小白粒落在窗棂上不规则地排开,稍顷被风吹走。虽不是能积留下来的雪,但不久恐怕就将变成潮乎乎软绵绵的雪团,向来如此。随后大地再度银装素裹。硬雪粒一般都是大雪来临的前奏。
然而老人们仍继续挖坑,看样子根本没把雪放在心上,甚至根本就不晓得雪从天降。谁也不望天,谁也不停手,谁也不开口。挂在树枝上的衣服仍在原先位置任凭狂风猛吹。老人数量已增至6位,后加进的两人使用的是丁字镐和手推车。拿丁字镐的老人跳入坑
内刨开硬邦邦的地面,推手推车的人用锹把掘出坑外的土铲进车内,推往斜坡卸下。坑已挖到齐腰深。风声再大也已无法消除他的挥锹抡镐的声响。
我打消想弹的念头,将手风琴放在桌面,去窗边观看一会老人们的作业。作业现场似乎没有指挥模样的角色。大家平等地劳作,没有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手持丁字镐的老人卓有成效地摧毁冻土,四位老人用锹掘出坑外,另外一人默不作声地推车把土运往山坡。如此静静观望挖坑时间里,我开始产生几个疑问。其一,作为垃圾坑未免过大,无需那么大;其二,眼看就要下雪。也许用于其他什么目的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雪无疑要被吹入坑内,明天一早恐怕坑己被埋得了无痕迹。而这点老人一看云势即当了然于心,持续飘落的雪已封到了北大山的腰部,山腰依稀莫辨。
如此思来想去,终归也未解开老人们作业的意义何在,便折回炉前在椅子上坐下,不思不想地怅怅看着通红的煤块火苗。我想,自己恐怕再也记不起歌曲。乐器有没有都是一回事。纵使音发得再好,若不成曲也终不过是音的罗列,桌面上的手风琴也终不过是精美的物体而已。我似乎理解了发电站那位管理员所说的话。他说:没有必要出声,光看就足以叫人动心。我闭目合眼,继续倾听雪打窗扇的声音。
中午,老人们终于中止作业,返回官舍。地面剩下的只有随手扔开的锹和丁字镐。我在窗前椅子坐下,望着空无人影的坑。望着望着,隔壁大校来敲我房间的门。他依旧身穿那件厚大衣,带檐的工作帽拉得很下。大衣和帽子都厚厚落了一层白色雪粒。
“看样子今晚会有相当厚的积雪。”他说,“午饭拿过来?”
“那当然好。”我说。
10分钟后,他双手端锅返回,放在炉子上。然后俨然甲壳动物随着季节更迭而脱壳那样慎之又慎地逐一脱去帽子、大衣和手套。最后手指捋着纵横交错的白发,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对不起,没能来吃早饭。”老人道,“一大早就有事非做不可,没工夫吃饭。”
“该不会是挖坑吧?”
“挖坑?啊,你指的是那个坑。那不是我的工作。尽管我不讨厌挖坑。”说着,大校哧哧笑了起来,“在镇里做事来着。”
等锅温热,他把里边的食物分在两个盘里放在桌上。青菜煮面条。他一边吹气,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那坑到底干什么用的?”我问大校。
“什么用也不干。”老人把汤送进嘴里,“他们是为挖坑而挖坑。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极其纯粹的坑。”
“费解啊。”
“十分简单,他们是想挖坑才挖的。此外谈不上任何目的。”
我嚼着面包,思索这所谓纯粹的坑。
“他们经常挖坑,”老人说,“大概和我迷上国际象棋是同一道理吧。既无意义,又无归宿。但无所谓。因为谁也不需要什么意义,更不想找什么归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分别挖看纯粹的坑。没有目的的行为,没有进步的努力,没有方向的行走——你不认为这样很好?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受谁伤害;谁也不追赶谁,谁也不被谁追赶。没有胜利,没有失败。”
“你说的我好像可以理解。”
老人点了几下头,把盘里最后一口面条倒进嘴里。
“在你眼睛里,或许这镇子的几种情况有欠自然。但对我们来说则是自然的。自然、纯粹、安详。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恍然大悟,也希望你大悟。我曾作为军人送走了漫长的岁月。也就罢了,并不后悔,毕竟自得其乐。现在还有时想起那硝烟那血腥那刀光剑影那冲锋号声。然而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驰骋沙场却无从记起。包括什么名誉呀爱国精神呀斗志呀仇恨呀等等。可能眼下你在为心的失去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也惶恐不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到这里,大校略略停顿,寻觅词句似的注视着室内。“但一旦丢掉心,安详即刻来临。那是一种你从来不曾体味过的深切的安详感——这点你可不要忘记。”
我默默点头。
“对了,在镇里听到了你影子的消息。”老人用面包蘸起面条汤说道,“听说你影子相当无精打采。吃进去的几乎呕吐一空,好像已经整整卧床3天。或许不久人世了。你要是不嫌弃,就去见他一次好么?对方估计也很想见你。”
“是啊,”我装出不无迷惘的样子,“我倒无所谓,可看门人能允许见吗?”
“当然允许,影子快不行了嘛。本人有见影子的权利,这条规定得清清楚楚。对于镇子,影子之死是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看门人再厉害也不得阻拦。也没有阻拦的理由。”
“那么,我这就去见见。”稍顷,我说道。
“是啊,这就对了。”说着,老人凑到身旁拍了下我的肩膀,“趁还没有天黑积雪时去。不管怎么说,影子对人是再亲近不过的。要好好体谅他的心情,以免留下遗憾,让他死得舒畅些。或许你会难过,但终究是为你本身。”
“完全明白了。”
说罢,我穿好大衣,缠上围巾。
正文 31。冷酷仙境(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轨道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便于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满怀欣喜。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10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
“怎么也不怎么,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壁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明脚下,空调器保持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开往涩谷的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正在地铁线路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是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停进站台,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已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默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