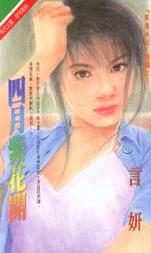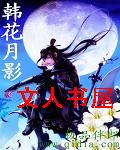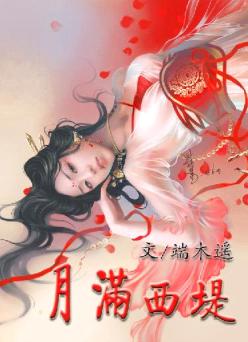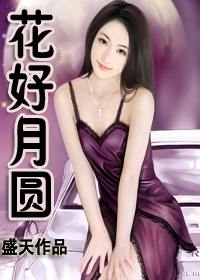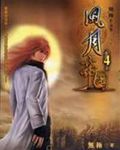沸腾的岁月-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懈,并且逐步蔓延到华尔街权力与名望的中心。1926年,未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开始了一系列侵占他受托保管的基金的行为(而公众直到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一点);1929年,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总裁通过卖空本银行的股票将400万美元中饱私囊。在华尔街60年代的弄潮儿身上,没有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行径,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发现。但在1926年,J·P·摩根的一名合伙人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而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摩根家族受到了上帝的庇佑。这位合伙人公开吹捧通用汽车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与该股票有很大的利益关系。40年后,1966年,华尔街遭遇了同样的震惊,因为人们获悉,两年前,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pany)的一名重要副总裁,在半个小时内买进或者授意买进了1万股得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exas Gulf Sulphur)的股票,而这明显是因为掌握了该公司在安大略发现大量新矿的内部消息。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在许多有趣的细节上展开。两次大崩盘发生时都是共和党人当总统,他们都当选于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都非常重视商业发展。两次大崩盘发生后,总统都在白宫与华尔街的领导人一起举行了精心计划又大肆宣传的会议。最后,两次崩盘都导致了疯狂的互相指责。
当然,这两次崩盘也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后一次崩盘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全美经济萧条(虽然情况确实很严重),还有性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差别,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如果将1929年的大崩盘与1969~1970年的大崩盘进行比较,人们甚至能够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3
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罗斯·佩罗的“坠落人间日”之后不到3个星期,华尔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军入侵柬埔寨刚刚一周,肯特州立大学案件过去仅仅两天,全美80所大学因学生和教师罢课完全关闭,另有三百多所学校的学生抵制上课。纽约市的大部分中学和大学都计划在5月8日星期五关闭,以筹备抗议活动。在所有的学生反战游行示威计划中,有一场将在华尔街举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着白衣的医科护士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来到华尔街进行和平示威。他们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纳德·R·伍沃德(Donald R。 Woodward)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位富有年轻活力、热爱和平的牧师。在交流过程中,师生们建议,考虑到华尔街地区白天的庞大人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个午间急救中心,因为三一教堂自殖民时期就屹立在华尔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处在金融区的中心—尽管没有成为它的精神中心。师生们说,如果三一教堂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将负责组建急救中心,并配备志愿人员。牧师充满感激和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急救中心正式启动的第一天就是5月8日星期五—回想起来,这一巧合简直是天意。
星期五,5月的纽约一个寻常的潮湿、寒冷、令人眩晕的早上,从大约7点半开始,数百名男孩和女孩从华尔街的两个主要地铁站—位于大通曼哈顿广场的第7大道百老汇站和位于百老汇与华尔街交汇处的列克星顿大道站—涌出。他们大都来自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和各个公立高中,这些学校在这一天都关闭了。最后,他们的人数达到1 000人,全都涌向金融区的中心广场,也就是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交汇处,在一群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示威。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打算找警察的麻烦。在细雨中,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联邦大厅立柱下,面对这令人生畏的摩根帝国曾在其中运筹帷幄、影响国家命运的大理石建筑,他们振作气势,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几天前纽黑文市的几个激进的青年领导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达成的一样,现在正在东北部数十所大学的校园里传开,这并不令人奇怪。第一,美国立即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军。第二,释放国内的所有“###”。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因被控参与折磨和谋杀亚历克斯·拉克利(Alex Rackley)而入狱的黑豹党成员,拉克利是一名被指为警察眼线的黑豹党成员。第三,停止一切大学资助下的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与1970年春天的许多次学生游行不同的是,这一次完全是非暴力的。事实上,学生们表现得非常配合,到了中午,雨过天晴,他们的情绪更好了。大部分的游行者坐在人行道上听演讲者演讲。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戏剧高潮(3)
11点55分:突然,从广场的四个入口同时涌入了大量建筑工人,就像训练有素的奇袭部队。他们许多受雇于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工程,他们褐色的工装和橘黄色的安全帽此时看上去像某种制服。他们许多拿着美国国旗;还有的人带着建筑工具,穿着重重的靴子,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武装。后来,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行动整齐划一,是因为有两个戴灰帽穿灰色套装的人用手打信号指挥。他们差不多有200人。
当他们冲过坐在地上的学生人群时,人们看清了他们的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国旗插在联邦大厅(又称国库大厦)门前华盛顿雕像的基座上,另一个是破坏游行,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边向雕像前行进边高喊,“向前进,美利坚!”“不爱她,就离开她!”在台阶上,他们遇到了少数警察的阻碍。由于在人数上对方占有压倒优势,警察很快被推到一边。国旗被成功地插上了雕像基座。为了第二个目的,建筑工人们不停地用棍子、拳头、靴子、螺丝起子和钳子殴打学生。他们在金融区的狭窄街道上追赶尖叫的男女学生,只要够得着就拼命打。他们从三一教堂的前门撕下代表刚刚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红十字旗。空气中充满了怒吼和哀号,以及血腥暴动的气息。勇敢的伍沃德牧师在自己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一直守在三一教堂前门,指引受伤者去里面的急救站。有两次,由于害怕教堂被侵犯,他命令关上大门。
三一教堂里面正在举行圣餐礼,恰巧是为了悼念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和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参加圣礼的人先是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越来越大的骚乱声;随着圣礼的进行,他们看到不断有流着血的学生走过或被扶着走过礼堂边上通往圣器储藏室和牧师更衣室的通道,年轻的医生和护士已等在那里为他们处理伤口。一共有50名游行者在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治疗,另有23人由于伤势过重必须送往比克曼市中心医院治疗。
此后一个多星期,华尔街到处是警察,人们仿佛身处法西斯国家。
这场规模虽小但程度激烈的暴乱,浓缩般地反映了全美国在那一时刻的悲剧。在这场令人沮丧的事件中,专业人士的华尔街,金融和法律的华尔街,权力和上流社会的华尔街,似乎站在学生这边。也许是出于普通的人性,也许是出于阶级情感,华尔街的牛派和熊派更加同情鸽派,而不是鹰派。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合伙人罗伯特·A·伯恩哈德(Robert A。 Bernhard)也在交易大厦遭到袭击,他在试图保护一名被殴打的年轻人时,被一名建筑工人用钳子严重打伤头部。往北几个街区,一名年轻的华尔街律师在抗议建筑工人时被推倒在地,遭到踢打。但大部分华尔街的权势人物都没有参与这场争斗,他们不在华尔街头。与1920年导致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著名华尔街爆炸案一样,1970年的骚乱也正好发生在邻近正午的时候:而不是午餐时间。街上出现了喧哗,高楼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职位高得拥有一扇窗户的人)都往外看。市场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的大部分精英们只是从高高的安全的窗口看着这场屠杀。
实际上,他们也做不了别的;即使他们冲下来,加入混战,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然而,这一天,华尔街的精英们充当看客的做法却有着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面:诚然,他们同情弱者,同情手无寸铁的人,同情和平爱好者,但是,他们袖手旁观—充满惊奇和恐惧地,从俯瞰可爱的(从他们的角度看)上湾地区的窗口往外看。此时的上湾地区,岛屿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来来往往的邮船穿梭其间。他们向下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那里传来受伤或受惊吓的孩子们刺耳的哭喊声。
4
这次事件(就像佩罗缥缈沉浮的命运一样)让人们关注起新时代华尔街与美国的关系,或者根本缺乏这种关系的现实。华尔街还能这样大玩纸面游戏、高高在上,而不顾窗外孩子们的哭喊声吗?没有人听到远处革命的断头台发出的嘎嘎声吗?那么,无论如何,如果你是一名1970年的华尔街人,至少你不能直接从战争中赚钱了。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时代,股票市场仍坚持一种老习惯,那就是在战争新闻面前,即使不是直白的欢呼,也是暗自得意,而在和平新闻,华尔街人士称之为“和平恐慌”面前,却表现出惊慌和歇斯底里。但1967年底的某个时候,华尔街开始认为越南战争不是一桩好生意,从而打破所有先例,毅然决然地反对战争,并表现出悲观,拥抱和平。军需企业不再是蓝筹股,最大的军需企业之一洛克希德很快将面临破产的危险。1968年初的和平运动导致或帮助成就了交易量创历史水平的大牛市。这是一个人们前所未闻的现象;华尔街旧的不光彩的一面结束了,有良知的金融家们舒了一口气。
或者,如果你是有良心的华尔街人,你可以对自己说,你的贡献在于为工业扩张提供融资,而这能帮助减少贫困,并最终消灭贫困。但现在你知道,或者最近才被迫反思,工业扩张并非只有有利的一面;每家新的工厂,不论多么现代化,多么清洁,都将在为许多人带来财富的同时,通过污染环境而带来丑恶、痛苦和死亡。
华尔街作为政治问题久已不被提起。就连美国的老左派都早已停止攻击华尔街。“华尔街的走狗”是一个会惹来嘲笑的说法,还不如说“蒙特卡罗的走狗”。随着企业和联邦政府的影响力和势力越来越大,华尔街逐渐变成没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设施。新右派干脆忽视华尔街的影响,只是在1967年,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同他的雅皮士朋友突发奇想地从观光走廊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几个月后,交易所的管理层对雅皮士做出反应—在观光走廊周围安装防弹玻璃,意思似乎是,他们把扔进去的美钞当做致命的武器。(也许,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的。)简而言之,有人对华尔街进行了嘲讽,而华尔街大张旗鼓地接受了它。但嘲讽其实并不是指向华尔街的,华尔街已经成为商业化美国的方便的代名词。难怪霍夫曼得意地说:“向股票交易所场内扔钱是很纯粹的信息,意思不言自明。它比成百上千的反资本主义小册子或文章表达的含义更丰富。”那些防弹玻璃多么郑重地为这一信息画上了着重号啊!鄙视傻瓜的华尔街这次被耍了。
第一章 戏剧高潮(4)
在暴风骤雨般的1967年和1968年,一切看上去都在瓦解—全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美元在巴黎不能兑换的地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刺,芝加哥民主党大会发生丑闻,学生骚乱逐步升温—愚蠢的股票市场却一路走高,毫无顾忌地上涨,似乎一切都好,或者一切肯定会变好,就像7月无忧无虑的日本金龟子。或者说,像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享受最后的晚餐。人们不禁要问:精明的华尔街难道对现实发生的事毫无察觉吗?
除此以外,难道华尔街不正生动地象征和体现了美国人刚刚开始学会重新审视的(即使不是排斥的)一切价值观吗?—新教徒式的勤勉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中心论和拜金主义。回想起来,华尔街不正是广泛遭到质疑的旧日美国的简化和现代化版本吗?而旧美国与正努力成形的新美国毫无关系甚至格格不入。
当然,华尔街声称自己比以往更能代表美国。即使在1929年经济繁荣的顶峰,华尔街也只是老实地承认,只有400万或500万美国人参与股票市场。1970年夏天,纽约股票交易所骄傲地公布了一项调查,其结果表明美国当时有超过3 000万股民。“人民资本主义”已经到来,有数字为证。但在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方面,1970年的股票市场并不比1929年更贴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