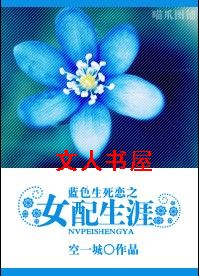蓝色妖姬-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东方鸿飞,不要躲躲闪闪的。”说着大踏步往前走,行出十数步却不见了鬼影。警长正暗赞劫路人卓绝的换位轻功,不料后脑生风,他本能地一蹲身,有个物件擦着头皮掠过,轮辘半天才停下来。警长用眼去辨辨,是个骷髅。刚要转身,那鬼风般地飘到面前,伸手去抓警长的喉咙,速度如风驰电掣。警长急闪,飞脚去踢鬼的横胯,鬼的身形一晃,用手一抄,抓住警长的脚,顺手牵羊地把他扔出数米远。
“好身手。”警长暗说,从地上弹跳起来,见鬼扑上,就地一滚,打起地躺拳来,双腿代替两手搏击。他先是以守为主,如条扭动的巨蟒护住洞|穴,利用间暇,看出对方用的是八卦拳,虽极力掩饰,但走的是乾、坤、坎、离……方位。警长重振雄威,长呼一声高起,把“燕青拳”打得如急风暴雨、漫天飞花。那鬼也不示弱,一掌接一掌地直劈下来。渐渐地两人都发出较重的呼吸声,警长暗想:这不是一种莫名其妙地较量吗?一分神,脸上便挨了一掌,不轻不重却火辣辣的疼痛。警长又想:如是生死相拼,这一掌必把自己打得口鼻喷血。再分神,第二掌又飞落下来,警长使出“平空抓燕”一招,牢牢地逮住鬼的手腕,往前一带,鬼脸便抵住自己的下额,一股温热、馨香的气息直喷脸上。他立刻想起“蓝宝珠”来,手一松,鬼身打个旋儿,腕子一抖,又打着警长一掌。东方鸿飞身体往后一仰,实实在在地摔在地上,见鬼跳过,身子如卷帘般翻过,用手去抓鬼的双裆。手刚触到鬼的胯下时,鬼便“唉哟”一声,刚要后蹿,身体却被东方鸿飞搂住,说:“朋友,这招叫‘浪子无形’。”双臂如铁箍儿围住木桶。那鬼也不再打了,只是极力地挣扎,但力量明显地稍逊一筹。警长感到鬼的身体温香、柔软,心族一动,竟用牙齿将纸面具扯下来,正是蓝宝珠,瞪圆一对怒目,尖声喊:“放开我!”
警长的双臂一减力,宝珠泥鳅般从他怀里滑出来,重重一掌打在东方鸿飞脸上,血顿时自嘴角淌下。“轻薄小子!”她举手再打,见东方鸿飞毫不抵抗地站着,便收回手,骂道:“你竟敢侮辱我,混账东西!”
“宝珠。”东方鸿飞用衣袖擦着血说,“我去找你,想不到你在这里装神弄鬼。”
“我用得着你找吗?”她怒气咻咻地转过身去。
“你不是走了?”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走不走关你啥事。”她说着,猛然转身,高喊:“看镖!”
一道蓝影直奔警长面门飞来。东方鸿飞一把接住,原是块蓝缎子手帕。他知道是给自己擦血的,忙捂住嘴角,感到滑腻腻的一股幽香。
望着伫立月光下的倩影,东方鸿飞对宝珠升发出一种由衷的怜爱。知道她全部窥探出自己和洪英的情形,心中不是嫉恨而是欢愉。警长突然呻吟起来,说:“我的门牙掉了。”
“你说啥?”宝珠扭过身,看到他手捧着手帕,一副忍痛的姿态。忙走过来,语调里蕴含着关切,轻声问:“真的?”显现出女儿的柔态。
东方鸿飞笑起来,目光显得狡黠。蓝宝珠又想气恼地转过身,但看到他的腮确实肿胀得厉害,本想安慰,但又不太情愿,仍然强辞夺理地说:“你跟着我干啥?”
“宝珠,”东方鸿飞上前一步,激动地说:“我的心你该是知道的了。”忘情地握住她的手,感到她温热的小手沁出细汗,“你不也在这‘鬼街’等着我了么?”
“鸿飞兄,”篮宝珠抽出被他持握住的手,两只眼睛亮得像注入水银,神情若定地说:“不错,你与洪英肉麻的情景我都偷看去了,按理说,我不该看这种……
可我又不能不看,你我结拜一场,蓝宝珠容不得有禽兽之行的义兄。我打灭蜡烛,实在是救了你。“”宝珠,洪英是我的婶娘,鸿飞不敢有乱人伦,再说,我,我已经有了……未婚妻。“
“是啥人?”她的声音有点儿微颤。
“宝珠,你何必明知故问?”他又上前一步,充满期待的希望说:“我和婶娘的谈话你不是已听去了吗?”
“你明明知道我在外面,能不作场戏骗人吗?”
“你真是强辞夺理。我即使知道你窃听于窗外,但我在臂上刺字时,你还没来啊!我纵然会诸葛的马前课,也料想不到会自天而降的芳陈侠影啊!”
蓝宝珠面颊发热,知道是难以解释自己跟踪他的用意,“鬼街”做鬼更难辨明意图。想到滦河畔勃然而去,用石打鸡、还枪、留柬,但又不愿就此远走高飞;跑到人家去窥听偷看婶侄秘事,身不由己地飞石打灯,听到他的呼声,因心情烦乱竟踩动屋瓦;到坟地戴上面具等候,又唯恐他不来,或不走此路……她为自己所作所为而困惑不理解,但又像鬼使神差。
当洪英那妖媚的女子扑到他怀内,她的心房便颤抖;洪英用两片红唇发疯似地在他脸上吸吮、磨擦时,无名的嫉恨变成狂怒,恨不得宰了那不懂廉耻的婶娘,她怕他把持不住而倒在红裙下,那样,说不准几粒石子便把他的双眼打瞎。她感到双腿发软,不愿再看屋内可怖的情形,飞石打灭蜡烛。室内一团漆黑后,她攀上屋顶,盼他出来,更盼他盲目地寻找自己。她扮鬼恐吓他并交起手来,是被一种酸溜溜的心情所驱使,恨不得痛殴东方鸿飞一顿,以渲泄积愤,但又不忍下重手,而他也没使出致命毒招。
“我知道你刺的是啥?”语调仍然冰冷。
东方鸿飞知道,他向洪英出示臂膀时,婶娘只是默默地看,由于视线角度,窗外的宝珠是看不清的。当下脱掉长衫和上衣,把胳膊伸到宝珠眼前,一轮皓月下,那已结成血痴的字迹尚能辨认。
“你……你。”蓝宝珠目光中夹杂着诸种情感:激动、感慨、喜悦、惊慌和悲伤,不由得用手去抚摸,女儿的柔情油然而生,低低地问:“这要带一辈子了……”
她慢慢地埋下浓密的睫毛。
“宝珠,我的妻子若是他人,她容不得我了,因为她不姓蓝。”
东方鸿飞勇气倍增地攥住她发烫的手,另一只手掏出那把勃朗宁手枪,放进宝珠的掌心,说:“宝珠,收下吧,这是东方鸿飞的心,它伴随我几年了。”
宝珠没有拒绝,望着他燃烧的眼睛,胆怯地垂下头,终于把枪藏好;然后默默地看着,摸着腕上蓝色的玉镯。镯子在星月下闪着微弱的蓝晕,她慢慢用衣袖擦着,擦了很久,一狠心褪下来,说:“小时是臂镯,后来就成手镯了……是妈妈的。”
她似乎很艰难地递过去。
手镯带着温馨,东方鸿飞放在贴胸的衣兜内,轻轻揽住她的腰,说:“我俩定情鬼街,千千万万的鬼魂为媒,群星明月作证,自此生同衾而死共|穴……”宝珠被他轻搂着,头垂得很低,一声不吭,像个懦弱的女孩儿。粗豪、英武和刚烈的草莽女盗全然变了,变成了女儿的心,女儿的血,女儿的一片痴情。
东方鸿飞嗅着满头乌发的幽香;聆听着火烫烫躯体内心房急搏的声音;慢慢扳起那张俏脸,那双明媚、清澈如秋水的眼睛羞涩地闭上了,两瓣变得鲜亮、丰满起来的红唇如紧锁的门扉,灼热的气息都自鼻孔喷出。东方鸿飞轻轻唤声“宝珠”。
“我打疼了你。”她说,去摸他的脸。
警长双手按住宝珠的肩头,说:“宝珠,我明媒正娶你。穿上凤冠霞帔,坐着花轿,夫妻拜堂,我把你牵到洞房去……”
宝珠伸手捂住他的嘴,深情地说:“只要你真心爱我,就是在这片坟地成亲也没啥。戴凤冠、坐花轿,那八方庆贺、满堂欢喜的良辰美景我何尝不想?女儿家只有这一天是威风的。”她语声变得低沉下来,“可你是警,我是匪,是被四处缉捕捉拿的女强盗,是杀人不见血的蓝色妖姬。你看得起我,不嫌我的出身,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鸿飞哥,你发个誓吧。”
东方鸿飞冲动地拣过个骷髅,摆在一棵被雷火劈倒的树前,说:“有你先逝人作证,我东方鸿飞与蓝宝珠结为夫妻,我若半点有负于妻,就是这棵树的下场!”
蓝宝珠突然跪下来,说:“我不知道你是善人,还是恶人,但总是先逝为仙,死算是人的善终。我蓝宝珠自此退出江湖,要做个贤妻良母,凡事都听从丈夫的安排。”
警长把她扶起来,两人目光默默相视,然后紧紧地拥抱一起。不知过了多长时辰,宝珠扬起脸,看到乌云将月光遮住,羞涩地把头藏在警长胸前,声音细微如蚁地说:“你刚才想做啥?
……就做吧‘东方鸿飞轻吻着她,说:“我们回去,告诉你母亲,让她也高兴。”
一句话提醒了宝珠,她说:“你不提回去,我倒忘了,小娟姐今天夜里来。”
二人边走边谈地离开“鬼街”、因关系发生变化,宝珠对警长不再有任何隐瞒。
她说,小娟这几天是到河南找一个古董商鉴定《八骏图》的真伪,两人约好在祝村见面。
“《八骏图》到底被你们弄到手了。”
“刚才,我偷听了你洪英婶娘的话,她讲出了这张画未落我义父手以前的经过。”
宝珠若有沉思地说,“这张画好像是不祥之物,谁都不能长久地占为己有。”
“宝珠,今后你做如何打算呢?”
“我跟着你。夫唱妻随,哪有你听我的道理?”她把身体偎依过去,警长用手揽住她的腰肢,心里却有些不安:吕小娟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如说出醍醐旅社中的情形,宝珠必然视自己如玩弄女性的男子,不仅勃然而去,还会反目成仇。蓝色妖姬的朱唇不是随意可亲的,那芳香的舌齿可以变成杀人的利刃。
嗜血的毒芯。
()
“我想,”宝珠温柔地说,“把画让小娟姐带走,算是物归原主。咱俩无牵无挂,到南方去。去苏州,人们说那里比天堂还美。你舍得警长这顶乌纱吗?”
“我早就不想干啦!”警长说,又问:“画是从范文心手里弄到的?”
“你不愧是个大侦探。”她嫣然一笑,轻轻拉紧警长的衣领,“风凉了。吕师姐忍辱扮成妓女,冒牌混进万春院,一是要引诱范文心,探出画的秘密;二是摸清王德兴的底儿……”
“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扮成妓女……”警长摇着头,装成故意不理解的样子。
“当初,她的身子已经被人骗了。再说,这几年被她要过的男子不知有多少呢!
她说,我看上谁,就和谁相好,然后再把他杀掉,到头来,她一个也舍不得杀。如不是我心狠,她不仅白白让范文心占了便宜去,画也拿不到手。我不该暗地说她的坏话。她人虽风流,但心肠好。哎?先别走,我有话问你。“宝珠用双手摆正警长的脸,神情严峻地说:”小娟姐对我说,她喜欢你,是真的吗?“
东方鸿飞很困难地点了点头。
她又问:“你也喜欢她?”
“我只喜欢你。”
宝珠的两只明眸闪着火辣辣的光,逼间:“她亲了你,在万春楼,对吗?”
警长轻叹了一声,算是默认。
警长胆怯而心虚,他贴胸的衣兜里正放着宝珠的蓝镯和小娟赠送的戒指头发。
尽管他不爱小娟,但不愿绝情般地遗弃掉。自从“醍醐仙梦”后,每到孤寂时,鼻端常飘溢过女人的气味,一闭眼便是驱之不去的女人形体,那些移动的,迷惑人魂魄的东西。他自省,懂得了譬如破戒的僧侣,松动的堤坝,很难再固若金汤。若不是宝珠飞石打灭烛火,屈从于洪英是顺理成章的事;若不是和吕小娟狂荡过一次,也不致于对宝珠有轻狎的行止。好在宝珠不谙男女情事,而且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来说,惊恐的便是期待的,厌恶轻浮却不厌恶心爱人对自己轻浮。
“你想啥?”宝珠问。
“我想,”警长停顿片刻,“中山门和红房子那两起‘绑票’案是你们干的吗?”
东方鸿飞突然想起那两起悬案,钱虽送到了,可土匪还是撕了“肉票”,被绑儿童的眼睛都被剜了去。
“我们从不绑票,也轻易不杀人。”她语态很坚决,“我们只偷富豪,得到值钱的东西就送回奉天去,那里有我们十几个弟兄。”
“宝珠,以后不要干了,粗茶淡饭我养活你,咱们夫妻要活个清白。”
宝珠很温顺地把脸贴在警长胸前。数年风高月黑、江湖喋血的生涯使她心肠变成铁石,如今,被一股强大的柔情软化了,感情的洪波吞没了一个看破世情的女子。
没有不需要爱的女人,爱情对于女人来说譬如迷离多彩的梦幻。此刻,她依偎在东方鸿飞宽阔的胸膛,犹如何靠着面巨大的山屏,安稳、可靠,是终身的归宿,将永远地躺在上面去做甜美的梦。她草莽之气消除殆尽,温柔得像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