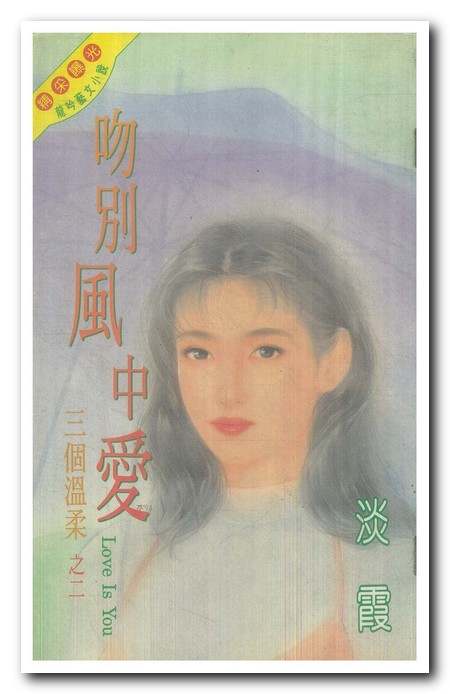the rainbow-虹(中文版)-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走在她身边,得不到满足的身体使他紧缩着自己的灵魂。难道她这么容易就获得胜利了吗?对他来说,现在丝毫没有他自己的幸福,而只有痛苦和心情混乱的愤怒。
现在正是盛夏,干草收获的季节已经快过去了。到星期六这工作便将完全结束。而斯克里本斯基到星期六也该走了,到那天,他一定得离开这里。
既然已经决定要走,他变得对她非常温柔,非常多情,他温柔地吻着她。那温柔、甜蜜、富有生意的亲昵使他们俩都为之沉醉了。
在他呆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等着她从学校里出来,随后带她一起去镇上吃茶。然后他弄了一辆小汽车开着送她回家。
坐在小汽车里,她更感到比什么时候都更为激动了。他为他自己的这最后一着也感到非常骄傲。他看到厄休拉在这充满浪漫情调的环境中已经像一团火似的燃烧起来了。她像一头小马一样怀着狂野的喜悦心情不停地喷着鼻子。
车子在拐角处歪了一下,厄休拉止不住倒在斯克里本斯基的身上。这接触更挑动了她对他的热情。一阵无法抑制的强烈的冲动使她抓住他的一只手,使劲捏在自己手里。他们彼此把手捏得那么紧,好像两个孩子一样。
微风吹在厄休拉的脸上,车轮掀起了一阵阵柔和的四处乱飞的泥浆,田野上是一片青绿。这里那里,点缀着一堆堆新割的青草,在那边闪着银灰色光亮的天空之下,是一簇簇的树丛。
一种新的烦恼的意识使她更紧地抓住了他的手。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话,却只是悲伤地紧握着手,彼此把闪着光亮的脸转向一边。
每过一阵,那车子总摇摆着使她一下子倒在他身上。他们一直就等待着这种使他们两人互相贴近的时刻来临。而他们外表上却一声不响地望着窗外。
她看着外边她所熟悉的田野在眼前飞过。可是现在,这已不是她所熟悉的田野了,这是一片神话世界。在那芳草萋萋的小山上立着的正是毒芹石。在这潮湿的盛夏的夜晚,在这神话般的世界中,它看上去是那么离奇那么遥远,远处几只乌鸦从树丛中飞了出来。
啊,她和斯克里本斯基为什么不可以下车去,走到那从来没有人来过的为魔法所迷的世界中去?那样,他们就会变成为魔法所迷的人,他们就可以抛开自己呆笨的旧的自我。她为什么不可以到那里去,到那银灰色的多变的天空下,到群鸦来往如梭的小山坡上去游逛一番!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到那潮润的草堆中去走一走,闻一闻黄昏的气息,到那忍冬在凄清的晚风中散发着芬芳的树林中去闲步一回。在那里,你只要偶尔碰一下树枝就会有一阵清冷的露滴撒在你脸上。
可是她却同他紧挨着呆在车子里,疾风吹过她仰起的热切的脸,把她的头发吹向脑后。他转过头来看着她,看着她那仿佛雕刻而成的光洁的脸;她的被风吹向后面的头发以及她的高扬起的尖鼻子。
面对着她这样一个敏捷清爽的处女,这对他完全是一种痛苦。他真想把自己弄死,然后把他的可厌的尸体抛在她脚下。一种急于想转身走开的愿望使他感到无比痛苦。
她忽然看了他一眼。他似乎正对着她趴伏着,准备往前跳,他似乎正来回闪躲,惟恐被人打着。可是忽然间看到她闪光的眼睛和发亮的脸,他的表情立即改变了,他又对她发出了那种毫无顾忌的大笑。她在无比的欢乐中使劲捏着他的手。他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了。她猛地一低头,在他手上吻了一下,她低下头去,怀着无限崇敬,用嘴亲吻着他的手。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可是他仍然显得很安静,他一动也不动。
她抬起头来,他们现在正摇晃着朝科西泽前进。斯克里本斯基马上要离开她了。可是他们似乎处于魔法的世界中;她的杯子里正斟满了幸福的美酒,她的眼睛只顾得上闪闪发亮了。
他敲敲玻璃,对那个开车的人讲了几句话。汽车在紫杉树下停了下来,她向他伸过手去,像一个女学生一样天真而简短地说了声再见。当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离开的时候,她的脸显得那么光彩夺目,对于他这时坐车离开的事她根本没有在意,无限的狂喜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心。她并没有看见他离开,因为她心中充满了光明,那也就是他本人。她的内心既然完全为他的惊人的光明所照亮,那她又怎么会想念他呢?
回到卧室以后,她在一种庄严宏伟的痛苦中挥动着自己的胳膊。噢,这是她已经改变形象的自我,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了。她要把自己抛进那暗藏着的光明中去。那光明就在那里,它就在那里,只要她能够走过去就行了。
可是,第二天她知道他已经走了。她的光辉的思想已经部分消失了———可是始终没有完全逃出她的记忆。那一切都太真实了。可是那一切现在都已经过去,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哀伤。一种更深刻的怀念占据了她的心,形成一种新的保留。
她尽量逃避新的接触和问题。她非常骄傲,可是也非常孩子气,非常敏感。噢,谁也别想再碰碰她!
一个人到处奔跑,她倒感到更为幸福。啊,从那些小胡同里跑过,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可又仍然和它们在一起。一个人能这样单独和自己的一切财富同在,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假期来临了,她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她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到处奔跑,有时在花园里松鼠出没的地方坐一阵,有时在长满小树丛的小山上躺一会儿,那里小鸟依人———常落在离她很近的地方———那么地近。或者碰上下雨天,她就跑到沼泽农庄去,拿着一本书躲在堆干草的阁楼上读。
她老是梦见他,有时梦境十分明确,可是在梦到最快乐的时候,那梦境总变得模模糊糊了。他决定着她梦境中的热情的色调,他是在她的梦境中跳动的血液。
当她不十分痛快,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她老是想念着他的外表,他的衣服和他给她的那些带军团标记的钮扣。再不然,她就试着猜想他在军营中的生活。或者假想当她出现在他眼前时,她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的生日是在八月里,她花了不少时间给他做了一个蛋糕。她感到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如果不给他送点礼物,那就显得太无礼了。
他们之间的通信很简单,大部分不过彼此寄几张明信片,而且也不很经常。可这一次要送生日蛋糕,她必须写一封信。
亲爱的安东。我想完全是为了让你过生日,阳光今天又普照大地了。
这蛋糕是我亲手做的,希望你长命百岁。如果味道不好就不要吃它,妈妈希望你在有便的时候前来看我们。
我是
你的忠实的朋友
厄休拉·布兰文
甚至给他写信,她也觉得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因为不管怎么说,写在纸上的字都是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
晴和的天气一直继续下去,收割机从早到晚发出低沉的哒哒声在田野里来回走动。她收到了斯克里本斯基的回信,他现在正出公差,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农村工作。他现在已是一支野战部队的少尉。他马上可以有几天假期,已决定到沼泽农庄来参加弗雷德的婚礼。
弗雷德·布兰文,在这次玉米收获季节过去后,就准备和伊尔克斯顿的一位小学校长结婚。
这次玉米收获结束的时候,正赶上一个一片青绿和金黄的甜蜜的秋天。在厄休拉看来,这简直仿佛是世界已经展开了它最柔和、最纯洁的花朵,它的菊苣花和它的番红花。天空蔚蓝而宁静,竹篱边黄色的树叶仿佛是自由游荡的花朵,摇摆在行人的脚下,放出一种直透入她的心灵,简直让人难以忍受的充满激情的音乐。这秋天的气息,在她的感觉中简直像盛夏的疯狂。她像一个受惊的山妖,从那一朵朵小小的野菊花边逃开,那晶亮的黄色的小菊花散发出无比强烈的气息,使她如醉如痴,她的两脚止不住战栗了。
接着,她看到了她的汤姆舅舅,他总是像图画中的酒神一样显得玩世不恭。他准备举行一次热闹的婚礼,他准备大摆一次酒宴,既作为庆丰收的晚餐,也作为婚礼的筵席:他们准备在家门口搭起一个帐篷,雇来供跳舞的乐队,在户外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
弗雷德对这事还有些犹豫,可是汤姆一定要这么办。另外还有那个既聪明又漂亮的新娘子洛娜,她也要求举行一次盛大的欢乐的宴会,这样才能适合她有教养的胃口。她曾在索尔兹伯里上过教师训练班,知道许多民歌,还会跳莫利斯舞。
因此,在汤姆·布兰文的指导下,准备工作早已在进行了。家门口巨大的帐篷已经搭起来,两堆巨大的篝火也已准备好了。乐队已经雇下,酒席也已经在准备之中。
斯克里本斯基是一定会来的,他准备在那天早上来到。厄休拉穿了一身用柔软的绉纱做的白色的新衣服,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她喜欢穿白色的衣服。配上她的黑色头发和金黄色的皮肤,她看起来很像南部的女孩子,或者更像热带姑娘,像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全身没有任何鲜艳的东西。
那天,她准备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止不住心里有点发怵。她要去充当女傧相。斯克里本斯基要等到那天下午才能抵达。
婚礼定在下午两点。当迎亲的队伍回到家来的时候,斯克里本斯基正站在沼泽农庄的客厅里。他从窗户里看见汤姆·布兰文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上衣,白色的裤子和白色的鞋罩,用胳膊挽着厄休拉大笑着从花园里的小道走过来。汤姆将是婚礼上的男傧相,汤姆·布兰文脸色像女人一样娇嫩,黑色的眼睛,黑黑的剪得很短的胡须,看上去真是一表人材。但是尽管他那么美,你从他身上总会感觉到粗野和淫荡的气息;他那样子很奇怪的像野兽一样的鼻孔使劲大张着,他那匀称的光着的脑袋看上去简直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的头前部完全光秃秃的,让人对那圆圆的脑袋一览无遗。
斯克里本斯基先看见的倒是那个男人而不是那个女人。她显得光彩夺目,仍带着她每次和她的汤姆舅舅在一块儿时必然会表现出来的离奇的,难以说明的,心不在焉的活泼神态。
可是她一遇见斯克里本斯基,那一切便都消失了。她现在所看到的只是那个像命运一样难以猜测的那个瘦长的,始终不变的青年在那里等待着她。她仿佛已无法再抓住他。他那满不在乎而又显得粗暴的神态使他看上去既充满了男人气派而又很有些洋气。可是他的脸仍是那么平静、柔和和难以理解。她和他握了握手,她的声音简直像刚被黎明惊醒的小鸟一样。
“举行一次盛大的婚礼,”她大声说,“不是十分有趣吗?”
在她那深黑色的头发上,可以看到几星彩色的纸屑。
他这时又感到心里一阵混乱,仿佛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而且变得迷迷糊糊不明所以了。可是他却希望自己非常坚强,具有男人气概,更粗暴一些。他这时走过来陪伴着她。
屋里摆着简单的茶点,客人们四下里随便活动着。真正的宴会要等到晚上才开始。厄休拉和斯克里本斯基一道走出去,穿过稻场走到田野里,一直走上了运河边的堤坝。
他们走过的新的玉米堆十分高大,显出一派金黄的颜色。一群白鹅在他们走过的时候大声叫喊着表示抗议。厄休拉感到自己像一团白色的绒毛一样轻快。斯克里本斯基神思恍惚地跟在她身边,他已抛弃了他的旧的形式,现在,另一个灰色的模糊的自我像一个蓓蕾展开了自己的花瓣。他们小声谈着话,自然是谈情说爱。
运河中蓝色的水流在充满秋色的两岸中轻柔地向前流动,流向一座青绿的小山。运河的左边是那繁忙的黑色的矿坑、铁路,和那在小山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城镇,而君临这一切之上的更有那座教堂。教堂钟楼上白色的圆形的钟在落日的余晖中清晰可见。
厄休拉感觉到那条路,穿过那阴森、诱人的混乱的城镇,便是通往伦敦的大道了。在运河的另一边则是一片青绿的沼泽地上的秋色,和沿河曲折成行的白桤木。再往远去,便是一片望不尽的刚收割过的庄稼地。那边,黄昏的清光是那么柔和,甚至一只红嘴鸥也仿佛在无限凄凉中拍打着自己的翅膀。
厄休拉和安东·斯克里本斯基沿着运河边的堤埂走着。竹篱上的草莓在片片绿叶之上已露出了鲜红的颜色。黄昏的清光、孤单的红嘴鸥的盘旋,微弱的鸟声似乎正在和煤坑那边传来的嘈杂声,以及对面城镇上的阴森的烟雾弥漫的紧张生活相呼应。他们俩沿着那绿色的水道走着,水底反映出一抹蓝天。
厄休拉心想,他现在看来是多么漂亮啊,特别是他的手和脸,因为太阳暴晒,泛起的那一片红色。他在对她讲着,他怎么学会钉马掌,和怎样挑选适合于屠宰的牛羊的。
“你愿意当兵吗?”她问道。
“我还说不上真是一个军人。”他回答说。
“可是你所干的事情都是为战争服务的。


![[继承者们]rachel的逆袭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3/1383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