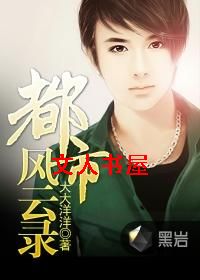七院诡案录-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我父母死后,秋宫鹿的目标就只有我了。就好像原来三个鱼饵,谁也不知道鱼会咬哪个钩。可提前将两个鱼饵扔进水里喂鱼,那么剩下的那个鱼钩,就是唯一能钓到鱼的。所有人只要等在这个鱼钩旁边,按照动物的本能去推断鱼咬钩时间,就能轻而易举地抓到这条鱼。
“那……那为什么……不是其他人?”
或许是由于身体虚弱神志恍惚,我突然之间再也无法忍耐了。秋宫鹿死了,积蓄已久的恨意突然之间没有了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们。
——为什么是我父母,不是其他人?既然能预见到,为什么不让灾害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转移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不知道的人,让他在角落静悄悄地死,别让我知道!
但一直以来,理智都压制着这个可怕的念头。我告诉自己,别人也是人,和父母一样,我不能那么自私。
而到这一步,我已经快要被自己的理智逼疯了。我必须要找一个仇恨的转移对象,至少去恨一个人,让这个情绪能释放出去。
我死死抓着昆麒麟,终于没能再忍住眼泪。而接下来他说的话,让我彻底坠入冰窖。
“丘荻,对于乐阳而言,你和你的父母没有分别。如果不是你的父母,那就是你和你妈妈,或者你和你爸爸……无论如何,他的决策是消耗最少的,乐阳手里只有一张叫做唐幼明的王牌,他只能用这张王牌去保护一个人。假设死的不是你父母,那么今天,死的就是你。”他看着我的眼睛,想将我带回病床上。我已经彻底没有力气了,只能任由他拖回去,“——在乐阳的计划里如果必定会死两个人,那我们只能庆幸,那两个人不是我们自己。”
当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马路对面穿着白色毛衣的青年,那么温柔地笑着。我甚至真的以为他就是昆慎之了,是那个昆麒麟口中“没有人比他更好”的师父——可他不是。
他说想要直接找出主谋,于是秋宫鹿和昆门鬼都被他找出了,代价呢?代价是我的父母。这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根本不算什么值得一提的代价。对于乐阳而言,死的是我父母还是我都一样,没有任何差别。
“很多事情……已经够了。丘荻,你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秋宫鹿死了,你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不要再管这些事情。甚至……甚至你想和我们彻底撇清关系都可以。”他说,“到此为止,昆门鬼现身,无论那是不是真正的昆门鬼,这些事情对你而言都太过危险了——你可以出国去继续当一个医生,离七院离上海越远越好。”
“……你是什么意思?”
“你伤成这样,只有我一个人来看你了。你还没有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的眼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挣扎着,却转而消逝,“……你自己调侃自己的那一句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根本不是调侃。你身边只有我了,而我是你全部的危险来源。”
——我看着他,寂静的病房里,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和这个人相距那么远——他在赶我走。我失去了一切,现在身边只有他了,而他居然在赶我走?!
我连恨的对象都没有了,现在他告诉我,我最后可以当做是依靠的人,在赶我走。
在这种撕心裂肺一样的痛苦里,我忽然明白叶月潭说的话了——我在依赖昆麒麟,当现在的自己离开了他之后,我很可能会活不下去。这种单方面的共生关系开始崩溃了,而且永远不可能修补。
这种感觉,可能就是所谓心死。
“把那几本书给我吧。你找到的东西都给我,然后你搬出去,回到你该过的生活。”他说,“秋宫鹿死了,结束了,你不能再干涉道界的事情了。”
我呆呆地听着他说,睁大了眼睛,难以置信从这张嘴里说出的话。
……那我呢?
我……也死了啊。
——自己突然不可遏止地笑了,笑得很剧烈,连伤口都绷裂了,白色纱布里面渗了血。他想抱住我,却生生停在床边,没有过来碰我一下。昆麒麟只是这样看着我笑,什么都没有说。
到现在为止,他让我退出。而我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付出了那么多代价,换到的只是这一个轻描淡写的结局?
我挣扎着要从床上下去,扯下了点滴针。针尖逆着在皮肤上拉出了一道很长的伤口,血流如注——但无所谓,这么点血根本死不了人。我扶着墙跌跌撞撞往外走,在门柜里拿了自己的包,掏出那两本书,扔在他脚前。
他问你要去哪?我说北京。
去北京,找陈叔和余棠。天大地大,我有的是地方可以去。
这一次他终于坐不住了,冲过来抓住我,想将我直接抱回去。我死死抓住门框不松手,纱布早就掉了,血把病员服染得艳红。这个情景其实挺可笑的,我也确实笑了,笑得停不下来,努力想挣脱他。就在这时,门口响起一声惊呼,“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我们都看向那里——那个人穿着一件灰色呢子风衣,藏青色围巾,正惊愕地看着屋里这两个拉扯在一起的。我也没料到会是他,尴尬地松了手,被昆麒麟一把拽了回去扔回床上。
“血!你身上都是……天啊,我知道你受伤了,没想到那么重……不过你们都在做什么?昆先生你疯了?”叶月潭把包一扔,也跑到床边,先按了铃。刚才挣扎的时候自己还没觉得痛,现在才感到撕裂的伤口那里刺刺的剧痛,“这到底怎么了?”
“他才疯了!”昆麒麟看着刚才胳膊上被我抓破的伤口,语气冷冷的,“他想就这样去北京。”
“丘荻,你去北京做什么?”
“你别问。”
“我是他医生,我必须要问。”他直接将昆麒麟拽出了病房,我听见叶月潭说,“看你们这幅样子,这段时间,昆先生最好别再来了。”
第94章 病案47
医生过来替我重新换了药,喷好了凝胶。伤口血也开始止住了,但我整个人都极度疲惫,不想说话。点滴重新挂上了,叶月潭调了一下滴速,坐在我床边。
“我和导师去北京看了一个病人。他的情况比你糟糕多了,真的。”他摸摸我额头,自己现在有点热度,估计是感染的关系。“不过也挺过来了。你不该和昆麒麟走得太近。你有女友对吗?而且是个很久不见面的?”
“对……”
“去见见她吧。你知道她在哪吗?”
我用手背盖着眼睛,努力回想——小顾很多年没和我联系,她家没有其他的亲戚,也没有什么能投靠的人了,而且她的家庭情况,不太可能换房子,应该还在原先的城乡结合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市中心有一部直达车。
“你去看看她。哪怕找不到人,这样也会对你有些好处。”他说,“暂时别去和昆麒麟接触,换一个人试试。原本就是恋人的话,关系回温很快?”
他这句话让我怔了怔——对啊,小顾。
我还有小顾。现在我们都一样了,没有了家人。而想起小顾,我又有了一个念头。
“我的女朋友……她有抑郁症。如果我去见她,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这也行。如果她要求我治疗……”
“费用我会付的。”我又想坐起来。生物凝胶在伤口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膜,暂时止住了血。现在我迫不及待想见见小顾,再不见到她,自己一定会疯的,“拜托你陪我一起去……”
“等你伤好了就去。”叶月潭点点头,“而且你这样的情况,我会想办法让导师也来看一下。这两天我都会陪着你,当然如果你不需要……”
“谢谢,还是很需要的。”我松了一口气。自己现在真的需要一个人待在边上,他能这样真是太好了。于是叶月潭先回去拿了东西,这几天他二十四小时陪护,要拿换洗衣物和一些工作用的文件,连办公室一起挪过来。
大概下午三点,叶月潭重新来了医院。手机不断接到昆麒麟的电话和短信,我看都没有看,后来干脆直接把这个人拉黑了。私营医院的VIP病房就和一个宾馆一样,非常干净整洁,而且还有陪护睡的小隔间。叶月潭将文书和电脑放在旁边书桌上,就在我边上办公。晚上他出去买晚饭,我觉得无聊,叶月潭就让我在书册堆里找想看的书,看完了还回去就行。
晚上伤口已经不太疼了,我能借着架子走几步。叶医生的书堆很整齐,大多都是专业书籍,我想翻一本杂志什么的看看,结果从书堆里落出了一个透明文件袋。
原本是想把它塞回去的,可是当看到第一张纸上的名字时,我为上面的内容愣了一下。
病案47:余椒
反应型抑郁症III
主治医师是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名字,张究学,记录员是叶月潭。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叶医生请了假,说是陪他导师去北京看一个老病人——
余椒这个名字不常见,如果是三少的话,这份病案很可能记载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我实在太好奇了,余三少这个人简直就是个超大号谜团,而且必须去了解他,因为我下一步计划去北京找余棠,和他们一起继续查下去,知道越多关于余椒的事情,对我就越有利。
我只是犹豫了那么一会,就拿起了这个文件袋,然后打电话给了出去买晚饭的叶月潭,告诉他,我突然很想吃莲花路一家老西餐厅的奶汁烤菜和老大房鲜肉月饼。我特意挑了两个离这里比较远的地方,等他回来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很仔细地将这份文件看完。
这份东西是病案,但是没有医院的病案那么规整,里面有手写笔记和多处修改。而且在一开头是一份问答。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地点是北京某个医院的治疗室。
病人信息:余椒,1979…6…17,现住地:北京。未婚。
张:请问你的名字?
余:余椒。
张:昨晚睡得好吗?王先生告诉我,你晚上还是在做噩梦。
余:不好。
张:做了什么梦,可以和我说说吗?
余:(转过了头)……
张:可以说吗。
余:没什么。
(本人给他看了几张照片,一共三张,是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与父亲)
张:看得清吗?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好。
余:……
(第一张是他父亲的照片,病人并没有什么反应)
(第二张是他的大哥。病人表示不想再看,翻过了照片)
余:我不想见他们。
(病人的情绪明显开始焦躁,出现了抑郁症典型反应)
张:你知道他们在哪吗?他们失踪了。
余:你也听了那些传言吗?说我杀了他们。
张:你可以不说。这是你的权力。
余:算了,就是我杀的。
张:余椒,你要知道,如果你在记录中这样说,我就必须报警。
余:随便你。
张:你这样会让我很为难,可以修改一下说法吗?
余:我没有动他们。
张:很好。我们可以继续了。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你在哪,还记得吗?
余:忘了。去问兆哥儿吧。我累了。
(病人已经出现厌烦情绪,对话可能会陷入僵局,我试着用王兆的事情来引导他的情绪,对于余椒来说,王兆是一个突破口,联系到他们之前做的那些事,这两个人很可能形成过一种隐性、双向的共生关系)
——以下对话为十五分钟后开始。
张:可以开始了吗?你刚才休息时,我听见你在电话里让人准备北京饭店的宴会厅。这个宴会厅是做什么用的?
余:吃饭用的。
张:嗯,为什么事情聚在一起吃饭?和谁?
余:兆哥儿生日。只有我和他去。
张:一个宴会厅只有你们两个吗?
余:只有我们俩。如果你想来也可以。
张:我很乐意去。你们都没有其他朋友?
余:我们不需要其他人。
(本人希望在此次对话后与王兆先生进行确认。因为病人对人有很重的抵触情绪,在此之前也有以故意透露不实情况来干扰本人判断的先例)
张:那么那些人呢?我听说,你最近和两名上海来的宗教人员走得很近。那是你的朋……
余:谁告诉你的?!
(病人情绪失控,十分激动,谈话不得不中止。他仍然与别人维持着相当远的安全距离)
……
后面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对话,比如他去和王兆确认谈话内容真伪、分析总结等。后面还有一张药单,我看了看,都是抗抑郁药物。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这份药单十分奢侈。
再往后翻,则是一些问诊记录。上面写了余椒从小到大的经历——和我所听说的没有任何差别,出生后被家人当做祥瑞,喜爱在乡下老宅中钻研古书,后来因为视力突发下降而回到了北京居住……可是这一整段都被医生用红笔划去,后面标注了四个字,“话不属实”。
也就是说,这一整段话,余椒全都说了谎。他为什么要说谎,这个人小时候究竟发生过什么?
接下来的一份文件才是真正让我惊讶的,因为谈话的对象是王兆,而且篇幅很长,时间是一九九六年,比余椒谈话记录要早两个月。
对话看起来是非常快的,我能看出王兆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因为记录里没有中断,而且里面的情况说的非常详细。
张:也就是说,王先生和病人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