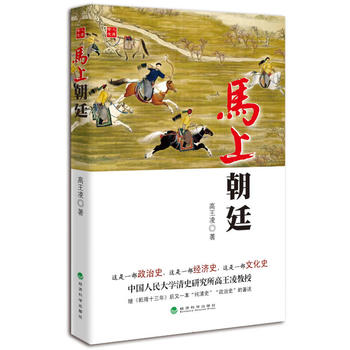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中必另有包藏祸心之人……安知其心不以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暗为将来引惑之计?其奸谋诡谲,所关不小。(42)
把它与剃髮一事联系起来。但皇上自己大概也有几分怀疑,这样“逆亿”是否不着边际了?(43)
同时,在办案中又发现,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一些“编造歌词”、“门墙书字”、“符咒”、“抄贴”,及种种“妖术”等神秘现象,本属不稽之说,不得不排除于侦讯之外,“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断不宜诧以为奇”。“叫魂”,难道不就属于这样一些“迹属微暧”,“不必过于诘问”之列么?(44)
如此说来,闹翻了天的割辫一案,竟是小事一桩!若有若无,似真似假,无法捉摸,无从下手,结果成为一个无法追查下去的案件,不得不适时中止,而不管它给皇上个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曾几何时,皇上却是那样的自信,是什么给了他这样一种自信呢?
那还是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于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遍布各地的教派遂被一网打尽。
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那么可依恃的(如“孙嘉淦伪稿案”实际上也没有侦破)。
无论是“叫魂”,还是“文字狱”一类的“政治罪”(政治案),或许都可以称为“非常规”的政治行为,在乾隆朝以后也都不再使用。例如,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再度出现过叫魂恐慌,但当局并未大做文章,事情很快也就无疾而终。(45)
但他目前还需要这些。
为什么又要采取和那样偏爱这些“非常规”的措施呢?这可能正如皇上所说:
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长治之视,必为根本切要之计。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46)
皇上为何要出以危言,说什么“朕之隐忧”?他说“持盈守成,艰于创业”,又说“久安长治”,显然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持盈保泰”在这里,也未必是一个保守消极的想法。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为此,自乾隆初年以来,修订《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编纂刻印经书,考订礼乐,重修太学、文庙,从事各项大工程的建设(从城垣到河工、海塘),种种“一劳永逸”的提法,和以后的搜书编书……那一个不是为了后代的长久考虑呢!从另一方面说,又有几个臣工理解皇上的这番苦心?
18.政治案件
总的来说,乾隆三十年代是一个文字狱的“低潮”时期,除了“叫魂案”前后几年案件较多以外;而且,其中许多属于“诬陷”案件,亦多被查明。但到乾隆四十年代,直接跟大规模的搜书有关,文字狱又多了起来,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乾隆朝文字狱·四(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九年)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十一月,湖南发生益阳县书吏郭湘昭擅造匿名揭帖一案,其后研讯明确,系属畏刑诬认。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江苏华亭人蔡显负才不羁,刊刻所著《闲渔闲闲录》,对邑绅指斥甚多。群绅以其怨望讪谤欲行公举,蔡显惧祸,抱书向松江府自首,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其“存心诡诈,造作逆书,任意毁谤”,合依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上谕: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诧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有间。及细检各处,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则是有心隐约其辞,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该犯罪案所系“。六月,蔡显从宽斩决,长子蔡必照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原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于雍正九年吕留良案结案前,曾遵旨陈情,请释放吕留良。经督抚等审拟奏闻,奉旨:严加锁锢,永远监禁。迨至乾隆改元,蒙恩赦放。乾隆六年,齐周华离家历游各省,一度曾为谢济世入幕之宾。本年十月浙江巡抚至天台县盘查仓库,齐周华遮道控诉,告发其妻及堂弟、原任侍郎齐召南等。当即搜出齐所携书籍多种,以其怙恶不悛,如将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应照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十二月狱具,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齐式昕、式文,孙齐传绕、传荣等,俱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朱氏,妾丁氏,长媳奚氏,次媳吴氏,幼子齐传绚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案株连齐召南等名士二十余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齐周华逆词案株及物故已久的前工部侍郎李绂,二月,江西巡抚搜查其诗文集,具折参奏。上谕:“所奏未免过当。检阅各签,如李绂所作诗文,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欺人恶习,尚无悖谬讪谤实迹,即其与戴名世七夕同饮,原在戴名世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无足深究”。但“所有各项书本,板片,该抚可逐一查明,即行销毁”。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进呈《国朝诗别裁集》,以钱谦益冠卷首。谕以钱“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命撤去其诗。本年六月,又以钱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谕令各省督抚等将两书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悉数缴出,汇齐送京销毁。并著广为出示,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实开启是后延续十八九年查办禁书之序幕。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九月,张震南原以诗句狂诞发遣伊犁,复于戍所递呈献策,妄言滋事。法司拟照大逆律凌迟缘坐。上谕:核其词句,尚与悖逆者稍间。张震南著改为立斩,即于该处正法示众。
十一月,余朴以考职微员辄敢投递疏稿,擅陈时务,悠谬荒唐,诞妄滋事,上谕:但阅其所言“通选法”、“行均田”二事,不过穷极无聊,希冀得官,尚无悖逆不法之处。余朴著从宽改为应绞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三月,河南罗山县在籍革职知县查世柱私纂《全史辑略》四卷,后与革书李风仪因房产发生纠纷,李遂抱书出首。河南巡抚以逆案奏闻,及调阅所纂之书,不过“沿明季野史之陋”,“并未敢诋毁本朝,尚不至于大逆”。但将应禁之《全史辑略》藏匿不毁,且敢采辑成书,查世柱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福建闽县人游光辉遇卜人潘朝霖算命,潘言其命好,将来必发大运,遂与交好。此后潘另与他人交好,游以此怀忿,欲图陷害。九月途遇,即将潘拉回家内,买酒留饮,诱使其写一书札。十月福建按察使外出,游光辉拦舆递上潘朝霖所书“逆札”,诉称欲邀其入伙,前来出首。奏闻,以律载“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潘、游均应凌迟处死,其叔、弟、子俱应照律拟斩立决。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直隶盐山县童生王殉著书四本,欲明正《四书》大义。因《四书》内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心想“如今皇上是仁义之君”,所以将“夷狄”改为“义帝”,借此表白自己并无“悖障逆谤毁”之心。书成后,遣兄王琦至京在户部侍郎金简家投递字帖,奏闻,提解至京,以王殉“读书不就,遂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希图哄骗银钱,甚至敢于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尤为丧心病狂,情实可恶”,应照“造作妖书律”拟请旨即行正法。
19.山东王伦起事
乾隆号称“十全武功”,其中最著名的当首为“西师”(乾隆二十年),次为金川(乾隆十二年);而对缅甸的战事,从乾隆三十一年开始,到乾隆三十四年受到重挫,双方罢兵求和。对此,皇上很不甘心,筹划对缅进行一次新的打击。但大小金川硝烟突起,不得不再次用兵金川。不想乾隆三十九年,就在大金川战事方酣之际,晴天霹雳,山东发生民变,一连攻陷几座城池,这在乾隆朝还是从未有过之事。
山东起事的领袖王伦,据说貌魁岸,有智谋,素习炼气拳棒,善“邪术”。乾隆十六年入清水教,三十六年始借气功医病,广收教徒。按照“白莲教”教义,大劫(“末劫”即所谓“白阳劫”)在即,王伦被奉为率领教众“应劫”之“收元之主”。乾隆三十九年春夏,山东荒旱,收成歉薄,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民众蓄怨已深;会知县沈齐义等差人严拿邪教,——就在近几年时间里,有好几个教派已被政府整肃,(47)——王伦得到信息,遂扬言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定于八月二十八日半夜子时提前举事,并预言其时会有风雨。
至期,寿张、堂邑同时起事,寿张知县沈齐义被杀。适值风雨大作,众益信服,所过之处,附众甚多,寿张、堂邑、阳谷、临清一带聚集两千余人。随即陷阳谷,复克堂邑,破城之后,杀官劫库,开监放囚,声言“只杀官劫库,不杀百姓”。然皆弃而不守,因三处城垣低矮残损,意欲攻得临清州或东昌府等坚固城池,以安顿随营家属,并伺机进取直隶、京师。
是时,中原腹地自三藩乱后,承平已近百年,教军遽起,畿辅震动。朝廷一面派山东巡抚徐绩、布政使国泰带兵从东昌一路进发,兖州总兵惟一从东阿一路进发,会同剿捕,上谕:此案情罪甚为重大,即当按叛逆办理,非寻常纠众抗官可比,一经擒获到案,即应迅速审明,将为首者立时凌迟,其同恶相济之逆党亦即应斩决,必须多办数人,俾众共知儆戒!又对绿营放心不下,命大学士军机大臣舒赫德即速由天津驰往临清,并调派健锐、火器营二千名,前往山东会剿。并命直督周元理、豫抚何煟于毗连山东地方,江督高晋于徐州一带,调兵堵截。
九月中旬,王伦屯兵临清城南柳林,击退巡抚徐绩所提官兵,趁夜围攻临清新城,城上以劈山炮、佛郎机、过山乌轰击,王伦军伤亡惨重。乃率大队及车辆、妇女、辎重,移屯运河东岸旧城之内,其时附众不下万人。兖州总兵惟一、德州驻防城守尉格图肯率军与之交战于临清城外,败回东昌,寻以临阵退缩,被斩于军前。王伦乘势欲阻断漕运,派人抢夺粮船,搭建浮桥,并在浮桥两岸分守,堵截官兵。
九月底,各路官兵合围临清旧城,除有部分教军溃围逸出外,王伦等千余人俱在旧城内固守。临清旧城地势广阔,居民稠密,惟城墙塌毁已久,舒赫德分派各路官兵入旧城搜剿。城内所杀尸身,填塞街巷,人马行走,几无驻足之处。沿河一带,浮尸满岸,其巷内教军车辆,半皆焚毁。次日,官兵探知王伦在汪宅一间小楼之上,将其团团围住。王伦称“我宁可烧死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即自焚。据舒赫德奏报,“杀死贼众不下一二千人,其余活口并直隶、河南两省擒捉送到者一千七百八十八名,又自寿张、阳谷、堂邑三县解到临清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已随时讯问正法”,致有“多杀无辜”之讥。
王伦起事是乾隆朝历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所谓小,是因事件前后不过一月时间,动用兵力及帑银都不算多。比较金川,用兵几近十万,前后五年时间,花费七千余万两,实在就不算大。以致有的乾隆传记都未写入王伦事件。(48)所谓大,是因为这一件事的性质,致使许多史书把它当作了乾隆中、后期历史的分界线,或清代由盛入衰的转折点。(49)
至于王伦起事的“性质”,更是自是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事情发生之初,皇上曾下令追查,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