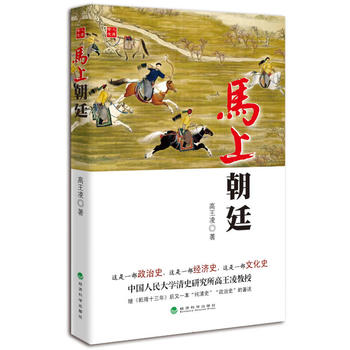���ϳ�͢(Ǭ¡�������ڶ���-�����)-��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¼䣬����ʱ������ʡ�и�ȡ�±�֮�£����������ܷá��þݳ����ر��ƣ��������Ժ��ݣ��������ޱ�����ߡ���������֮�ˣ����ò����������Ϣ��
�����Ȼ������������⣬��Ի��δ�أ����Խ�������ɽ����ֱ�������������б���֮�ˣ��ν��Ϸ�����Ү��������������β�����Ω�»���Ϊ��֮ªϰ������ʹ�ޡ�������ǣ�����֮���ӣ���7�����³��ĸ������ʣ�����ɽ����ֱ�������Ǿ㾭�����ư����������ʡתδ������һ������δ����ʵ���ţ�������ּ��ѯ�����Ķ�ʱ��������δ���ࡣ���Ǹö������ڵط������������ģ��������ţ���8��
�������³��ţ����Ͻ�һ��ʩѹ����һ��������㽭Ѳ���������µģ���������ʮ���մ��������������ʮ���գ���δ��ʵ���࣬�ⲻ�ɽ⡣�ط��д˵ȼ�ͽ����������ּѯ�ʣ����а켰���˰�ʵʼ����ʡ�����Ϣ��ѭ֮ϰ�������β����ơ���������ǰ��β��о��࣬����������跨������һһ��ϤѸ�����š������ǰ�ӻ����Ըɾ��壡��9��
����ͬ�գ��ּĽ���Ѳ���ñ����ͣ�ǰ�˼Ȳ���ʵ��棬���Ŵ�ѯ�ʣ��ֲ��������ţ�һζ�ӻ���ѭ��������β������࣬������跨�ü���������ɽ��ʡ�������ټ����Σ�����߮��֮���������������һ���о�ʵ���š������������ģ����Ǹø���ȡ���壬������Ϊ����Ҳ����10��
�������鵽����һ����ìͷ�ƺ��Ѳ�����ָ��л�а�������Ƕ��ŵط���Ա���ر��������Ķ��������ˡ��������ǣ����Ϻ����dzɼ����
�����ڸ���Ϣ����˵�Ƿ����ڻʵ������֮���һ���������⣬������ѧ�߿�������������ǽл갸���ص������ˡ��ڻ������ʡ����֮����ⳡ�������伤�ҳ̶ȿ��²���������˱�������11��
�������Եط���Ա���������స���Ȳ�ͬ����������Ҳ��ͬ���ض������ΰ��������ѹ��࣬���Ѳ�������Ӱȥ���٣�Ʈ������������ҥ�Դ��ţ�����������Ҳ����һ�㡰а�̡���������Թ̶�������������ϵ���෴������Ա����ǡ���кܴ������Ժ���ʱ�ԡ�
���������������ʾ������й�����һ���˿ڸ߶���������ᣬ�ӽл갸���漰�ġ��ﷸ���������и��ָ����ġ����˺�������ְҵ�ߣ���������ؤ��ɮ�ˣ��ر��Ǽ�����ؤ���η�ɮ�����������ʵ��Ķ����ˡ����������ߡ���Ϸ��֮�˵ȡ�Ҫ���ɷ�һһ����ν���ϼ��ѡ���12��
����������ܾ����������Щ���۰��շ��˿ڹ��ٶ�����ȴ�������֣�������û�������ַ���������������ݵ������������£�����ɮ����ʯ�������������ֻ��ط����ɷ��������������������������ݸ���ɮ���վ����չ�ͨ����ͨ��ȣ����ɸ���ʡ�ܷò钂���������ˣ���̨���ɷ����o��DZ��ɮ���в���أ��������ˣ���ʼ����ϸ�Ѳ飬�����ɷ����Ķ����ˣ����������û�˷����ģ�������ϵҪ�������壬��������Ҳ����������Ľ������ʱ�Ҳ����ɷ�����ֻ�ܽ���������ߣ�����Ԫ����Դ����Բ��ɮ����Ѻ���ʶԣ������Ż�ɽ����֮��Ԫ�����������û���Ԫһ�����Է���������
�����������������ٸ����������ģ�Ҳ��ֻ�����ױ����ƶ��ˡ���������˵���ط���˾��鱣�ף�����ʮ����һ��ͷ��ʮ����һ�׳���ʮ����һ����������ӡ���ƣ���д�������������������ҵ�����йʾ�Ǩ�Ƽ�������֮�ˣ���ʱ�ʱ����Ͼ��Ǽ��и��Ҹ�����ͷ�������ѵ����ɰ�ͼ������
������ˣ�����ָʾ�����ܶ�������ּ�������϶���Ա����ɽ�����ָ����ɮ�����13�����������������ա����ա��㽭��������ǰ��ָ�������������Ѱ�������������14��
������ϧ���ǣ����б����ƶȲ�û����ô���롣�����������ط��ٲ�����ʵ���У�һ����Ҫ��ԭ������Ǩ�ƴ��⣬�Լ����ƾ�Ӫÿ����ף����ز��������ײ飬������ѭ�����ɹ��ס���15����ƽ��֮��ν��鱣�ף�ȫ����Ӧ���£������Ծ��Ĵ��¡���16��
��������Ѳ���ñ�Ҳ����˵������ʡ����֮��������סַ�����������ڲ����ټ�����������������������סַ������17��������������Ȼ�����еı����ƶ�������ġ�
���������ɷ�������˸��ʼ����һ��ȷ�У���ʹ��������������ء����Ͼݸ�ʡ�า�������ͻ��˷������ʶ�����ƣ���������ж��ߣ���������Ӱ�졣���������֣���18��
��������Ѷ�У���ʱ�������ͽ����Ѷ��ֹ���跨����������ͽ�������������̼��±У������ɸ�������19���������ʶ��գ���δ��һʵ�����������ɷ����ƣ����ó���������������䱸�����̣����һ�������20���ںܶೡ�ϣ�ʵ�ʶ�������ʹ������Ѷ��
�����ڴ˰��У����ϻ�ʹ����һ����ͬѰ������������ָ��ר��ר�Ÿ����ر�����Щ������Ա�������������ɸ�ʡѲ�����ھ�ʦ���ɴ�ѧʿ��ͳѫ�����������ж��ࡢ��������Ӣ���ȣ����������ר�족��������ˣ������Լ�ҲҪ����һ�������Σ����Ŵ�����ﷸ���ͣ��Ⱥӣ����ڣ�����������ϸ��������21��
����Ϊ�û��ﷸ���ڴ���ר��֮�£�������Ա�ͣ�������Ҫ�������ɮ���ټ����أ����Ʒ����������㾡ƾ��������ڸ������ڳ�����ڼ��м����磬�����ֹ���Ժ֮����һ�����ķò飨��ʦ������22������ѡ���ۣ��������ͣ������ڷ�����Ժʳ��ס��֮�أ���ͷ�Ȼ���������������֮�ˣ��������ʣ�¶�������μ��������Ѳ飨ֱ��������23�����װ������ͬ���ۣ��β����ߣ����ڳ������μ���ɽƧ����һ������Ъ�꣬���������������ܷò飨�㽭������24�����ž���ּ��������һ���������������������ࡣ
�����ɴ˿������ڡ��лꡱһ�స������ʾ�����ģ���������ʵ�ֹ��ҵġ����뼯Ȩ���ʹ��ϵ��µġ�����һԪ�������������������������ף�����ͼ�Ǻ����Եġ����˵ʮ�����͵��й��Ѿ���ʼ���С��ִ���������25��������ص�����Ҳ��������������һ����ֹ��ǰ�ִ��Ĵ�ͳ���Ĵ�����
�����������£������ڿ�����������Ӻ����������˵��û�й�������һ���ϣ������ѳ�Խ�˻��桢�ʿ�����ϧ���ǣ���һ���뷨��ʵ����һ�뷨֮�䣬����һ���ľ��롣�ο�����Ŀ��Ҳ������ô��ȷ���أ�
���������º�谸�Ѿ���ɽ�������ա��㽭������ֱ������ʦ�����������ϣ��������ӵ����Ⱥӡ�ɽ���ȵأ�ÿʡ��������������ʮ�������ȡ������߶�ϵ����ͽ����������������������ƾ�ţ����淸ȴһ�������º��֣�����Ҳ�м��ֿ�ԭ֮�飬��Ϊ��Щ����������Ľ��������������ּѯ�ʣ�ɽ������跨���У�Ѳ�����Ẻ���ࣺ��δ���������й��¡������⾩��������ͬ�̲���Ѷ��������ʡ��ȡ���ʣ���ϵ������̱������������������������֣�������δƽ������26������ɮ���������Ǹ����������ϵ�����Ƹ������̱��ϡ���27���㽭�û�ɮ����Զ��������������գ��ַ�����������ҹ������������������С���28��
�����ر����ص��ǣ�ɽ��ʡ����ץ���������������͢�ºͽ����ӣ�����ָ֤��Ϊ��Ҫ�����㽭������ɮ����Ԫ����ʯ���������������������µ��ǣ����DZ��˸�����û�и�����ӣ���29����������ص������ˡ������ȥ�������ж����˱�ǣ��������30��
������˵�������Ѯ�����ϴ��Ⱥӻص����������������ϵذ䲼��ּ��
����͵���һ�£������᷸�⾩��Ѷ����������ͬ�̲�������ͳ��������Ϥ�������ʶ������ƣ�����η����ָ�ߡ��ɼ�����ʡ������ǰ�����������ں�ʵ������δ�ã�ͽʹ�����ij����������֣���������δ��Э���˰����ھ�����ӹ��졣��31��
������Ȼ�˰�ǰ��δ��ɱһ���ɷ������ڻ��Ͽ�����������ʡ��Ӹ�Ż�֮������˾��ȴ���ɲ���ʾ�ʹ������������ܶ��߽�������Ѳ�����¡�ǰ����Ѳ���ñ�������Ѳ�����ԡ��㽭Ѳ����ѧ����ɽ��Ѳ�����µȣ������ϼ��鴦��ɽ��Ѳ�����Ẻ������Ѳ�������ļ��̿����ۼ������ֱ��Բ���ʹ���������н���а켩����������֮���صȹ٣����Ž���ö�����һ��������ּ��ְ����32�����꣬����л갸ͬ�ڵ���һ������������һ����Ա�ܵ����������м�����ʮ�˸�֪�ء���ʮ����֪����ʮ�ĸ���̨����ʮ��������ʹ����ʮ�Ÿ�����ʹ����ʮ����Ѳ���Լ�ʮ�ĸ��ܶ�����33����ȷ����һ���������˶����ˡ�
�����л�һ��Ϊʲô��Ȼ��˲�����֮��������Ϊʲô��˹�������ּ����ӹ��족��
�����������ʣ��������л갸�У���ϯԭ����ʼ���վ��ǻʵ۱��ˡ����Եط���������ʩѹ�������룬����̱�ѵ�⣬��ͬһ��ӥ��ӵļ��٣����һ�����ⶼ��Ϊ���ĸ��˽�����ҲѺ���˻ʵ۵�����Ȩ������34������������������������������������Щ������˵����������Եĵط�������ͻ�������Եĸ�ʡ����ʵ��һ���ģ�����ֻ�����ڵ���Ĵ�С��ͬ���ѡ����Ƕ�û�а취��ȫ���������Ϲ��Լ�ͳϽ�ĵ�������������һ����������Ĵ������������Ĺ������⡣ʹ��һ���Ӳ嵽��һԪ����ʩ��������ʵ�����뼯Ȩ����Ȼ��һ������ջ�ȴ�������ס�
������������һЩ�뷨����Щ�뷨���ܾ���Ϊ�ǡ��顱�ģ�����ϧ�������ڡ��Ŵ����롰�ִ����Ľ���֮�䡣��Ӧ�Ľ��軹������������ʡ���ε�״��Ҳ�������ı䣬���ϵġ��ִ�����Ŭ����Ҳֻ�õ���Ϊֹ�ˡ���˭����������������ġ��������������ʲô�뷨��
���������ϳɼ����������ŭҲ�ɺ�ǡ���35�����������Ա�����в��ơ������ٴ�Ǭ¡ʮ�����������Ѿ�����һ��˼ά��ʽ����Ҳ���ڳ�Ϊ������������һ���������ࡣ
���������Dz����ڹ���������Ρ��л�Σ������ʹ��һ�֡����ƽ��յġ������˶��������ַ������������ţ�����������������36����ʵ���ط���Ա���²�����Ҫ�ͻ�������ʲô������Ȩ��������ν������ͨѶ��ϵ���ȣ����෴�����ǵ���Ϊ���ڻ�����ǰ����ԶΪ�����ģ���������Ҳ�����Լ��ġ�����Ϊ����
������ν��Ա�ġ�����Ϊ������Ի����Ӧ��Ϊ���������ܾ������¼���Ҫ�㣬��һ������Ҫ���̻���ʥ���������������硰������֮�£�����ʥ����ѵ�����꣬��Ϊ���У���ʤ��㤡�����37���������Ϳ������������ԣ������ա�����38����ñ�Ӵ��㣨�����ǶԻ��ϵ�ͻ�����롢С��������������Ҫ���ֳ�ʮ���ֵ���������ͬǬ¡ʮ���긵�㱼�������о�����������Ȼ��ҹ����һ�㣻��39����������Ҫ��ʵ��������ر����������ѣ���ֽ��㣬������������Ⱦ��Ҳ�����������ۣ������û����Լ�������Ϊ���յز�����Ǭ¡ʮ����ĸ��㣻���ģ������衰װ�㼸�֡��ˣ���Ǭ¡��ʮ������յ³ƣ��������м���Ͷ���⾰��ū�ŵ�װ�㼸�ֱ�����ơ���40����ֻ����������Դ��ˡ�
�����ڿ������������Ƶ���Ϊ�����Գ�Ϊ�����ŵĵ��ơ������ǽ������㷺�ģ����ż��ֲ�ͬ�Ĵ�����ʽ����æ��������ת�����ߡ�ͳһ���������滯���Լ���Ħ��ӭ�ϣ��ȵȡ���41��
���������һ�֡��ٳ��Ļ�������һ���Ƕȣ�����Ҳ�ɽ������������������������Ϊһ���������ǣ�Ҳδʼû�м��ֵ�����˵������������һ��������˵��ר�ơ������ܻ���ר�ơ��������ء�����������֮�䣬�ʹ�������һ���е��Եġ����������ݶ����Ρ���ʹ������ܹ᳹ʼ�ա����ⷽ�棬һ���ط���Ա����������ռ��֣��������Ա��������ܣ�������˵�����ˡ���һ���棬��Թ�Ա����Щ���������¡����Dz���äĿ����������ģ����٣����ϾͲ��������ס�������������ľ��䲻ͬ���������Ʒ�ȵĹ�Ա���֮�����Σ�����Ҳ�ǿ�ǰ���ˡ�
�����ص��������������ѿ��������˶���Ŀ���м���������ʧ�����¼䣬���������ʵ���
�����˰����ɣ���Ϊ�ϲ⡭�����������ã��ֲ��Ϲ���ʵ�飻��������֮˵���������Ʋ�������������֮�ˣ����н����ȫ����ȥ����
�������б����а��ػ���֮�ˡ�����֪���IJ���Ϊ����һ�£�ϵ�����ƶȣ���ȥ���裬���������ͣ���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