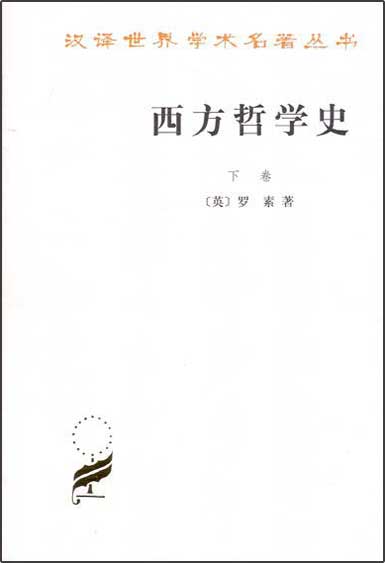艺术哲学-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还有马夫,拿枪的骑士,同他一样穿着缀有金线坠子的大马士革白缎子。他的传令官,金羊毛骑士,把他介绍给公爵夫人。随后走出许多别的骑士,马的披挂有的是台金线织的大红呢,有的是绣着金铃的呢,有的是大红丝绒上镶着貂皮,有的是紫色丝绒缀着金线或丝线的坠子,有的是洒全的黑丝绒。——假定今日的政府要人穿得象歌剧院的演员,学着调马师的样子做出种种技击的架式,你们一定会觉得荒谬绝伦;可见感受形象的本能和装饰的需要,在当时是多么强烈,而现在大为衰退了。
可是这还不过是序幕,比武以后八天,轮到勃艮第公爵请客了,那比所有的宴会都阔气。极大的厅堂上张着挂毡,毡上织着大力士赫刺克勒斯一生的故事,五扇门有弓箭手站岗,穿着灰黑两色的长袍。两旁搭起五座看台安置外客,都是些男女贵族…大半是化了装来的。客人的坐位中间放一张高大的食桌,摆着金银的杯盘,用黄金与宝石做装饰的水晶壶。厅中央立着一根大柱子,上面“放一个女人的像,头发挂到腰间,头上戴一顶华丽的帽子,大家吃饭的时候,她乳房中有肉桂酒流出。”三张其大无比的桌子,每张桌上放着好几样“摆设”,都是庞大的机关布景,好比现在新年里给有钱人家的孩子的玩具,不过扩大了规模。以好奇心和活跃的幻想而论,当时的人的确是孩子,最大的欲望是娱乐眼睛;他们拿人生当做幻灯一样戏弄。两样主要的“摆没”,一样是一个大肉饼,有二十八个“真人”在上面奏乐,另外一样是“一所有窗洞有玻璃的教堂,有四个唱诗的人和一口叮叮当当的钟。”但“摆设”总共有一二十样:一所大型的宫堡,壕沟里流着玫瑰花露,塔顶上站着仙女梅吕西纳;一个用风车发动的磨坊,几个弓箭手和射弯手在那里射喜鹊;一只桶埋在葡萄园里,流出一种苦酒,一种甜酒:一只狮子和一条蛇在沙漠上搏斗;一个野人骑在骆驼上;一个小丑骑着熊在巉岩与冰山之间奔跑;一口有城市与宫堡环绕的湖;一条满载货物的船抛下锚停在那里,船上有绳索,有桅杆,有领港员;一个用泥上和铅砌的美丽的喷水池,周围用玻璃做成小树,花叶俱全,还有一个背着十字架的圣·安特菜;一个玫瑰花露的喷水池,雕像是一个裸体的孩子,姿势和布鲁塞尔的玛纳冈比斯喷水池上的一样。你看了这些“摆设”,简直以为走进了一家卖新年玩具的铺子。
但有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摆设还嫌不够,他们还要看活动表演;所以另外有十几个节目,节目与节目之间,教堂里和大肉饼上奏起音乐,使席上的宾客除了眼睛有得看,耳朵还有得听:钟声大鸣;一个牧童吹小风笛,几个儿童唱一支歌;人们轮流听到大风琴,德国号,双簧管,唱圣诗,长笛台奏,由六弦琴伴奏的合唱,小鼓合奏,打猎的号角和猎大的嗥叫。然后一匹披暗红绸的马倒退进来,两个吹喇叭的“不用鞍子,背对背坐在马上”,前面有十六个穿长袍的骑士开路;随后出来一个半人半秃鹰式的怪物,骑在野猪身上驮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两支标枪和一个小盾牌;后面是一只人工做的小白鹿,披绸挂彩,角是黄金的,背上驮一个孩子,穿一件深红丝绒短褂,唱着歌,鹿唱着低音部分。一这些人物野兽都在桌子四周绕一个圈子。最后还有一个玩艺儿大受欢迎。先是一条龙在空中飞过,明晃晃的鳞甲把哥特式的高耸的天顶照得雪亮,接着飞出一只鹭和两只鹰;鹭马上被鹰啄落,有人捡来献给公爵。临了慕后号角齐鸣,幕自处,埃俄尔卡斯王那松出台念一封他妻子梅台的信,然后他斗牛,杀蛇,耕地,把妖怪的牙齿掇种,长出一批武装的人。宴会到这个阶段变得严肃了:那是一部骑士的传奇,《阿玛提斯》中的一幕,好象把堂·吉诃德做的一个梦实地表演。厅上出现一个巨人,穿一件绿绸袍子,缠着头巾,手执长枪,牵一只披绸挂彩的象,象背上放二座宫堡,宫堡里面有一个修女打扮的妇人,象征“圣洁的教会”;她停下来通名报姓,号召在场的人参加十字军。于是金羊毛骑士带着几个侍从宫出来;他颈间挂一根镶嵌宝石的金项链,手里拿一只活的山鸡。勃艮第公爵手按山鸡起誓,愿意帮基督教付伐土耳其人;所有的骑士都跟看他发愿,每人有一篇誓约,文字仿照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迎拉奥》的体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山鸡之盟”〔一四五四〕。宴会用一个带有神秘色彩与道德意味的跳舞会结束。在音乐声中,在火把照耀之下,一位白衣大太肩上写着名字,叫做“上帝的恩宠”,向公爵朗诵一首八行诗,临走留下十二个妇女,代表十二美德:信仰,慈悲,正直,理性,节制,刚强,真实,慷慨,勤谨,希望,勇敢,每个女子由一位骑士陪随,骑士身穿暗红短褂,缎子的衣袖上绣着花,钉着主银首饰。十二个妇女和骑士跳舞,替比武的优胜者夏德莱公爵加冕,到清早三点,场上宣布有另一次比武的时候,舞会才结束。——节目太多了;感官和想象力为之麻木了;这些人对于娱乐只是贪嘴而不会辨别味道。这一阵热闹和许多古怪的玩艺儿给我们看到一个蠢笨的社会,一个北方民族,一种才成形而还粗野幼稚的文化。他们虽与梅提契同时,却缺少意大利人的高雅大方的趣味。但两个民族的风俗与想象力,实质上并无分别;象佛罗伦萨狂欢节上的车马和豪华的场面一样,中世纪的哲学,历史,传说,在这里都成为具体的东西;抽象的教训化为生动的形象、美德变做有血有肉的女人。结果就有人想把这种种东西画成图画,做成雕塑:而且所有宴会中的装饰已经是浮雕和绘画了。象征的时代让位给形象的时代:人的精神不再满足于经院派的空洞的概念,要观赏主动的形体了;人的思想也需要借艺术品来表现了。
但尼德兰的艺术品不象意大利的艺术品;因为精神的修养和趋向都不一样。上面两个代表教会与德行的女人念的诗都幼稚,平凡,空洞,毫无生气,全是陈辞滥调,一连串押韵的句子,节奏和内容同样贫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维拉尼,在尼德兰不曾出现过。人的精神觉醒比较晚,距离拉丁传统比较远,禁铜在中世纪的纪律和麻痹状态中比较长久。他们没有阿弗罗厄斯派的怀疑主义者和医生,象彼特拉克所描写的;也没有复兴古学的近乎异教徒的学者,象洛朗·特·梅提契周围的那般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与感情,这里比威尼斯或佛罗伦萨活跃得多,顽强得多,便是在勃艮第宫廷奢华淫逸的风气之下还照样存在。
他们有享乐的人,可没有享乐的理论;最风流的人物也为宗教服务象为妇女服务一样,认为那是荣誉攸关的大事。一三九六年,勃艮第和法国有七百贵族加入十字军,生还的只有二十七个,其余全部在尼科波利斯战死;蒲西谷把他们叫做“受到上帝祝福的幸运的殉道者”。刚才你们看到,利尔那次大吃大喝的宴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郑重其事的发愿,要去讨伐危害宗教的敌人。还有些零星故事证明早期的虔诚并未动摇。一四七七年,纽仑堡有个人叫做马了·侃采,到巴雷斯泰恩去朝圣,数着卡尔凡山到波拉多的屋子有多少步路,预备回来在自己的住家和当地的公墓之间造七个站和一座卡尔凡山;因为丢了尺寸,他又去旅行一次,回来把工程交给雕塑家亚当·克拉夫脱主持。法兰德斯象德国一样,一般布尔乔亚都是严肃而有点笨重的人,生活局限于一乡一镇,守着古老的习惯,中世纪的信仰和虔诚比宫廷中的贵族保持更牢固。这一点有他们的文学为证;十三世纪末期他们的作品有了特色以后,只限于表现内心的虔诚,重视实际的和城邦本位的布尔乔亚精神:一方面是宣扬道德的格言,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当时真实的政治与历史为题材的诗歌;另一方面是歌颂圣母的抒情作品,神秘而温柔的诗篇。总之,日耳曼的民族精神是倾向信仰而非倾向怀疑的。尼德兰人有过中世纪的托钵僧和神秘主义者,有过十六世纪的反偶像派和大量的殉道者以后,一步一步的接近新教思想。倘若听其自然,民族精神发展的后果可能不是象意大利那样的异教气息的复活,而是象德国那样的基督教思想的中兴。——其次,所有的艺术中以建筑为最能表现民众在幻想方面的需要;而法兰德斯的建筑,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仍然是哥特式的,基督教的,意大利的和古典的式样对它不生影响;风格走上繁琐与萎靡的路,可并不变质。哥特式的艺术不仅在教堂中居于统治地位,在世俗的建筑物中也占统治地位:布鲁日,罗文,布鲁塞尔,列日,乌特那特各地的市政厅,说明这种艺术受人爱好到什么程度,并且爱好的人不限于教士而包括整个民族;他们对哥特式艺术忠实到底;乌特那特的市政厅开始建造的时候,已经在拉斐尔死后七年〔一五二七〕。一五三六年,法兰德斯出身的“奥地利的玛葛丽德”当政的时期,哥特式艺术还开放最后和最细巧的一朵花:勃罗教堂。——我们把这些征候归纳起来,再在当时的肖像画上研究一下真实的人物:捐献人,教士,市长,镇长,布尔乔亚,有身分的妇女,都非常严肃,规矩,穿着星期日的服装,内衣浩白,脸上冷冰冰的,表示有一种坚定深刻的信仰;那时我们会感觉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在这儿是在宗教范围之内完成的,人尽管点缀现世的生活,并没忘了来世的生活,他用形象与色彩方面的创造,表现活跃的基督教精神,而不是象意大利人那样表现复活的异教精神。
法兰德斯艺术的双重特性,是在基督教思想指导之下的文艺复兴;于倍·梵·埃克,约翰·梵·埃克,劳日·梵·特·淮顿,梅姆林,刚丹·玛赛斯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切其余的特征都从这两个特征出发。——一方面,艺术家关心现实生活;他们的人物不再是象征,象老的圣诗本上的插图,也不是纯粹的灵魂,象科隆派画的圣母,而是活生生的有血肉的人。人身上用到严格的解剖学,正确的透视学;布帛,建筑,附属品和风景上面的极细小的地方,都描绘无遗;立体感很强,整个画面非常有力,非常扎实,在观众的眼中和精神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后世最伟大的作家并不超过他们,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们。显而易见,那时的人发现了现实;蒙住眼睛的罩子掉下了,几乎一下子懂得刺激感官的外表,懂得外表的比例,结构,色彩。并且他们喜爱这个外表:他们画的神和圣者都穿着金线滚边,钉满钻石的华丽的长袍,披着金银铺绣的绸缎,戴着灿烂夺目的刻花冠冕;勃艮第宫廷中的一派奢华都给搬上画面。他们还画透明平静的河水,明亮的草原,红花白花,青葱茂盛的树木,满照阳光的远景,美丽的田野。他们的色彩特别鲜艳,强烈;单纯而浓厚的色调依次排比,象波斯地毯,不用中间色而单靠颜色本身的和谐作联系;还有大红披风上的褶缝,天蓝长袍上的皱裥,镶黑边的铺金裙子,绿的帷幕象夏天大太阳底下的草原,强烈的光线使整个画面显得热烘烘的,带些棕色;这是每样乐器发挥出最大音量的音乐会,声音越洪亮,音色越正确。回家觉得世界很美,便把它安排为一个盛大的节日,真正的节日,跟当时举行的一样,照到的阳光只有更明朗;但决不是什么天上的那路撒冷,渗透着另一世界的光线,象贝多·安琪利谷画的。他们是法兰德斯人,决不脱离尘世。他们认真细致的照抄现实,照抄所有的现实:包括盔甲上嵌的金银花纹,玻璃窗上的反光,地毯上的绒头,兽皮上的细毛,亚当和夏娃的裸体,一个主教的满面肉裥的大胖脸,一个市长或军人的阔大的肩膀,凸出的下巴,巨大的鼻子,一个刽子手的瘦削的腿,一个小孩子的太大的脑袋和太瘦的四肢,当时的衣著,家具。这些形形色色的描写,说明他们的作品是对于现世生活的歌颂。——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也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歌颂。不但题材几乎都与宗教有关,还充满着一种为以后同类的画面所没有的宗教情绪。他们最美的作品不是表现宗教史上一桩真实的故事,而是表现真实的信仰,主义的概要;于倍·梵·埃克心目中的绘画,同西摩纳·梅米或丹台奥·迎提〔十四世纪意大利画家〕一样,是高等神学的说明;他的人物和附属品尽管是真实的,也还是象征的。劳日·梵·特·淮顿在《七大圣礼》上画的大教堂,既是一所真正的教堂,也代表神秘的教会;因为教士在祭坛前做弥撒的时候,基督就在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