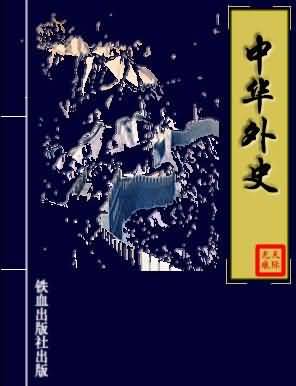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密斯史出后门去,我也是由北岸坐船来的。到了这边,我也爱这西岸幽静,要在这
里走走。”杨杏园道:“这个日子还没有什么趣味。到了秋天,这山上满山乱草,
洒上落叶。岸边的杨柳疏了,水里的荷叶,又还留着一小半,那时夕阳照到这里来,
加上满草地里虫叫,那就很可涤荡襟怀,消去不少的烦恼。”李冬青笑道:“杨先
生这一通话,把秋天里的夕阳晚景,真也形容得出。这是幽人之致,人间重晚晴啦。”
杨杏园笑道:“幽人两个字,不但我不敢当,在北京城里的人,都不敢当。有几个
幽人住在这势利场中?”李冬青也笑道:“不然,古人怎样说,‘冠盖满京华,斯
人独憔悴’呢?”杨杏园记得《随园诗话》中有一段诗话。一个老人说:“夕阳无
限好,只是近黄昏。”一个就解说:“不然,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正和这
段谈话相似。这正是她读书有得,所以在不知不觉之间,就随便的说了出来。觉得
生平平章人物,都是持严格的态度,没有三言两语,可以说得他死心塌地的。这时
李冬青轻描淡写的说了这样几句,他就心悦诚服,完全同意。虽然有人说,情人言
语,无一句一字不是好的,但是他不相信这句话。他便对李冬青道:“这话自然可
以驳倒我所持的论调,但是我也无非是个糊口四方的人,怎样敢以憔悴京华自命。”
李冬青笑道:“我并不是驳杨先生的论调。”杨杏园也怕她误会了,连忙说道:
“自然不是驳我。”两个人都这样忙着更正,倒弄得无话可说。李冬青收起了伞,
扶着石头,慢慢的走到水边下,回转头来,不觉一笑。对杨杏园道:“你看岸上一
个影子,水里一个影子,这正是对影成三人啦。”说时,她身子一歪,怕跌下水去,
连忙往后一仰,以便倒在岸上。杨杏园站在身边,也怕她要跌下水去,抢上前一步,
伸手将她一扶,便搀着她拿伞的那只胳膊。李冬青倒退一步,这才站立住了。当时
在百忙中,没有在意,这会站住了,未免不好意思,两脸像灌了血一般,直红到脖
子上去。杨杏园见人家不好意思,也大海孟浪,心想她若一不谅解,岂不要说我轻
薄?自己退了一步,也站着发呆。李冬青抽出纽扣上的手绢,在身上拂了几拂,又
低头拂了一拂裙子,笑道:“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杨杏园也笑道:“所
以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两人说了这样几句陈书,才把不好意思的情形,遮掩过
去。杨杏园又道:“密斯李刚才说对影成三人,我想要上头是月亮,下面是水,中
间是人,这才有趣。”李冬青道:“月亮下固然是好,但是水面上的斜阳照到人身
边来,却另有一种趣味。说到这里,我就要回套杨先生刚才所说的,是秋天的斜阳
好。金黄色的日光,一面照着平湖浅水,一面照着风林落叶,才是图画呢。”杨杏
园笑道:“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李冬青对于这话,好像没有听见,打开她手捏
的那柄扇子去扑草上飞的一只小黄蝴蝶。这蝴蝶往南飞,她也往南追,追得不见了,
她才算了。杨杏园看见,也从后慢慢跟了来。李冬青扇着扇子道:“倒招出我一身
的汗。”提着手上的伞,将伞尖点着地,一步一步望前走,慢慢的已绕过西岸,便
对杨杏园道:“杨先生也要回寓了吧?”杨杏园道:“我还想在这里面走走呢。”
李冬青道:“那末,我就先走。”说着她弯腰鞠了一躬,便含着笑容,向大门口走
去了。
杨杏园望着她的后影,直等不见了,便在路边一张露椅上坐下了。心想这样个
年轻的人,何以对于一切世事,都这样十分冷淡,我真不解。她的家庭似乎有一幕
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她处处都是强为欢笑的样子,但是我想她本人身上,总没有什
么问题,何以也是这样疏疏落落的?就以她交的女友而论,人家敬爱她的很多,她
却只和那位顾影伶什的史科莲要好。也就可怪。一个人坐在露椅上,发了一会子呆,
忽见地下,有些东西移动。定晴仔细看时,并不是什么东西,原来是太阳落下去了,
月亮的光,便渐渐亮起来。他坐的地方,正是一株大槐树,月亮的光,从树叶里穿
着落到地下,树一动,仿佛就有些薄薄的影子,在浅草上爬来爬去。杨杏园抬头看
时,大半轮月亮,正在树的东边,月亮边几个大一点儿的星,银光灿烂,正在发亮。
蓝色的天空,已经变成灰白色了。自己好笑起来,一个人坐在这里,算什么意思,
起身便望大门口走。
走到那石桥,靠在栏杆上,又看了一会荷花,忽然有一个人,伸手抚着他的背,
回头看,却是华伯平。杨杏园笑道:“秘书老爷,好久不见啦。”华伯平笑道:
“大文豪大记者。”杨杏园道:“你们统一筹备处是个极时髦的机关,薪水照月发
的,你这三百六十块钱的现洋,够花了吧?我们这算什么,像做外线的女工一般,
全靠几个手指头,何从大起?”华伯平便拉着他的衣服,说道:“走走!我请你吃
晚饭。你两次找我,没有遇着,今天算是陪礼。”杨杏园道:“听说你在别的地方,
又弄了两个挂名差事,真的吗?”华伯平笑着说道:“你们是干净人,不要打听这
样卑鄙龌龊的事情。走走。”杨杏园道:“怪不得你忙呢,有三个衙门要到,自然
没工夫了。”华伯平道:“衙门里屁事!筹办处每天去一趟,其余两处,十天也不
到一回。”杨杏园道:“那末,为什么还忙得很?”华伯平道:“除了打四圈,在
惠民饭店里,我是坐不住。早几天,一吃了饭,就踌躇到哪处去玩好。后来熟人一
多了,公园游艺园这些地方,只恨不能分身去应酬。到了晚饭之后,照例是一趟胡
同,非到一点钟后,不能回家。你想,哪还有工夫出来找朋友?”杨杏园道:“你
这样闹,不但经济上受大影响,与卫生也有碍。”华伯平一皱眉道:“这也是没有
法子,你不去,也有人找你。”杨杏园道:’我听说碧波你也给他弄了一个顾问,
是真的吗?”华伯平道:“是真的。”杨杏园道:“他不过是一个学生,你们的处
长,既不认识他,又无联络他之必要,给他这样一个名义作什么?”华伯平道:
“怎么是名义?一百块现洋一个月啦。自然不认识他,也不必联络他,这完全是我
提拔他。”杨杏园道:“你和贵处长一保荐,他就答应了吗?”华伯平笑道:“这
真是笑话。我们敝处的顾问,本来有三四百,也有处长自己请的,也有各处代表硬
要的,也有各方面头等人物荐的。其余便是和处长跑腿的几位政客开单密陈的。最
后处长就把这一大批的名单,交付一个机要秘书,缮写清楚一个等次,由他批准。
偏是那时我也在办公室里,老总就叫我帮着办理。”杨杏园道:“老总又是谁?”
华伯平笑道:“老总就是处长,我们同事这样说惯了呢。那位机要秘书缮名单的时
候,他却私自加上四五位去。其实我也不留心,他却做贼心虚,对我说,这是哪个
阔人的侄子,哪个阔人的大舅,非加上不可,得去和老总说。你何不也加上一个名
字,每月至少弄他一百元。我就说:‘我的名字,怎好加上去呢?那不成了笑话?’
他说:‘谁说要你的名字呢,阿猫阿狗,你随便写一个得了。’我说:‘乱写一个
也行吗?’他说;‘乱写到底差一点,你把你的令亲令友开上一个得了。若是在什
么公团里办事的,那就更好。’我听他这样说,一想碧波近来手头很窘,他又是什
么文化大同盟的会员,何不把他弄上?因此就开了一个名字,给那位机要秘书,而
且说明他的履历。他欣然答应,就把他写上名单去了。其初我还认为未必有效,谁
知过了两天,他真的给我一封聘函,说是已经规定了,每月一百元车马费。我拿了
这封信去告诉碧波,他还以为我和他开玩笑呢。”
杨杏园和华伯平两个人站在石桥栏杆边说话,忘其所以。直等话说完了,华伯
平才重申前请,要杨杏园去吃晚饭。杨杏园道:“我原不用得和你客气,但是到了
这时,是我办事的时候了,我不能再耽搁。你若请我,改为明天罢。”华伯平道:
“这里的西山八大处,我只去过一次,你若抽得出工夫来,我们同到八大处去玩一
天,好不好?”杨杏园道:“这个热天,爬山有些不合宜。”华伯平道:“咱们坐
轿子。”杨杏园道:“坐轿游山,这似乎有些笑话。那种轿子,两根木杠抬一把藤
椅,真有些像江南人抬草庙里的菩萨。而且上山往后倒,下山往前冲,也不舒服。”
华伯平道:“那末,不上山,在山脚旅馆里坐坐,好不好?我还有个新朋友,在半
山中新盖一所房子,高兴我们可以在那里借住一宿,第二日一早回家,也不误事。”
杨杏园欣然道:“好多年没有在郊外住过了,你果真去,我可以奉陪。”华伯平道:
“我一天到晚没事,有什么不去?你明天早饭后在家里等我,我坐了汽车来邀你。”
杨杏园道:“好,就是这样办。”就和华伯平分手回家。
到了次日,杨杏园起了一个早,把所有的稿子,都预备好了。编稿子的事,就
打电话,托了同事的代办一天。不到十一点钟各事都预备妥了,便催着长班开早饭。
这里饭只吃了一碗,华伯平就走进来了,后面还跟着有吴碧波。杨杏园道:“很好,
三个人不多不少。你们都吃了饭吗?”华伯平指着吴碧波道:“在他寄宿舍大饭厅
上吃的饭,居然是一家很齐备的小馆子。在北京当大学生,真是最舒服不过的事,
什么都有人替你准备好了。”吴碧波道:“你很羡慕学生生活,我们换一换地位,
如何?”华伯平道:“无奈人不能当一辈子的学生,若是能当一辈子的学生,谁不
愿意?”他二人在说笑话,杨杏园便赶忙吃饭。吃过饭之后,胡乱洗了一把脸,催
着长班沏茶。等茶沏好了,又滚热非常,各人斟了一茶杯,只端起来沾了一沾嘴唇,
便放下来,等不及喝了,三人就匆促出门登车而去。
汽车出了阜成门,不一时,便来到乡下。这汽车经过的马路,两面都种着柳树,
虽然也有间断的地方,却离不很远,汽车在绿荫里面飞跑,清风迎面而来,倒也不
觉的热。马路的两边,人家地里,种着的玉蜀黍和高粱,都有五六尺高,青苍披离,
一望无际。杨杏园道:“你看,这种高粱地,真是深密隐蔽,所谓青纱帐起,难免
可以藏匪了。”吴碧波道:“也是去年这时,我在城外进城去,一个人骑着一匹驴
子,走到这样四围都是高粱的地方,真是要捏着一把汗。”杨杏园道:“这里是大
路,不断的人往来,歹人藏不住,不要紧的。”吴碧波道:“这却难说呢。我听见
说,是哪家一个小姐骑脚踏车进城,路上走脱了伴,把身上的首饰全取下来,埋在
一株柳树兜下,做了暗记号,然后飞跑而去,第二天才坐了汽车来挖取东西。”杨
杏园笑道:“法子倒是好法子,若是果然路上出坏人,他是一个女子,根本上人就
是危险品呢,她就没有料到吗?”说起话来,不觉车子已走了二十多里路。西山迎
面而起,越看越近。先是看见一排山,渐渐分出岗峦,渐渐看出山上的房屋,渐渐
看出山上的树木,山脚下一座西式楼房,半藏半露在树影丛中,西山旅馆,已经在
望。
一会工夫,汽车过了一道乾河石桥,便停在旅馆边空场里。这里到也停了七八
辆汽车,一路挨山脚排着。大家下得车来,就闻着山草野花一股清芬之气。静悄悄
的,听得四周深草里的虫叫,顿觉耳目为之一新。走进旅馆门口那个露台下面来,
只见茶座下,除了四五个中国人而外,全是西洋人。犄角上那张桌子,沏了一壶茶,
围坐着七个人,都是矮小个儿,穿着粗料的西装,叽哩咕噜说个不歇。杨杏园对华
伯平道:“讨厌得很,我们上那边去坐罢。”说着,他便在前走。露台外面,是个
敞厅,也摆了两张桌子,又有几个穿西装的矮个儿围着坐在那里。华伯平知道杨杏
园不愿意,便说道:“我们既然来了,也不可以不逛逛山,先到山上去走走,回头
再来休息,好不好?”杨杏园首先赞成,吴碧波也没有持异议,三人就在那小花圃
里穿了过去,插上小路。这时,路边下有个穿短衣服的人,在一边跟着走,对华伯
平道:“先上那一边,看竹子,上碧摩崖。这一边是……”杨杏园知道是山脚下领
路的,无非借此弄几个小钱。便对他一摆手道:“这里我们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