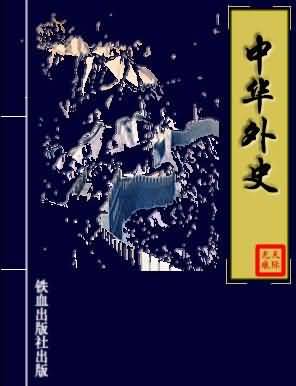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9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扑着她的两腮,笑了出来。便问道:“什么价钱?”余瑞香道:“那不一定,是按
着法国佛郎算的。佛郎涨价就贵些,佛郎跌价,就便宜些。”梅双修道:“买多少
佛郎一瓶呢?”余瑞香道:“好些的,值六十多个佛郎。”李冬青道:“六十多个
佛郎!不是我说一句小器的话,用这种化装品,好似多做两件好衣服。”江止波笑
道:“密斯李,你这句话还不彻底,衣服只要齐整洁净就得了,又何必穿好的。固
然,美的观念,人人都是有的,青年人不是不可修饰。但是我主张修饰的程度,要
男女一样,我们才不至于做男子的玩物。”说时,她将技到脸上的短头发,扶到耳
朵背后去。笑道:“譬如剪发,有许多人反对,说是男不男,女不女,叫人观之不
雅。这话就不通,难道女子定要戴着一头头发,去表示别于男子?况且我们的人格,
人家观之雅不雅,何必去管呢?”杨爱珠和江止波都在学界委员会当过委员的,两
个人的感情,比较又亲密些,说起话来,也就比较的不客气些,她就笑着说道:
“这不是天安门,你又拿了这男女平等的大题目,在这里演说。”江止波道:“并
不是我喜欢说话,我想我们要做一番事业,第一不要去做男子的玩物。要不做男子
的玩物,第一要废去玩物式的装饰。”杨爱珠和杨玛丽虽和江止波的行为相同,但
是都爱拾落得漂漂亮亮的,听了江止波的话,都表示反对。杨玛丽说几句话,里面
夹一个英文单字,和江止波争了半天。最后,江止波满脸急得通红,却又怕人疑心
她恼了,勉强放出笑容。说道:“我不能和你争了。硬要和你争,也是我失败。因
为这里除主人翁和密斯史,都是反对我这种论调的。”朱映霞早就知道她的名字,
绰号“女张飞”,开起联合大会,她一演说,激昂慷慨,连男学生都有些怕她。便
成心去迎合她,笑着说道:“密斯江,我并没有作声,你怎样知道我也反对你的论
调?”江止波眼睛瞧着朱映霞身上穿的印花绸单褂子,把手一指道:“凭这个你就
应该反对我的论调。”朱映霞笑道:“我穿衣服,向来随便,今天因为来拜寿来了,
不能穿得太素净了。”江止波连忙改口道:“我说着好玩呢!我这样很平常的话,
谁不知道,值得反对。”说时,她圆圆的脸儿,满面春风笑起来。朱映霞想道:
“凡是当学生代表,或者什么委员的人,对朋友总是二十四分客气的,这‘女张飞’
也有这种手腕呢。”李冬青在一边,也怕她们说恼了。便对朱映霞道:“听说你们
学校里,处处都含有美术的意味,哪一天带我们去参观一次,好不好?”朱映霞道:
“可以,不用带去,约一个日子,我在学校等你得了。”余瑞香道:“我很爱美术
的,也很愿瞻仰你们贵校,那末,我和密斯李一路去罢。”朱映霞昂头想了一想,
口里念道:“西洋画,写生,雕刻。”然后对李冬青道:“礼拜五罢,那天下午,
我没有课。”李冬青道:“是啊!我在报上看见你们是星期五开展览会啊。”朱映
霞笑道:“那是上星期五的事,早过去了。”江止波道:“提起报,我想起一桩事,
这前面不有两位客,是新闻记者吗?密斯李,请你替我介绍一下,我这里有两份宣
言书,请这两位,在报上登一登。”说时,便将她随身老带着出门的那个皮包,由
旁边一张桌上拿过来,打开皮包掏出一大卷信件,在里面找出两张油印稿子,交给
李冬青。李冬青一看,是女界霹雳社成立的宣言。开头一行一句,便是“打倒蹂躏
女权的强盗”,接上三个感叹符号。第二行第二句,“铲除女界无人格的蟊贼”,
接上也是三个感叹符号。这一篇宣言,简直激烈得无以复加。李冬青一想,你们发
油印传单,只要写得出,就到街上散去,大不了,不过被警察没收了去,那要什么
紧?若是印在报上,人家报馆里,可要负法律上的责任,这不是玩的。恐怕不肯呢。
便笑道:“你们这宣言之外,当然还有别的消息,我引密斯江和他们当面去交涉罢。”
江止波道:“很好,一回熟了,第二回我就可以直接找他们去了。”说毕,江止波
便催着李冬青和她一路到前面客厅里去。
李冬青先和何剑尘杨杏园道:“这位密斯江,有两件稿子请二位在报上登一登。”
这句话说完,江止波走过去,微微点了一个头,便将两张稿子,给何杨二人各一张。
笑道:“二位是尊重女权的,一定和敝社表示同情。”何剑尘一看,心想糟了,这
种稿子,怎么能登?但是人家当面来说,又不便拒绝的。便笑道:“敝社这种稿子,
向来归杨君发,我交给杨君就得了。”江止波道:“二位是一家报馆吗?”何剑尘
道:“杨君兼有两三家报馆的事,敝社也有他。”江止波道:“那就好极了,都请
杨先生办一办罢。”杨杏园对何剑尘望了一眼,心里就在骂他给难题别人做。便对
江止波道:“这当然可以的。不过报纸上登载的文字,和散的传单,比较上法律的
责任重些,这词句之间,似乎……”这时,两只手捧着那油印稿,很注意的看。江
止波见杨杏园这样慎重,站到杨杏园身边去,也跟着杨杏园看那稿子,意思考察杨
杏园注意哪一点。她站在杨杏园并排,略为前一点。她人本比杨杏园矮些,头又微
微的一偏,那剪了的短头发,直挨到杨杏园肩膀上去。在此时间,她那脖子上的胰
子香,头发油香,都一阵阵袭人鼻端。杨杏园是个未婚的青年,在这大庭广众之中,
对这种情况,能受而又不堪受。那江止波却毫不觉得,还追着问道:“杨先生,你
看这里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吗?”杨杏园离开一步,故意走到茶几边去喝一杯茶,然
后说道:“原文似可不登。”李冬青在一边看见,心里明白,心想他已经是够受窘
的了。便插嘴道:“若是真有什么妨碍,密斯江也不能勉强,就请斟酌办罢。”江
止波是在外面办社交的人,哪里还不知道这宣言书过于激烈。就掉转口风道:“对
就请杨先生斟酌办罢。”这时朱映霞和朱韵桐出来了。朱韵桐对李冬青道:“天怕
要下雨,我先走一步了。谢谢!”李冬青道:“忙什么?还有比你路远的啦。”朱
韵桐道:“不,我和这位密斯朱,顺道要到一个同学家去说一句话。”那朱映霞的
未婚夫梅守素,却对朱映霞轻轻的说了一句“我们一块儿走”。他这句话说了不要
紧,一屋子人的眼光,都射在朱映霞身上,闹得人家真不好意思,红着脸,勉强装
着生气的样子说道:“你要买书,你尽管到琉璃厂买去,我的书,我自己会去买。”
梅守素碰了这一个橡皮钉子,当着大众,驳回去,不好,不驳回去,也不好。拾讪
着满屋子里找火柴。找到了,自去擦着吸烟。大家看了,脸上都带一点微微的笑容,
连那老先生方好古,也伸手摸摸胡子。这样一来,朱映霞更不好意思了,拖着朱韵
桐便走。江止波夹着一个皮包,也跟了上来,说道:“密斯朱,我也走,一块儿走
罢。”
三个人辞了李冬青,同出大门。约摸走过十家人家,迎面来了两个男学生,都
扶帽子点头,叫了一声“密斯江”,过去了。朱映霞朱韵桐先都愕然,还以为是在
招呼自己呢,走到胡同口,又听见一个人喊道:“密斯江。”抬头看时,又是一个
男学生和江止波点头。朱韵桐心里想道:“真巧,怎么一出门,就碰见江止波两班
男朋友,不知道的,还说是我们的朋友呢。”三个人又走了一条小胡同,便上了大
街。就有一个穿蓝布长衫白皮鞋的少年迎了过来。二朱一猜,就是江止波的朋友,
先就让开一步。那少年不叫“密斯江”,简直叫她的号“止波”。他问道:“止波,
哪儿去?后天开干事会举代表到汉口去,你是必定要到的。”江止波道:“这事,
我不管。上次推去上海的两个代表,他们开回账来,每天有八十块的汽车费,你瞧!
这成什么话?我们女学生一毛二毛讨饭一样来的捐款,给他们这样去花,我有些不
服气。许多人得了这个信,都要提出质问呢。”那人道:“我也不服,密斯江,你
若到会提出抗议案,我一定附和你。”他两人说话时,面前又过去一班人,都用眼
睛向这边看来。他们走过去不多路,就听见有人轻轻的说道:“你看,那个剪发戴
草帽子的,就是江止波。”朱韵桐朱映霞彼此都听见,四目相视。江止波和那人说
完了,又同二人走了一些路才分手走去。朱韵桐道:“一个女学生,怎么认识许多
男朋友?怪不得外面议论纷纷的说她。”朱映霞道:“你要说这人,真没有人格,
我可以证明你的话不确。不过她女带男性,一点不避嫌疑,做事实在太率直了。”
朱韵桐笑道:“她有男朋友没有?”朱映霞道:“不是正在说她的男朋友吗?”朱
韵桐道:“不是平常的男朋友。”朱映霞道:“啊!你说那个,还没有呢!因为差
不多的人,都有些怕她。”朱韵桐道:“你怎样知道?”朱映霞道:“听见人家说
的。”朱韵桐笑嘻嘻地道:“谁说的?”朱映霞被她这样一问,笑着不说。朱韵桐
道:“只怕是密斯脱梅告诉你的吧?你们的感情太好了,简直无话不说呢。”朱映
霞笑道:“大街上走道别嚼蛆了。雇车去罢,省得你一路罗唆了。”
说毕,雇了车子,就同到一位女朋友家里来。这女友也是朱映霞的同学。她的
名字叫乌淑芬。因为她生了一脸的疙疽麻子,人家当面称她“密斯乌”,背后却叫
她“乌麻皮”。不过脸是麻,心里是很聪明的,用功的学生都喜欢和她来往。她对
朱映霞道:“你两人怎样一路来了,今天下午,女生开半天的会,就是你没有到。”
朱映霞道:“什么事?”乌淑芬道:“今天教务长在讲堂上公布,模特儿已经请好
了,从明天起,无论男女学生,一律画模特儿。当时我们就反对,说女生不画模特
儿。教员说:“这话太顽固了,不是艺术家应说的话。难道人体写生,女画家就废
除它吗?”磋商半天,教务长总是说非画不可。后来我们让步,说画也可以,让女
学生专在一个教室里画。教务长也不肯,说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一个办法。他知道
我们不会上堂,他说画人体写生不到的,记过一次。你看这事怎样办?依我说,这
事也很普通了,我们用艺术的眼光看去,好像学医的学生理学一样,那也不见奇。”
朱映霞道:“你上堂不上堂呢?”乌淑芬道:“大大方方的去,怕什么?”朱映霞
笑道:“我们班里的男生,有两个坏鬼,就怕他捣乱。”朱韵桐插嘴问道:“你们
画时,真对着活人画吗?”朱映霞道:“自然对着活人画,难道模特儿是什么东西,
你还不懂?”朱韵桐笑道:“懂我倒懂,不过我疑心一个女人,怎样好意思一丝不
挂,让人家去画?我总怕这话,是顽固派造的谣言。”乌淑芬道:“我们也没有画
过,据我们猜想,总不能一丝不挂。我们向来是画半截的人体标本,活人也许只画
半截呢。”朱韵桐道:“那倒罢了,不然,莫说是画,看见也要叫人肉麻。”她说
这一句话,大家心里一想,都笑起来。当学生的人,是睡得早的,她们谈了一会儿
话,各自散了。朱映霞回得家去,一个人想,明天还是上学不上学?若是不上学,
母亲一定问什么原故,她老人家,因为男女同学,是反对我进这个学堂的,因为有
个他在里面,他要这样办,母亲才答应了。而今若是告诉母亲,说是不分男女,一
齐对着一个赤着身子的女人画像,她一定说是怪事。不但不要我画,恐怕还要我退
学呢。我想还是不告诉母亲的好,省得麻烦。明天到学校里去,若是女生都画,我
也只好跟着。若是也有不画的,我就请两点钟假罢。这样一想,就没有作声。
次日一早上学,恰好头一点钟,就是画模特儿。讲堂外的空场上,女同学三三
两两,交头接耳,在那里说话。同班的男生,脸上都带一点笑容,对女生好像比往
日有些希奇的样子,来来去去的,都不住的望过来,意思是侦察女生什么行动似的。
乌淑芬早就来了,和两个女生,站在一株柳树底下说话。朱映霞看见,便也走了过
去,就问乌淑芬道:“怎么样?我们都上堂吗?”乌淑芬道:“大家都是唧唧哝哝
的,在私地里反对,并没有哪个肯和教务长去交涉的。那还不算了。”一句话刚说
完,当当当,上课的钟,已经响起来了。那些男学生,好像上饭堂似的,一刻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