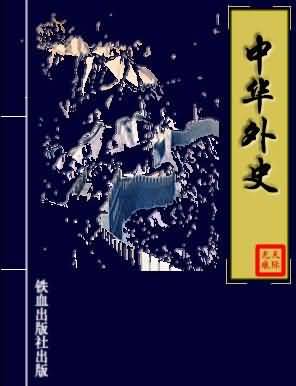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院子里徘徊着一会儿,胡二已经送上饭来。因为杨杏园向来不吝惜小费的,
所以他们过年这一天,也格外孝敬一点,有四个碟子,两碗菜,一个小火锅,另外
一把小锡壶,烫了一壶酒。这些东西,都给放在外边屋里桌子上。又给他找了两个
洋瓷蜡台,点了两枝红色的洋蜡烛。杨杏园一看,心想道:“难为你们,倒有些意
思。”这时,屋子里炉火熊熊,红烛高烧,茶几上两盆梅花,烘出一阵一阵的香味,
加上桌上的筷子酒杯,都已摆好,不觉也有点酒兴。便端了一把椅子,对着梅花坐
了,斟上一杯酒,喝了一口。这时,爆竹的声音,越发一阵紧似一阵了,虽然一个
人自斟自饮,却是今天是大年三十夜的观念,一刻也去不了。看见刚才看的《十八
家诗钞》,还在旁边桌子上没有收起,又未免记起“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的
句子,便将一枝洋蜡烛移在身边,拿了一本诗摆在面前,一边喝酒,一边念诗。不
知不觉一小壶酒都喝完了。火锅里的菜,也吃去一大半。筷子一放,这才觉得有点
儿醉。胡二为他这一顿吃得久,已经来过三四次了。这时又来了,见他一人在屋里
徘徊,便道:“馆里有几桌牌,杨先生不来一个吗?大年下,热闹意思。”杨杏园
却只笑笑。胡二倒了茶水,收拾碗筷去了。杨杏园也踱出院子来,一看天色,比先
更黑,半空中花爆的火焰,也比前更多。隔壁邻居,爆竹刚刚放完,一种硫磺气,
穿过墙头来,犹自未消。刚才一会儿围炉酌酒的时候,不觉任兴喝去。喝过了,脑
筋未免昏昏的,就是身上也微微的出了一些汗。如今在冷的空气里站着,又闻着爆
竹气味,精神倒为之一快。想起今天买了两块多钱花爆,还放在书架子下呢,便叫
胡二督率两个小伙计,搬了出来,在院子里放。他们听说放不要钱的花爆,都点着
一根香,很高兴的来放。杨杏园背着手,站在廓檐下,膝陇着醉眼看人家放爆竹,
满院子都是硫磺味,却也有趣。爆竹放完,夜也深了,那远近的爆竹声,仍旧断断
续续,闹个不了。他坐在屋子里听着,想着平常听人家放爆竹,很是讨厌,今晚听
到放爆竹,却别有一种趣味,这也就不可言喻了。坐了一会,酒气还没全消,便倒
在床上,起初还闲着眼睛听爆竹,后来渐渐就不听见。
第二十四回 新句碧纱笼可怜往事 锦弦红袖拂如此良宵
杨杏园一觉醒来,已经另是一年。那窗户纸上的太阳,又下来大半截了。漱洗
已毕,喝着茶,想了半天,有一桩事好像没办,想了一想,原来是没有看报。这时
忽听见吴碧波的声音在外面喊道:“恭喜恭喜。”说完,人已经进来了。杨杏园道:
“你这崭新的人物,还好意思拜年。”吴碧波道:“人家都以为过年好玩,我反觉
得今天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昨晚上打了一夜的牌。天亮了,又无可消遣,便和几个
打牌的,专门走小胡同,看人家门上贴的春联。这种事情,好像很无聊,其实有趣
的很。譬如介绍佣工人家的门口,贴着‘瑞日芝兰光甲第,春风棠棣振家声’。又
像寿材店门口,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牛头不对马嘴,却是
偏偏又有些意思。仔细一想,不由得你不发笑。”杨杏园道:“这一早晨,你们都
是干这个玩意吗?”吴碧波道:“糊里糊涂一跑,由北城到南城,走的路实在不少,
可是好的对联,却不过一两副。他们到了南城,逛厂甸去了,我却来找你。”杨杏
园道:“去年何剑尘拿着许多红纸回去,大概写了不少的对联,你何不去看看?”
吴碧波道:“你也闲着没事,我们一道去谈谈,好不好?”杨杏园正在无可消遣,
也很同意,便和他一路到何剑尘家来。
走到门口,并没有看见贴春联,却有两辆人力车,放在大门边,好像是等人的
样子。杨杏园道:“我不进去了,这不是他家里来了客,就是他夫妻两人要出去。
何苦进去扫人家的兴。”一言未了,只见何太太穿了一身艳装,走了出来。后面跟
着一位二十开外的姑娘,长发堆云,圆腮润三,双目低垂,若有所思,皓齿浅露,
似带微笑。不事脂粉,愈见清灌。她身上穿了一件瓦灰布皮袄,下穿黑布裙子,肩
上披了一条绿色镶白边的围脖,分明是个女学生。和何太太艳装一比,越发显得淡
雅。何太太一眼看见杨杏园和吴碧波,便道:“请家里坐。剑尘在家里。我不久就
回家来的,回头我们再打牌。”说着她和那位姑娘坐上车子,就拉起走了。
杨杏园道:“很奇怪,他家里哪里来的这一位女学生?看她样子,朴实得很,
绝不是何太太的旧姊妹,也不是何剑尘的亲戚。这却教人大费思索了。”两人走进
门,直往何剑尘书房里走去,只见他面前桌上,摆着两个围棋盒子,一张棋盘,一
本棋谱。他眼睛望着棋谱,一只手两个指头,夹着一粒棋子,不住的在桌子上扳。
一只手伸在盒子里抓棋子。全副精神,都射在棋盘上,两人走了进去,他并不知道。
一直等他们走到桌子边,抬头一看,两手推开棋盒子,才笑了起来。杨杏园道:
“尊夫人刚才上车,想是逛厂甸去了。你怎么不前去奉陪?”何剑尘道:“她是去
拜太师母的年,我怎么好陪着去?”杨杏园道:“你又信口开河,她哪里来的太师
母?”何剑尘道:“你们刚才进来,看见她身后还有一个人没有?”吴碧波道:
“不错,她后面跟着一个女学生。”何剑尘笑道:“那就是她的先生,有先生自然
就有太师母了。”杨杏园道:“这一位女西席,是几时请的?怎么我们一点儿不知
道?”何剑尘道:“说来就话长了。有一天我在敞亲家里闲谈,说到女子的职业问
题,我敝亲告诉我,说正是很要紧的事,不过不可本事太好了,太好了,就怕没有
饭吃。我说,这话太玄,我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现在有个女学生,
书也读得好,字也写得好,她丢了正经本领,只靠绣花卖钱吃饭,你想这不是本事
太好的不幸吗?’我就问:‘这是什么缘故?’他说:‘这个女学生,原是庆出的,
父亲在日,是个很有钱的小姐。后来父亲死了,嫡母也死了,她就和着她一个五十
岁的娘,一个九岁的弟弟,靠着两位叔叔过日子。两个叔叔,一个是金事,一个还
做过一任道尹,总算小康之家,不至于养不起这三口人。无如她那两位婶母,总是
冷言冷语,给他们颜色看。这女学生气不过,一怒脱离了家庭,带着母亲弟弟,另
外租了房子住了。她母亲手上,虽然有点积蓄,也决不能支持久远,她就自告奋勇,
在外面想找一两个学堂担任一两点钟功课,略为补贴一点。无如她只在中学读了两
年书,父亲死了,因为叔叔反对她进学校,只在家里看书,第一样混饭的文凭就没
有了。’”杨杏园道:“教书不是考学校,只要有学问就得了,何必要文凭?”何
剑尘道:“你不知道她那种没有声誉的人,私立的中小学校,不会请她。公立的学
校,他们又有什么京兆派,保定派,许多师范毕业生,还把饭碗风潮闹个不了,没
有文凭的人,他们还不挑眼吗?所以我说的这位女学生,她就情愿收拾真本领,干
些指头生活。我听了敝亲说,很为惋惜,就说内人正打算读书,她如愿意做家庭教
师,我可以请她。我敝亲以为是两好成一好的事,一说就成了。其初,我也不过以
为这位女士国文精通而已,不知她的本领如何。况且她又很沉默的,来了就教书,
教了书就走,没有谈话的机会,我也没有和她深谈。一直到了前五天,我们送了她
一些年礼,她第二日对内人说,她没有什么回礼的,新画了一张画,打算自己挂,
如今就算一种回答的礼品,请我们不要见笑。我将那画一看,是一幅冬居图,师法
北苑,笔意极为高古。我就大为一惊,不料她有这样的本事。后来我又在上面看见
她题了一阕词,居然是个作者。”杨杏园笑道:“你把那位西席,夸得这样好,恐
伯有些言过其实。”何剑尘发急道:“你不肯信,我来拿给你看。”说着,跑进里
面去,捧着一块镜架子来。把那镜架于放在桌上,用手一指道:“你瞧,你瞧!”
杨杏园一看,果然是一幅国粹画的山水。画的上面,有几行小字,那字是:
窗外寒林孤洁,林外乱山重叠,地僻少人行,门拥一冬黄叶。
檐际儿堆残雪,帘外半钩新月,便不种梅花,料得诗人清绝。
杨杏园道:“这词本不算恶,在如今女学生里,有能填词的,尤其是不多见。”
说着,一看画上面,有一块鲜红的小印,刻的是隶书,是“冬青”两个字。他不觉
失声道:“咦,奇怪!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便问
道:“她姓什么?”何剑尘道:“她姓李,你认识她吗?”杨杏园偏着头想了一想
说道:“认识我是不认识,只是这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吴碧波道:“这有
什么可想的,这位李冬青女士,既然是个词章家,难免向报纸杂志上投稿,大概你
在报纸上遇见她的作品了。”杨杏园道:“也许是这样。”吴碧波笑道:“剑尘夫
人有这样一个好先生,将来一定未可限量。可是待先生要既恭已敬才好呢。”杨杏
园道:“这一层我想一定不会错的。你只看这一幅题词和画,用描金红木镜框子配
起来,真是碧纱笼句呢,其他可想了。”何剑尘却只笑笑,依旧把画送到里面去了。
一会儿,何剑尘家里的老妈子,搬出许多年果子来。何剑尘一皱眉道:“不要
这个,赶快收了去,把昨日蒸好了的那些成东西,可以切出几碟子来。”说到这里,
对吴碧波道:“看你们的神情,大概还没有吃饭。煮一点儿面吃,好不好?”吴碧
波笑道:“你刚才要把年果子收了去,我原就老大不高兴。如今有面吃,我自然是
愿意了。”何剑尘便吩咐家里人办去,又笑道:“不是不给年果子你们吃,这种东
西,实在太俗,也没有什么好吃。”吴碧波道:“这样说,你又何必办在家里呢。”
何剑尘道:“等你娶了老婆,你就会知道所以然。这都在奶奶经上,多少章多少条
规定的呢。”不多一会,老妈子果然端上八碟腊肴素菜之类和一小壶酒来,三人一
面喝酒,一面说笑。说了一阵,又说到这位李冬青女士身上来。杨杏园问何剑尘道:
“你们嫂夫人,既然去拜太师母的年,怎样这位先生倒在你们家里?”何剑尘道:
“她们也是前世的缘分,这位先生和这位高足,简直不能隔一天不见面。李女士是
前天在这里教书的,昨日过年没来,今天她在家里预备了许多吃的,怕内人不去,
就先来接她了。”吴碧波道:“她上面是个嫌母,下面是个弱弟,一个人长此维持
下去,恐怕不容易吧?”何剑尘道:“现在她自由自主,不过负担重些,倒不要紧。
从前靠着她叔叔的时候,十分可怜。前不久的时候,她曾做了几十阕小令,叙述她
的境况,题为《可怜词》,可惜她不肯拿出来给我看。但是由刚才你们看的那首词
而论,已经值得碧纱笼了,那末,她的《可怜词》可想而知,可怜的往事,也就更
可知了。”杨杏园道:“文字为忧患之媒。这位女士,要是不认识字,糊里糊涂的
过去,或者不会这样伤心。”何剑尘道:“你这话也有相当的理由,我却也承认不
错。”
说到这里,剑尘的夫人,已经回来了。何剑尘道:“你怎么回来得这样快?”
何太太道:“我知道三差一,赶紧回来打牌来了。”杨杏园笑道:“爱老师,到底
不抵爱打牌。”何太太道:“我这个老师,也不能再教我这个无用的学生了。她要
到学堂里,真做老师去了。”何剑尘道:“哪个学堂要请她?你怎么知道的?”何
太太道:“也是老太太说的,还叫我问你可以去不可以去。说是个什么教戏子的学
堂。难道唱戏的还要进学堂吗?”何剑尘道:“唱戏的怎么不能有学堂。有一天在
街上过,你看见一大班孩子,一律穿着黑布马褂,蓝布棉袍,戴着青布小帽,在人
家屋檐下,梯踏梯踏的走,那就是唱戏的学生。你还问我呢,这是哪家大店里,这
么些个徒弟?我就说是唱戏的,你忘了吗?”何太太道:“孩子唱的戏,我也看见
过,台上扮起小生小旦,都很俊的。那些孩子,就像苦儿院里放出来的可怜虫一般,
面孔黄黄的,拖一片,挂一片:你说是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