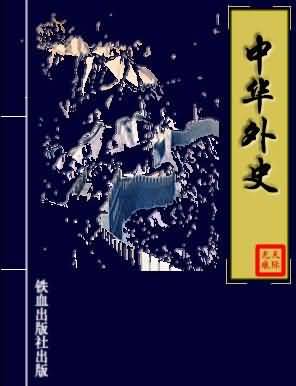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1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是我的熟人。这是一桩小事,还说什么人格担保吗?”挂上这边的电话,于是打
一个电话给他相熟的医生刘子明,请他就去。把医生约好了,这才去睡觉。
到了次日起来,刘子明也来了电话。杨杏园接着电话先道谢了一声。刘子明道:
“你不要向我道谢,我先向你道歉。你那贵友,我昨晚匕到的时候,人已不中用,
没法子救了。”杨杏园道:“死了吗?什么病?病得这样急。”刘子明道:“并不
是病,是服了毒了。我看那情形,很是凄惨。”杨杏园道:“服了毒,很奇怪。这
人是个很活泼的青年啦。’划子明道:“这事你一点不知道吗?为什么你又打电话
找我呢?”杨杏园道:“我也是接了朋友的电话,转达给你的。既然这人出了这种
惨事,我倒要去看看。”挂上电话,并不耽搁,便到平安公寓来。
一进门便见西厢房门外摆了一张桌子,五六个人在露天里坐着,好像议论一件
什么事似的。陈学平精神颓丧,也坐在一张藤椅上。两只脚却一直架到桌子上来,
人倒仰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养神。杨杏园先叫了声“学平”,他睁眼一看,连忙站
起来道:“你怎么来了,知道这一件事吗?”杨杏园道:“我是听见医生说的。他
现在什么地方?”陈学平道:“在屋里躺着。”杨杏园道:“我和任君,也是朋友,”
虽然交情不深,人到这步田地,实在可惨。我要进去看看。”说时,顺手将房门一
推,只见屋里的东西,弄得异常凌乱。桌子上摆满了茶壶茶碗药瓶药罐之类。靠着
床两张椅子,上面堆了许多衣服和几双脏袜子,满地上是纸片药汁棉絮,床上直挺
挺地睡着一个人,脸上把一条白手绢盖着。他身上穿一件旧湖绉夹袍,上面也粘满
了斑斑点点的痕迹。自然,这就是任毅民的尸首。杨杏园想他也是风度翩翩的一个
少年,活的时候,是多么活泼,一口气不来,就躺在这里,一点事情也不知道了。
他这样想着,正要走上前,伸手去揭面上那块白手绢。陈学平连忙执着他的胳膊。
杨杏园回头看时,陈学平连连摆手说道:“不要看罢,你若看了,你心里要难过的。
你看看他那手,你就知道了。”杨杏园走近一步,俯着身子一看,只见他的手指,
全是紫的。手指甲,还变作青色。陈学平道:“你看见吗?就此一端,其余可知了。
出来坐罢。他这样一来,让我受了很深的刺激。不要尽看,越看越让人伤心。”杨
杏园和这任毅民,虽然不是深交,看见这样子,也是恻然不忍,便同到外面来坐,
陈学平顺手就把门带上了。杨杏园道:“他这人很活动的,何以出此短见哩?”陈
学平道:“正是因为他太活动了,所以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头。”杨杏园道:“是什
么原故呢?你能告诉我吗?”陈学平道:“我很愿告诉你。你若隐去名姓,把他的
情节在报上登出来,倒可以劝劝人。不过说起话长哩。”正说到这里,一阵五六个
人,抬了一口白木空棺材进来。又有一个人捧着一叠纸钱,三四束线香,一齐放在
房门口。院子里这几个人,都张罗起来。杨杏园看这样子,现在才开始料理身后,
人家各有事,不便在这里说闲话,便对陈学平道:“有什么事要我办理的吗?”陈
学平因为他和任毅民交情很浅,而且又是忙人,不便连累他,就说:“身后的事,
草草都已料理清楚了。已经打了一个电报到他家里去,预料一个星期之内,就要来
人的。你有事,请便罢,两三天之内,我到贵寓来看你,可以把他的事,详详细细
奉告。”杨杏园听他这样说,便回去了。
过了两天,陈学平手上捧着一本很厚的抄本书,来访杨杏园。说道:“我不是
在朋友死后,揭破他的阴私。这实在是一部惨史,少年人若知道这一件事,大可以
醒悟了。”杨杏园接过随便一翻,就翻到了一页新诗。诗前面并没题目,只是写着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大概是首数的次序,总题目在最前面呢。一页一页,倒
翻过去,翻到最前面,原来题目是“无题”两个字。旧诗的题目,新诗倒借来用了,
这很是奇怪的。于是先看第一首,那诗共有五句。诗说:“人声悄悄,见伊倚着桌
儿微笑。我正要迎上前去,摇动了孤灯的冷焰,我的痴梦醒了。”这也不觉得有什
么意思,翻过一页去,再看前面写着“五”字的一首。那诗说:“禽石填不平的恨
海,我想用黄金来填它。黄金填不满的欲壑,我又想用情丝来塞它。青苔下的蝼蚁,
哪能搬动芳园的名花?这都是自己的妄想,不成呵!怎样反埋怨着她?”杨杏园点
了一点头,陈学平在一旁看了说道:“你是反对新诗的人,怎样点起头来?”杨杏
园道:“我因为他偷了几句旧诗词,学着曲的口气一做,倒很是灵活。这一首诗的
意味,和第一首的情形,大大不同,象是觉悟了。”陈学平摇头道:“他哪里能觉
悟?他要觉悟,就不会死了。你再往后看去,你就明白了。”杨杏园道:“我不要
看了。与其我看了来猜哑谜,何不干脆请你说出来呢?”陈学平的肚子里,早也就
憋不住了,于是就把这一段小史说出来。
第七十三回 慷慨结交游群花绕座 荒唐作夫妇一月倾家
原来这任毅民家里倒也是小康之家。他的父亲希望他在大学毕业,得一个终身
立脚的根基,就极力的替他筹划学费,整千的款子汇到北京银行里来存着,让他好
安心读书,不受经济压迫。不料经济不压迫他,就放纵了他。他有的是钱,做了绸
的,又做呢的。单夹皮棉纱,全做到了,又要做西服。衣服既然漂亮,就不能在家
里待着。不然,穿了好衣服,给自己的影子看不成?所以天天穿了衣服,就到各繁
华场中去瞎混。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这三个地方,每天至少要到一
处,或者竟是全到。因此他的朋友和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三国巡阅使。他听到这
个绰号,倒不以为羞辱。以为朋友中只有我有钱,能够这样挥霍。这三园之中,男
的有每日必到的,女的也有必到的,彼此都是必到的,就不免常常会面。而且这些
地方去得多了,和戏场茶座球房的茶房,也就会慢慢认识。认得了茶房,这三园出
风头的是些什么人,无论是男是女,都可以打听了。
任毅民常遇到的,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郎。她也是今日梳一个头,明日换一件
衣服,时时变换装扮的人。任毅民看见,不免多注一点意。她出入三园,老和任毅
民会面,也就极是面熟。有一晚,任毅民在游艺园电影场里看电影。休息的时候,
见那女子也在那里,而且是一个人。任毅民便悄悄的问茶房道:“那个女孩子,常
到这儿来,你们认得她吗?”茶房笑道:“任先生连她都不认识吗?她就是杨三小
姐。”任毅民道:“她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堂里念书?”茶房道:“那可不知道。
反正她不怕人的,任先生和她交一交朋友,谈上一谈就全知道了。”任毅民道:
“我总看见她有两三个人在一处,今天就是她一个人吗?”茶房道:“就是她一个
人,今天要认识她,倒是很容易的。”任毅民听说,笑了一笑。一会儿工夫,那杨
三小姐,忽然离位走出场去,沿着池子边的路,慢慢的走着。任毅民一时色胆天大,
也追了上来。不问好歹,在后面就叫了一声密斯杨。杨三小姐回头一看,见是他,
也没有作声,也没发怒,依然是向前走。任毅民见她不作声,又赶上前一步,连喊
道:“密斯杨,密斯杨。”杨三小姐回头一笑,看了任毅民一眼。任毅民越发胆大
了,便并排和她走着。笑问道:“怎么不看电影?”杨三小姐却不去答他这句话,
笑道:“你怎样知道我姓杨?”任毅民道:“以前我们虽没说过话,可是会面多次,
彼此都认得的。要打听姓什么,那还不容易?”杨三小姐笑道:“你不要瞎说。我
看你还是刚才知道我姓什么呢。你和茶房唧唧哝哝在那里说话,口里说话,眼睛只
管向我这里瞧着,不是说我吗?我让你瞧得不好意思,才走开来的。”任毅民笑道:
“其实我们老早就算是熟人了,瞧瞧那也不要紧。”杨三小姐笑道:“我倒是常遇
见你,而且就早知道你贵姓是任呢。”两人越谈越近,便交换名片。原来杨三小姐
名叫曼君,在淑英女子学校读书,现在虽然不在学校里,自己可还是挂着女学生的
招牌。任毅民和她认识了,很是高兴,当天就要请她去吃大菜。杨曼君道:“我们
交为朋友,要请就不在今日一日,以后日子长呢。”任毅民觉得也不可接近得太热
烈了,当天晚上,各自散去,约着次日在北海漪澜堂会。
这个时候,还在七月下旬。北海的荷花,也没有枯谢。二人在漪澜堂相会之后,
任毅民要赁一只小游船,在水上游玩。杨曼君说是怕水,不肯去,也就罢了。过了
几日,这天下午,二人又在北海五龙亭相会,在水边桥上,择了一个座位,杨曼君
和任毅民对面坐下。任毅民坐了一会,然后笑道:“论起资格来,我是不配和你交
朋友。但是在我个人的私心,倒只愿我一个人和你常在一处,你相信我这话吗?”
杨曼君淡淡的笑道:“有什么不相信,男子的心事,都是这样的。”任毅民笑道:
“口说是无凭的,总要有一点东西,作为纪念,那才能表示出来。”说着,就在身
上将一个锦盒掏出,说道:“这是我一点小意思,你可以带在身上,让我们精神上
的友谊,更进一步。”杨曼君接过锦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人心式的金锁,锁
上铸了四个字,乃是“神圣之爱”,锁之外,又是一副极细致的金链子。这两样东
西,快有二两重,怕不合一百多元的价值。杨曼君笑道:“谢谢你。你送这贵重的
东西给我,我送什么东西给你呢?”任毅民道:“我们要好,是在感情上,并不在
东西上。我送这点东西给你,不过是作一种纪念品,何必谈到还礼的话。”杨曼君
笑道:“虽然这样说,我应该也送一样东西给你作纪念品才好。”说时,把一个食
指点着右腮,偏着头想了一想,笑嘻嘻的自言自语道:“我送你什么东西呢?”任
毅民笑道:“就是依你这种样子,照张六寸的相给我吧?”杨曼君道:“要相片子,
我家里有的是,何必还要新照一张?”任毅民道:“只要你给我东西,无论什么,
都是好的。”杨曼君笑道:“既然这样,我到水中间摘一朵莲花给你吧?”任毅民
道:“也好,但是你怎样得到手呢?”杨曼君道:“那还有什么难处?回头我们赁
一只船在水里玩,划到荷叶里面去,就可以到手了。”任毅民笑道:“荷花丛中,
配上你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姐,真是妙极。我是一个浑浊的男子,不知可配坐在后艄,
给你划船。”杨曼君眼睛一瞟,嘴一撇道:“干吗说这种话?那是除我不起了。”
任毅民因为上次请她坐船,碰了一个钉子,所以这几天总不敢开口。现在她自己说
出来了,自然是不成问题了。不过要把这句话说切实些,还得反言以明之,所以带
说带笑的试了一句。杨曼君风情荡漾的,反来见怪,那就是十分愿意同游的意思。
任毅民得了口风,赶快就要去赁船。杨曼君和他丢了一个眼色,笑道:“何必忙呢?
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阳光不晒人再去罢。”任毅民巴不得这样,她先说了,自然
是更好。坐了一会,又吃了些东西,等太阳偏西,然后赁了一只小船,划到北海偏
西去。一直等到夜幕初张,星光灿烂,方才回码头。
到了次日,任毅民是格外的亲热,雇了一辆马车,同她坐着到大栅栏绸缎庄去
买衣料。买了衣料,又陪杨曼君去听戏。听了戏,又上馆子吃晚饭。接连闹了几天,
杨曼君才慢慢高兴起来。以先任毅民说家里怎么有钱,父亲怎么疼爱他,杨曼君听
说只是微笑,并不答话,那意思以为任毅民是说大话。任毅民见她不相信,就不肯
再说,免得在朋友面前,落了一个不信实的批评。这一天下午,二人在公园里玩够
了,杨曼君要他在一家番菜馆里吃大菜,任毅民便陪着去。两人找了间雅座,一并
排坐下。杨曼君笑道:“今天不是我要你到这儿来,你一定不肯这样请我的,以为
这是小番菜馆子呢。”任毅民道:“我也不是那样的阔人,连这种地方,都当他是
二荤铺。况且这种地方阔人到的也很多呢。”杨曼君道:“我看你用钱,很是不经
济,大概你府上,汇的学费,不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