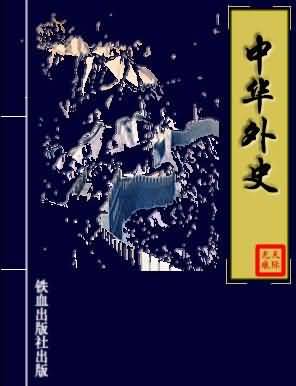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1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什么的,你知道吗?”茶房轻轻的答道:“是一个镇守使呢。打湖南来,还不到
两个月,在晚香玉头上,恐怕花了好几千了。”富家驹道:“他叫什么?”茶房道:
“名字我可不很清楚,只知道他姓马。”富家驹道:“他叫晚香玉来,今天是初次
吗?”茶房道:“不,好几天了。”说毕,昂头想一想,笑道:“大概是第四天了。”
富家驹听了这一套话,心里真是叫不出来的连珠苦,在浴室里先洗了一个澡,然后
上床才睡。但是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睡了半天,又爬起来打开房门。在夹道里
张望张望。见茶房都已安歇了,走近隔壁的房间,便用耳朵贴门,听了一阵。那里
虽然还有一点叽叽咕咕的声音,但是隔着一扇门,哪里听得清楚,空立了一会子,
无精打彩的回房,清醒自醒的睡在床上,自己恨晚香玉一会,又骂自己一会,一直
听到夹道里的钟打过四点才睡着了。
第六十五回 空起押衙心终乖鹣鲽 不须京兆笔且访屠沽
富家驹次日醒来,已是十一点钟,洗了一个脸,茶也没吃,慢慢的就走出大门。
只见田大妈坐了一辆人力车迎面而来,富家驹见了她,她却没有看见富家驹。车子
到了饭店门口,就停住了。田大妈给了车钱,开步就要向里走。富家驹忙叫住道:
“田大妈,这样早到饭店里来找谁呀!”田大妈一回头,看见富家驹,脸上立刻变
了色,红一阵,白一阵,张口结舌的说道:“大爷你早呀,在哪儿来?”富家驹微
笑道:“昨晚上我没回去,住在这饭店里,刚才起来呢。”田大妈道:“我说呢。
昨天晚上太晚了,回不了家,这可真对不住。”富家驹笑道:“是我懒得回去,不
是不能回去,也没有什么对不住。田大妈这时候来了,到饭店里找谁?”田大妈道:
“上海来了一个人,要请我们姑娘到上海去,我去回断他呢。”富家驹道:“这是
好事呀,回断他作什么?”田大妈道:“咳!话长,再谈罢。”田大妈说完这话,
匆匆忙忙,就进饭店去了。富家驹在街上雇了一辆车,垂头丧气的回家。一进房门,
就见钱作揖留了一个字条在桌上。拿起来一看,上面写道:“老富,昨晚上乐呀,
这时候还没回来。钱留字。”富家驹也不知道心中火从何处而起,一把就将它撕了,
扔在地下,便倒在床上,摇着两只腿想心事。听差走进房来说道:“后面杨先生说
了,您回来了,请您到后面去坐坐。”富家驹正也没了主意,和杨杏园谈谈解闷也
好,便走到后面来。只见杨杏园捧着一本英文书,躺在沙发椅上看。富家驹道:
“杨先生还是这样用功。”杨杏园将书一扔,笑道:“我很有到美国去玩一趟的野
心,所以几句似通非通的英文,总不时的温习一两回,以备将来出洋应用。其实这
倒是妄想了。我要是能和贤昆仲掉一个地位,我这个希望,就不成问题。可是天下
事就是这样,想不到的难于登天,想得到的,反而看作平常。”富家驹心虚,生怕
杨杏园绕着弯子说他,未免脸上红了起来,笑道:“这些日子,我实在荒谬极了,
学校是没有去,钱倒花得不少。从今日起,我要改过自新了。”杨杏园笑道:“你
怎样忽然觉悟起来了?”富家驹叹了一口气道:“咳!我到今日,才觉得娟优并称,
实在是至理。把爱情建筑在金钱上,那完全是靠不住的。”杨杏园道:“我看你这
样子,定受了很大的刺激,何妨说出来听听。”富家驹道:“我真不好意思说。因
为杨先生劝我多次了,我总是不觉悟。”杨杏园笑道:“这样说,大概是晚香玉的
事了。她有什么事对你不住吗?”富家驹也不隐瞒,就将自己昨夜在晚香玉家打牌,
和在饭店里碰到晚香玉的事,一一说了。杨杏园笑道:“你这弄成了偷韩寿下风头
香了。”富家驹道:“说出来,杨先生或者不肯信,连这个偷字,我都是不能承认
的。我想,我昨晚倒住在上风,可是晚香玉的香味,倒在下风头了。”杨杏园不觉
触起他的旧恨,长叹一声道:“都道千金能买笑,我偏买得泪痕来。老弟,你能觉
悟,花了几个钱,那不算什么?以后还是下帷读书罢。象你这样年轻,前途大有可
为。在花天酒地里,把这大好光阴混了过去,岂不可惜?不是你自己说破,我也打
算劝你一番。现在你已在情场上翻过筋斗,这话,我就不用得说了。”富家驹道:
“杨先生常常看佛书,要怎样入手。一定知道。象我们从来没有研究过佛学的人,
也能看佛书吗?”杨杏园笑道:“何至于此,受这一点刺激,你就看破红尘了吗?
老实说,佛家这种学说,把世事看得太透彻了,少年人看了,是要丧元气的。”富
家驹道:“那末,杨先生为什么看佛书呢?”杨杏园道:“我是老少年了。你我何
可并论?况且就是我许多地方,也未能免俗,这佛书算是白看了。我以为倒不必看
佛书,就是把你所研究的功课,设法研究出一些趣味来,那些牢骚,自然也就会丢
掉的。”富家驹道:“从今天起,我要把功课理一理了。况且不久就要年考,真要
闹个不及格,那倒是笑话。”杨杏园笑了一笑,也没有说什么。
在这一天下午,杨杏园接到李冬青一个包裹,里面是几件衣服,要杨杏园转交
给史科莲的。杨杏园便打了一个电话给史科莲,问道:“衣服是送过去,还是自己
来取?”史科莲说:“自己来取,请明天上午在家候一候。”到了次日,史科莲果
然来了。杨杏园道:“年考近了,密斯史,还有工夫出门?”史科莲道:“嗐!不
要提,为着一个同学的事,忙了四五六天,还是没有头绪。”杨杏园笑道:“大概
也是一个奋斗的青年。”史科莲道:“从前也许是奋斗的青年,现在要做太太了。”
杨杏园道:“这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事,可以宣布吗?”史科莲笑了一笑道:“我想
不必我宣布,杨先生也许知道,因为这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杨杏园道:“是
了,仿佛听见人说,贵校有个学生,好好的跳楼,就是这个人吗?”史科莲道:
“正是她。”于是把蒋淑英和洪慕修一番交涉,略略说了一遍。又说:“蒋淑英为
洪慕修的交涉跳楼,她跳楼之后,还是到洪家去养病。她的情人张敏生,因为和我
见过两次面,麻烦极了,天天来找我,叫我给他邀密斯蒋见一回面。我本想不理他,
但是我看他实在受屈,所以曾去见了密斯蒋两次。真是奇怪,那密斯蒋住在洪家,
竟象受了监禁,一切都失却自由,我真替她不平。”说时,脸也红了,眉毛也竖了,
好像很生气似的。杨杏园笑道:“早就听见密斯李说,密斯史为人豪爽,喜欢打抱
不平,据这件事看起来,真是不错。”史科莲道:“并不是我多事。密斯蒋和我相
处很好,差不多成了姊妹了。我见她被那个姓洪的软禁,非常的奇怪。我们既没有
写卖身字纸给人,这个身体总是我自己的。为什么让人困住家里,不能出大门一步
呢?”杨杏园道:“北京是有法律的地方,那姓洪的把密斯蒋关在家里,那和强盗
差不多,是掳人绑票。可以叫那姓张的,以密斯蒋朋友的资格,告姓洪的一状。”
史科莲道:“我也这样想过,可是密斯蒋不承认姓洪的关住她,那又怎么办呢?”
杨杏园道:“她不至于不承认。”史科莲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生气呀!昨日
我到洪家去了一趟,我告诉她:‘姓张的天天找你,你应该去见他一面。’她说:
‘我姐夫不让我出门,我也没办法。’我说:‘行动自由,你姐夫还能干涉吗?’
她说:‘并不是他干涉我,他总劝静养,我不能拂他的情面。’杨先生,你想这人
说话怪不怪?为顾全情面,闹得行动都不能自由了。”杨杏园听了她的话,仔细一
揣想,不觉笑了起来。说道:“她的话,说的并不可怪,不过密斯史没有听懂,觉
得倒可怪了。你想,一个天天要她来,她不来,一个随便一留,她就不去。这哪里
是人家软禁她?分明是自己愿要受软禁。我看她和姓张的要绝交了,你不管也罢……”
杨杏园说时,望着史科莲,似乎下面还有话,他忽然淡笑一下,又收住了。史科莲
道:“我看也是如此。不过我很替她发愁,她若是不回来,学业固然是荒废了,恐
怕还不能得着什么好结果。我今天还去看她一次,作为最后的敦劝。她真是不觉悟,
那也就算了。”杨杏园笑道:“不必了。天气很冷的,在路上跑来跑去,为别人喝
饱了西北风,人家也不见情。不如在我这里便饭,然后将我的车子送密斯史回校去。”
史科莲道:“冷倒不怕,就是怕去了,遇见那个姓洪的。我看见他那种殷勤招待,
一脸的假笑,就觉有气。”杨杏园笑道:“幸而密斯史到我这儿来,我很随便的。
不然,密斯史倒要厌我一派虚情假意。”史科莲笑道:“我说话是不加考虑的,杨
先生不要疑心。”杨杏园笑道:“我也用不着疑心,冈为我招待得很冷淡呢。”正
说到这里,只见听差托了一个托盘,端着一壶咖啡,两碟奶油蛋糕,送到茶几上来。
听差将咖啡斟了两杯,自走出去了。杨杏园搭讪着将糖罐子里的糖块,一块一块,
望着咖啡杯子里放。史科莲见他一直放下五块糖,还要向下放。不觉笑道:“你既
喝咖啡,为什么又这样怕苦?”杨杏园道:“我并不怕苦。”史科莲道:“既不怕
苦,为什么要放下许多糖呢?”杨杏园这才省悟过来了,一看手上,两个指头,还
钳着一块糖呢。史科莲一说破,越是难堪。便笑道:“我听了密斯史所说密斯蒋的
事情,我正想得出了神,我不知所云了。”史科莲也略略看出他的意思,并不客气,
一面喝咖啡,一面吃蛋糕。因为这样,杨杏园也不便再说请她吃饭,又谈了一会,
史科莲告辞要走,约了年考考完,再来畅谈。杨杏园和她提着东西,送到门口,看
她雇好了车子,上了车,才转身进去。
史科莲到了洪家,一直进去,只见蒋淑英围着炉子,在那里结红头绳的衣服。
她见史科莲进来,连忙将那衣服,交给旁边的老妈子,让她带去。笑问史科莲道:
“学堂里问了我吗?我现在身体全好了,决计明后天回学校去。”史科莲见屋子里
并没有人,便问道:“你这话是真的吗?”蒋淑英脸一红,说道:“我前前后后想
了几夜,觉得还是回学校去的好。况且年假到了,我总要去考一考。”史科莲见她
已这样说了,当然用不着劝她,而且谈了没有多久,洪慕修就回来了。自己不愿多
坐,便回学校去。
洪慕修笑问蒋淑英道:“你这位同学,年纪很轻,衣服又很朴素,倒觉得淡雅
宜人。”蒋淑英道:“你不要看她年纪轻,她很能奋斗,她现在念书是她一个人的
举动哩。”洪慕修道:“这过渡的时代,青年男女,真是危险,据我看,十人就有
九个发生了婚姻问题的。”蒋淑英道:“你不要瞎说,她自己念书,是因为她寄住
在亲戚家里,不愿看人家的眼色,因之离开那些人,自己干自己的,并不是为了婚
姻脱离家庭。她自己的婚姻,我想她一定能完全作主,谁也干涉不了,谁也破坏不
了。”洪慕修觉得话中有刺,笑道:“那是自然,谁也不能干涉谁。”蒋淑英趁着
这种说话的机会,便对洪慕修道:“姐夫!我在这里叨扰许多天,我实在不过意,
我要回学校去了。”洪慕修听她这话,脸上并不表示诧异,很自然的答应道:“二
妹怎样客气起来了?我怕你是把话反说,觉得有什么事不安适了。”蒋淑英道:
“笑话了。姐夫这样招待,还有什么不安适?我到姐夫这里来,原是养病。现在病
既好了,我怎样还在这里叨扰?况且马上要考年考,我当然要回学校去考的。不然,
我岂不要留级?”洪慕修道:“那是当然。今天晚上,二妹不必去,明天去罢,用
功也不在这一天。今天晚上,我请二妹吃小馆子,吃完饭,一同去看跳舞,这算我
是欢送你。”蒋淑英道:“我又不出京,欢送什么?”洪慕修道:“实在因为令姊
去世以后,你帮我不少的忙,这算是我酬谢你。”蒋淑英道:“这样说,我越发不
敢当了。”洪慕修笑道:“其实都是笑话。不过因为留洋学生会,今天晚上开纪念
会,我有两张票,顺便请一请你。”蒋淑英向来就羡慕这种文明的集会,听了洪慕
修这样说,便欣然的答应去。
一到了六点钟,洪慕修先换上了一套极漂亮的西服。便问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