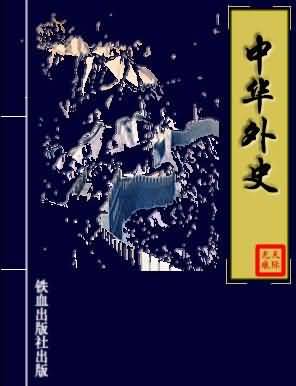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园笑道:“算了,我算已经长了见识了,你们二位自己去逛罢,我不奉陪了。”史
诚然笑道:“这是南式的。还有北式的,你没见过,不去吗?”杨杏园摇摇头道:
“不去!不去!”便雇了一辆车子,自回会馆,陈若狂等他上了车子,叫住道:
“杨先生,杨先生。”杨杏园便叫车子停住,问“什么事”?陈若狂想了一想,笑
道:“明早奉访,再谈罢。”杨杏园见他不说,也不再问,坐车走了。
到了次日,一早陈若狂就来了。杨杏园知道他是来借钱的,故意装作不知道,
看他怎样开口。陈若狂道:“杨先生,昨天的事,对你不住,隔日再奉请。”杨杏
园道:“我这几天很忙,胡同里倒没有工夫去。我们这些吃笔管儿的,这些化钱炉
的地方,哪里能常去呢。”陈若狂道:“你这话真对。不瞒你说,我就为这个,闹
了一身亏空。我门部里那班同事,逛起来,都不知死活的,盘子钱,一给总是五块
十块的钞票。我跟着他们一处闹,哪里能不照样呢?前天晚上,和我门一个参事去
捧场,偏偏我不走运,一输就是七十多块,这两天就闹得山穷水尽了。昨天那一趟,
笑话极了,实在是不得已。”说到这里,现出很踌躇的样子,笑着说道:“我还做
了一件缺德的事呢。前儿晚上,遇着部里几个混小差事的。硬要拉去逛二等,也偏
偏凑巧,遇着他们打鼓,我打了一场赊帐的牌,约着今天给人家钱呢。”杨杏园笑
道:“什么叫作打鼓?”陈若狂道:“就是北班子里所谓开市,不过借故向客人敲
竹杠罢了。因为他们这一天,要叫一般唱大鼓书的在窑子里唱大鼓,意思是请客人
去听,所以就简称为打鼓。”杨杏园笑道:“这名词真有点俗不可耐,但是你刚才
说,前天晚上和你们贵参事捧场,怎样又逛二等去了呢?”陈若狂红着脸道:“捧
场那是大前天晚上的事,我正为了这个为难。但是数目太少了,不是极熟的朋友,
又不好开口,所以我托史诚兄转恳你老哥,想通融个十元以内的数目。”杨杏园笑
道:“这点事,我还可以帮忙,但是阁下似乎不至于困难得这样。”陈若狂道:
“不瞒你说,报馆里虽然一个月给我一百元的薪水,其实这位王天白经理,是有名
的光棍,口惠而实不至的。部里的薪水,上月份早用光了,这一个月,还没有消息
呢。我现在维持现状,全靠上海方面特约小说的一笔款子,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
这款子不久也就要汇来了。那时候,我一定奉壁。”杨杏园道:“像我们这班人,
都不在洋场才子之列,想加入卖小说的这一党很不容易的。你居然能拿一百多元一
月,自然也值四元一千字,这个资格你如何混到的呢?”陈若狂含糊答道:“这算
什么!我有一位朋友,他一部小说,只做了十二回回目,就得了五百块钱,这比四
元一千字,不更值钱吗?”杨杏园道:“我仿佛也听见有这一种传说,当真的吗?
这到底是哪家书局出的呢?”陈若狂笑道:“中国哪有这大资本的书局!这是某部
一个参事出的。原来这参事有三个儿子,都和他姨太太发生关系,大儿子逼得跑了,
二儿子娶了媳妇,被这位姨母霸占不能进新房,闹出许多婚姻问题的笑话。我那位
朋友,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打听了一个详详细细,随便和他经理谈起来。他的经理
说:‘这种官场五历史,着实可以替他铺张一下子,痛痛快快骂他一顿。你的笔底
下很俏皮,可以作一篇小说,在我们报上发表。’我那朋友,自然奉命维谨的做起
来,因先拟了十二回回目,请他的经理斟酌一下子。他的经理说‘很好,今天就可
以先把回目发表。’这一来不打紧,可把那活乌龟急坏了。他想上次通信社发了一
篇新闻稿,已经够瞧的了,再要做出小说来,这一个小小前程,恐怕靠不住。只得
托人向我那朋友的经理商量,情愿出点代价,收买他的版权,由三千块讲价,直讲
到五百块钱成交,这一部小说就此无影无踪。这不是十二回回目卖了五百元吗?”
杨杏园笑道:“你这话告诉我是不要紧,若是告诉了别人,在报上索性来个新闻界
之新闻,又要生出许多是非呢。”陈若狂道:“我原知道你是一个不管闲事的人,
我才告诉你。”说着又把许多的话,来恭维杨杏园。杨杏园等他恭维够了,才拿出
一张五元的钞票交给他,说道:“我这两天也闹饥荒,对不住,只有这个数目,你
带着使罢。”陈若狂接着钞票道:“是是!我很能原谅的。”说了几句话,他就走
了。
原来他在二等窑子里留宿过多,身上已经染了许多毛病,这个时候,他正在害
淋症。头里两天,他并不知道,每天晚上,依旧到二等茶室里去胡缠,后来觉得坐
久怪不方便,又很痛,在小解的时候,低头一看,嗳呀,下身全不成个样子了。那
一股腥气,触着鼻子,不由得人要作呕。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常听人说什么
淋症,就是这个东西吗?这如何是好呢?这是平生破题儿第一遭的事情,又不好意
思问人怎样医治,仿佛记得报上不要紧的地方,那卖药的广告里面,有什么五淋白
浊丸之类,从来没有注意过,现在何不查它一查。想着,就把所看之报纸,翻了几
种。这一查,长了许多见识,才知道这个症候,有许多名目,和许多关系。不过卖
药的广告,都说他的药好,不是一个礼拜断根,就是不灵还洋,或者是一用就好。
到底买哪一样好呢?拣来拣去,就从中拣了一样定的价钱最贱,说得最有效验的丸
药,买了一瓶。谁知这种药,报上的广告,尽管说得灵验,吃了下去,却不见得好
在哪儿。他既不好意思问人,更不愿意到医院里去诊治,就依旧在报上广告栏里胡
乱再去找丹方。甚至胡同犄角上,禁止小便地方,所贴那些花柳专科的广告,也偷
着瞧它一下。于是今天换一样丸药,明天换一样丹方,闹了整个礼拜。到底后来打
听了一种西药,叫做什么“三代爱美”的,都说很有效力,他就去买了一瓶试试,
吃下去觉得毛病好些。可是这样东西,贵得厉害,一瓶只能用一昼夜,价钱却是两
元五角。他为医病起见,没有法于,只好咬着牙齿去买,不上十天,已经花了不少
的钱。他问杨杏园借钱,正是为医治淋症。昨天晚上,极力敷衍杨杏园,无非是想
多借几个钱,把病诊好。
谁知他淋症好了,别的病又发了,从这天起,精神疲倦得很,四肢常常作寒作
热。心想这是小病,不要紧的,也就没有理会。他报馆里除了那位王天白而外,还
有一位编辑,这人就是杨杏园同乡黄别山。他看见陈若狂一天疲倦一天,便道:
“若狂,我看你脸上一点儿血没有,你表面上虽能支持,你内症可是很重,我劝你
还是找个大夫瞧瞧罢。你不信,你把镜子照照你已经不像个人样了。”陈若狂听了
这话,当真把镜子一照,果然眼睛陷下去许多,脸上白里转青,像蜡人一样,不觉
吃了一惊。心想:“我不过是一点小小感冒,怎样病得这般厉害,再要不医治,恐
怕真要成大病了。”他决定的主意,就到他一位同乡陈大夫那里去诊病。这人认识
的阔人很多,是由十多名同乡议员,公函警厅,保准了的免考医生。手段虽不能十
分高明,门诊费却走二元,出诊也是五元起码。北京阔人有个最怪的脾气,是爱贵
不爱贱,所以他的生意,居然很好。这天陈若狂到他那里去瞧病,因为同乡的阔人
都信任他,以为总不会错的,所以并没有考虑,一直就来。他到了医生家里,照例
出了两块钱挂号,那门房把他引进一门诊病室里来。这屋子里,也有些字画文玩之
类,却一大半是同乡官员的下款。一张横桌里边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在那里看
群强报。见他进来,很客气的,请他坐下。陈若狂见他那样子不像是医生,也不像
是仆役,倒看不出所以然来。那人等陈若狂坐了,问了他的姓名籍贯住址,拿出一
张诊病单来,给他一一用笔填上,然后再去请医生出来。陈若狂这才知道他是医生
的助手,心想到底大名家的气派不同。一会儿医生由外面进来,有五十来岁年纪,
嘴上略略有点胡子,穿了一件旧罗长衫,斯文一脉的,态度很为从容。他对陈若狂
微微点了一个头,请他在一张横桌边坐下,自己对面坐下,先把那单子看了一看,
然后问道:“陈先生是什么病?”陈若狂道:“身上时寒时热,四肢无力,只觉疲
倦得很,胃口也坏,一点儿东西不想吃。”那陈大夫点点头,头里那个开单子的人,
取过一个小小的布枕头放在桌上,陈若狂知道这是按脉的,便把手放在上头。那陈
大夫伸出一只手来,按住他的脉。他那指甲,都有一寸来长,他只管歪着一个脑袋,
凝住神数脉息,用手极力的按脉,那指甲直陷入陈若狂的肉里,戳着生痛。一会儿,
陈大夫把两只手的脉按完了,便对陈若狂道:“不要紧,这是受了一点风寒,吃一
两剂药就好了。”说毕,翻开桌上雪亮的铜墨盒,拿起笔来,在那诊病单上,开了
几句脉象和病由,后面就狂草一顿,开了十几味药。陈若狂所认得的,有什么荆芥
一钱,防风一钱五,紫苏一钱,厚朴一钱,柴胡一钱五,姜制生附子一钱,干姜一
钱,其它各样,还有他不认得的。陈大夫开完了药方,在抽屉里面,又拿出一颗象
牙图章,在单子上盖了一方鲜红的印。然后交给陈若狂,说道:“先吃两剂,好一
点就不用来瞧了。”陈若狂应了几个“是”,就出了陈大夫家里,转回幸福报馆。
谁知来的时候,还能走几步路,这回去的时候,心里十分难过,身子有点支持不住,
恨不能马上就在街上躺下。也没问车钱多少,雇了一辆车子就坐回来。到了家里,
自己便倒在床上,将药单交给一个听差,教他买药就煎,也没有给第三个人知道。
谁知这个药,虽然不上二两,吃下去,效验很大,这天晚上,陈若狂大烧大吐,浑
身骨头,酸痛难言,不住的只是哼。他这样子,病是已经很重了,应该要好好的静
养,这幸福报馆内,又极嘈杂不堪。那位王天白社长,是一位大交际家,报馆里办
事的人,不过两三位,住闲的人,倒有七八位。这班人多半是来京找事的,住在报
馆里,除了白吃白喝,还可以挂个新闻记者的名义,比住公寓会馆就强的多。这闲
客里面,虽然是吃白食的,也很有人才。有一位德国留学生,他学的是螺丝钉专门
学,有一位是前清候补道,还有一位是张勋部下的副官长。就把以上三位来论,可
见幸福报的座上客,也是应有尽有。这些宾客,一天到晚,无所事事。除了出去找
朋友而外,到了报馆里,就是坐在一处,高谈阔论,研究时局。他们研究时局的屋
子,正在陈若狂房的隔壁,在平常的时候,陈若狂听他们说话,也不过认为无聊,
现在在枕头上听着,只觉吵得头痛,但是也没有权可以干涉人家,只是心里头骂,
恨不得把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给他轰出报馆去。
他一病三日,那陈大夫开的药方,已经吃了两剂,不但是没有治好一点病,简
直火上加油,把病越发引了上来。在陈若狂以为自己的病,不过是风寒小症,也知
道陈大夫药方,大半是发散的,吃下去,病不好,也不至于坏事。到了第四天,陈
若狂便昏昏沉沉的睡着,有时候清醒过来,只觉得浑身酸痛,两只大腿,一点儿也
移动不得。除了黄别山晚上到报馆里来的时候,去慰问他外,谁也不理他。至于王
天白社长,因为欠着纸行里印刷费,正在外面设法,更没有工夫问他的病了。陈若
狂的收入,本来有限,他对人说,那里几百,那里几十,那都不是实帐。在他这病
的时候,部里固然已经欠薪几月,报馆又正在闹穷,他分文莫进,正所谓贫病交迫。
不但没有人为他医病,就是有人为他医病,这笔医药费也是无所出啊。陈若狂病到
第四天以后,已经没有吃药,病也不见得加重,只是昏昏沉沉的要睡,就是有一两
个人来看看他,也以为他的病要好了,不很注意。说起来很快,一过就是一星期。
这天晚上,黄别山将事办完,特地到他屋子来看他,只见他盖着被服,歪着头朝里
睡。在电灯底下,看见他耳朵背后,发起一块一块的红疤,因便上前来细看。这时
陈若狂知道有人来,便将被服一掀,翻了一个身。他这一掀被服的时候,一股热气
往外一冲,黄别山便闻着一阵又腥又臭的气味,不觉倒退几步,一阵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