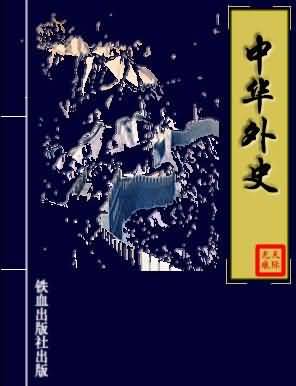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10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吃小馆子。吃了小馆子,又去逛胡同,走了两家,我硬抽身跑来了,他们还在等我
呢。”杨杏园道:“国家养你们这班官,不发薪呢,就怨天恨地,说是枵腹不能从
公,发薪呢,你们又花天酒地,把办公做个幌子。”华伯平笑道:“得了得了,不
要发议论了,你拿画给我瞧罢,我还要走呢。”杨杏园看他那种急的样子,知道他
不能久等,便把画拿给他看。这画是个小中堂,画着半勾霜月,一角孤城,城外一
片沙漠,两个游骑,向城门飞奔而来。纸却是雪白的。华伯平道:“这并不是古画。”
杨杏园道:“本不是古画,你且看看那落款下面的图章。”华伯平仔细看了一看,
乃是“伯秋之章”四个字。华伯平道:“哦!是他画的,他是我的同乡,做江西吉
安县知县,没到任落水死了。”杨杏园道:“不错,就是他,他叫赵伯秋,十年前,
在江西做官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你看这一轴画能值多少钱?”华伯平道:“这
一轴画,卖给外省人,他当一轴平常的画买去,出不了什么大钱。你卖给我,算是
找着主顾了。我出一百块钱罢。”杨杏园道:“你不把它当骨董,我可把它当骨董
哩。老赵的画,我家里一共只有三轴,卖了可没地方找去。你要买,就出一百三十
块罢。”华伯平笑道:“原来是你的画,我不能要。明天同乡知道,说我华伯平挣
了几个钱,把朋友收藏的东西,都搜括了去,岂不是笑话?”杨杏园笑道:“你不
要瞒我,你不是收藏家,你哪有闲钱去买这个?你买了去送老头子的礼,对也不对?
就是你买,那也不要紧,朋友就不能作买卖吗?”华伯平道:“你的话,猜是猜着
了。据我说,我出一百不少,你就要二百或一百五,以所爱之物而论,也说得过去。
何以单单要一百三十元?”杨杏园道:“我有一笔费用,差一百三十元,所以想卖
这个数。”华伯平道:“你有什么费用,结婚费吗?若是为这个,我借一百三十元
给你。要你卖东西,就不够朋友了。”杨杏园道:“不是,不是。有东西买,岂不
很好,我何必负债。”华伯平道:“虽然,你这话还是可疑,设若你东西只值十块
钱,你因为要一百三十块钱,也卖那个数吗?再说你差一千呢,就要卖一干吗?”
杨杏园道:“你是做买卖来了,还是论逻辑来了?”华伯平道:“好!我就出一百
三十元,不和你争了。不过我想你不嫖不赌,哪里会钻出这一笔费用。”杨杏园笑
道:“将来也许可以告诉你,现在因某种关系,要守秘密。”华伯平见杨杏园一定
不肯告诉,只得罢了。便说道:“画我是不要你的,我明天叫人送一百三十块钱过
来得了。”杨杏园道:“我在客中,这轴画我留着也没有地方去挂。挂起来,也没
有相当的骨董来配,我还是卖了的好,省得负债。你就把画拿去罢。你若不要画,
还说我用手腕来借钱呢。”华伯平道:“笑话,我哪有这种意思?”杨杏园道:
“你不要画,我就不借你的钱。”华伯平没法,只得把画拿走了。他想道:“杨杏
园为什么不肯负债呢?这一定是结婚。大概不愿在新夫人面前露出穷相,所以宁愿
卖掉这可有可无的画。”他知道杨杏园等钱用,第二天,居然起了一个早,九点钟
就派专人把钱送了来。杨杏园将钱拿到,也没有停留,就把钱送到李冬青家里去。
李冬青恰好这天上午无事,还在家里。杨杏园来了,便出来在客室里和他见面。
杨杏园将钱如数交给李冬青,问道:“够不够?”李冬青道:“足够了。总要多个
三十块钱呢。”杨杏园道:“那就很好。密斯史这时进学校,哪里不要用钱,就留
着她零用罢。”李冬青用手扶着茶几,轻轻的抚摩着,眼睛又望着手,沉思了一会。
然后微笑了一笑,对杨杏园道:“这个钱,几时要用?”杨杏园笑道:“还打算还
我吗?我要加一的利呢。”李冬青对这一句话,就不好答了。理由是为什么借钱不
要还?可是在彼此的友谊上,又绝不许计较金钱问题。一定要谈有借有还,就太俗
了。她的脸太嫩了,这一急,却急得满脸通红。但急中生智,也答应一个不着边际。
便笑道:“加一的利,也不算重。借来的钱,至少也是三分利,这也不过赚六分罢
了。”杨杏园道:“我并不是借来的。”李冬青笑道:“不要相瞒。第一次,尊囊
就给我搜括无遗,哪里还有储蓄?越是这样说,我越过意不去”。杨杏园道:“自
然不是储蓄,是我把一轴画卖来的钱。”李冬青道:“这就对不住了。回头密斯史
又要说许多不安的活。”杨杏园道:“不不!这事我是不出面的。在史女士面前,
千万不要说是我的款子。因为……”李冬青知道他的意思,第一,他和史科莲,没
有很重的友谊,这样帮助,有些躐等。第二,也决不愿意在自己面前,对女朋友卖
这一个大人情,第三,他这个人情,并不是对史科莲而发的。便笑道:“这是怎么
说呢?难道我乞诸其邻而与之,就这样示惠吗?其实第一次那一笔款子,我就实说
了。”杨杏园道:“并不是我矫情,因为史女士现在的环境,是不适用‘嫂溺援之
以手’那句话的。”李冬青道:“既然如此,我叫密斯史保守秘密得了。”杨杏园
觉得“秘密”这两个字,又有些刺耳。笑道:“那也无所谓。”自己说了这无所谓
三个字,却也不知何所谓。便搭讪着说:“我家里还有事,我要回去了。”说着,
站起身来便走。李冬青照例送到大门口,然后拿了钱进去。
这几天史科莲和李冬青同睡,没事却在那间小书房里看小说。刚才李冬青和杨
杏园所谈的话,她句句都听见了。李冬青拿了钱进来,一把就递给史科莲,说道:
“这全够了。好了,明天你可以去上学。”史科莲道:“真难为你,给我搜罗许多
钱来。”李冬青道:“我哪里有许多钱,还不是那位杨先生办的?”史科莲道:
“他帮我这一个大忙,我心里真过意不去。”李冬青道:“他不但帮你的忙,他也
知道你要感他的情,却叫我不要说出来是他的钱呢。”史科莲道:“既然如此,我
尊重杨先生的意思,只感谢密斯李。”李冬青道:“杨先生帮你的忙,你何以感谢
我?”史科莲笑道:“若不是你认识杨先生,他又怎样能帮我的忙呢?我感谢你,
你自然要去感谢他,这手续就不错了。”李冬青道:“这无所谓手续,也无所谓感
谢。是杨杏园说的,乃朋友应尽之义务。”史科莲道:“这样说,就完全便宜我了。”
李冬青有一句话要说,几乎要说出来,又忍回去了。只笑了一笑。
史科莲得了这笔钱,是满天愁云尽散,脸上的笑容,也就止不住显出来。到了
次日,她就离了李家,搬到学校去。学校里的生活,那都是有秩序的。而且耳所闻,
目所见,都离不了功课。和余家那种繁华家庭的状况,自己寄人篱下的环境,完全
不同。不说别的什么,第一吃一碗安心饭,不看人家的眼色。这时史科莲除了挂念
祖母是一桩心事外,竟成了个自由之神。好在余瑞香始终和她不伤友爱,不时写信
给她,报告外祖母平安。史科莲因此乃安心去做她的功课,满打算毕业而后,学着
李冬青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到自己之所以有今日,到底不能不感谢杨杏园。
很快的工夫,一个星期又过,大家都换了夹衣。史科莲得了杨杏园第一批款子,绸
缎未雨,早把夹衣作好,这时也全身更换起来。她又想,若不是杨杏园,莫说读书,
第一项这衣服问题,就不得了。他虽然不要我感谢他,我究竟受之有愧,因此她就
当在她寝室里的时候,用自来水笔,写了一封信给杨杏园。那信道:
杏园先生:我写这封信给您,实在冒昧得很。因为您极力的协助我,是不愿意
我知道的。我这时写信和您道谢,岂不有伤您的本意吗?不!这事在您那一方面,
可以这样设想。在我们受惠的人,良心上,却不能容许我缄默。所以我于尊重尊意,
和安慰我良心的两方面,转来转去,费了一个礼拜的研究。结果,良心战胜了友谊,
我只得冒着不是,写信给您道谢。道谢两个字,实在形容不出我心中的感激,但是
我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我是一个没有学问,而又穷无所归的女子。我不信这世
上人,除了李冬青之外,还有几个人能看我一眼。现在我知道不然了,天地之大,
不少好人,只是难以遇着罢了。学校里的生活很好,由前十天的我,变到现在的我,
我简直得到第二个生命。生平的快事,莫过于此。在这种良好环境里,我现在除了
思念一个寄人篱下的六旬祖母而外,没有别事,只是尽力的奋斗。这是可以报告助
我的朋友的。我不长于文字,写得不成东西,求您原谅。即颂文安。
史科莲 谨启
这一封信,觉得是一种可纪念的东西,杨杏园连信纸信封,一并收起来,放在
一个收文件的小匣子里。又想不能默尔受之,也就拿了一张信纸,回了一封信,无
非是自己谦逊一番,又勉励史科莲几句。写完了。就交给听差寄去。当听差将这封
信拿走之时,恰好吴碧波前来拜望他。吴碧波的目光,最是锐利,远远的看去,已
经看见信封上有女士两个字。一脚踏进门,看见他的书桌,笔还在砚池边斜搁着,
便笑着问道:“来的不巧,又要打断你的诗兴吧?”杨杏园道:“作什么诗,几个
月也诌不出七个字来哩。”吴碧波道:“你看,笔还搁在砚池上,大概正是工作时
间。”杨杏园道:“见面很少,既然来了,多坐一会儿,畅谈畅谈。我这时不作事,
刚才是写一封信。”吴碧波就故意问道:“写信给谁?让我来做一回福尔摩斯。据
我想,这封信,很简单。你看,那一盒信纸,不是像没动一样吗?大概不过一两张
八行。既然很少,当然是不重要的。可是你写好了就封,封了就寄,一定又是急于
要答复的。因为墨汁还没有干,信已不在桌上,当然是写好就付邮了。这封信,大
概是寄给朋友,不是家书。要是家书,发得这样匆促,你岂能态度还这样安闲?再
说这封信一定是寄给一位极好的朋友。我是知道的,你有一个坏脾气,把写信认为
最便宜的事,却往往因此延搁下去。有许多要紧的事,都耽误了。你若不是写给好
朋友,不能这样留心。这是我一分钟内理想和观察上得来的推测,你看对不对?”
杨杏园笑道:“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一封信罢了,值得这样研究?来来来,我们
下盘围棋。”吴碧波知道杨杏园有三不高明,下围棋,猜诗谜,拉胡琴,都是最爱
又够得上打零分的。这时他发起下围棋,决不能这样不量力,分明是王顾左右而言
他。也就笑道:“你那种棋,罢了。”杨杏园听说他不下棋,也就一笑而罢。问道:
“你怎样有工夫出城?”吴碧波道:“罢了课了。”杨杏园道:“上半年罢课罢了
两个月,你们已经玩够了。下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个星期吧?怎样又罢课?”吴碧
波道:“上半年为教员欠薪罢课,原来没有解决。下半年,是财政部答应给钱,才
开学的。开了学,财政部不给钱,校长受了骗了,教授们一恼,又罢课了。”杨杏
园道:“上半年记得罢了两次课了吧?”吴碧波道:“可不是!第一次是为闹外交
罢课,第二次是为闹洋钱罢课。倒霉,自从我进大学的那年起,每个学期,都有罢
课的事。我读了四年书,大概罢了十次课。合起寒假暑假一算,说句良心话,顶多
读了一年半的书罢了。这个学期,是第五个年头,看看又算完了。再过一年半,就
要毕业。说起来在大学读六年的书,弄个学士头衔,真也不容易。要像这个样子,
六年工夫,能学个什么?家里每年汇整千的洋钱到北京来,白养我们住公寓吃小馆
子,这是何苦?不晓得留着钱,让我们在家里当少爷。”杨杏园笑道:“岂仅住公
寓吃小馆子而已乎?”吴碧波道:“自然还有,那还可以算作例外。至于在北京住
公寓吃小馆子,却是贫富一样。千里迢迢,到北京干这个,真冤。”杨杏园笑道:
“你现在是一个格议了,总算一个官。中国的父兄给钱子弟们读书,无非是要他作
官。你既然作了官了,算已经达到目的,读书不读书,那有什么关系呢?”吴碧波
道:“在北京作官真容易,不料我居然也占些官味。难怪上海斗方名士,近来整批
的往北京跑。”杨杏园道:“你这话有所